
焦点平台登录发布:
火车到了武昌,不知道要停几分钟。我溜出车厢,靠着出站通道处的栏杆,点一支烟。人极少,零零散散。犹记得进站时人流涌动推推搡搡,火车吞进去不少人,现在却没吐出来多少,那些人不知道哪里去了。巨灯悬空,恍如白昼,我总觉得不太真实,如果不是远处幽深的黑暗,谁能知道此刻是夜里三点多。可我没有一丝睡意。嘴里叼着烟,我认真地盯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女人从我面前缓缓而过,我猜他们是一对母子,小男孩歪着脑袋,眼皮上覆盖着睡意,一手拽着女人衣服的一角,空出来的另一只手拉着发亮的黑色皮箱。他们沿着楼梯一点一点往下消失。这个时候,我听到了火车要开动的声音。我把手里的半截烟掐灭,然后准备上车。隐隐约约觉得乘务员高大、笔直,像一棵树。这才仔细打量了她,她的腿很长,能撑得起那件深蓝色的长领风衣,配以黑皮鞋,似乎颇有精神,不过,我还是从她的眼神里捕捉到了某种疲倦。她很快把厚重的铁门关上,很沉闷的一声巨响,虚假的黑夜就被挡在了外面。咯噔一声,火车像被什么力量推了一把,抖了抖笨重的身子,才开始一点一点南下。
人们早已睡去,跌进黑咕隆咚的梦境,整个车厢也是一片暗色。火车像一块巨大的铁将黑夜撞得粉碎。车身摇晃不已。夜风从外面漏进来,我是越来越没有睡意。站在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又把烟点着,看见红光泛起,明亮了,又一下一下暗灭。后来,我晃晃悠悠爬上卧铺,是上铺,躺下来,反复调整姿势。无论我怎么调整,还是别扭,无数重量从四面八方压下来,有一只巨手捏着我,用力往紧攥,我感觉自己如狭小洞穴里的一只甲虫,笨拙又无奈。焦点娱乐注册
半夜醒来,发现周正东打过三个电话,还发来一条信息,内容只有一句话:你说,一个人怎么可能凭空消失?
说实话,我不知道,故无法回答。如果可以,我倒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他见多识广,或许可以解答一二。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突然发生了。告诉周正东的时候,他比我还诧异,在电话里直呼我名,韩亮,到底怎么回事?我说,陈河可能出事了。周正东在那边喊,出什么事了?我想了想,不知道该怎么说,最终还是说,他消失了。电话那头沉默着,好像吞咽下了什么。我大声喊,陈河消失了,不见了。停了许久。周正东一定在揣摩“消失”二字的具体含义。他问,你什么打算?我说,我决定去一趟广州。周正东说,一起去吧,你,我,陈河,好多年没见了。我说,好。高中毕业后,周正东考上了兰州的一所大学,毕业后留在那里教书,他算是比较有出息的一个。后来他却辞职了,换了不少工作,也跑过不少地方,一直折腾,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经历过很多,有些事看得比一般人透彻。焦点娱乐注册
陈河要坎坷一些。高考落榜后,在他母亲的鼓励下,他选择原校复读,本以为也可以像周正东那样考个师范院校,没想到,第二年他又去复读了。事后经常会听到他自嘲“高考战场,别人六年,我打了八年”。我们也只是笑笑,不说话,当时的静默里有一种任由他倾诉的理解和包容。他高中时被安置在教室后面的角落里,除了我和周正东,没有人愿意跟他说话。可还是会有同学背后议论他,说他身上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味道,说他是没有爸爸的野种,说他是异类。这让他更加自卑,也更加自闭,所以他也不反驳,就躲在属于他的角落里写诗。更多的时候是在宿舍,他睡下铺,一块藏青色床单垂下来,昏黄的光从里面一点一点挤出来,所有人都知道他躲在里面干什么,所有人都选择无视他的存在。后来有一次体育课,自由活动期间,他从教室里走出来,把刚写好的一首诗拿给我看,想要分享他的激动。我见过那个黑亮的笔记本,上面爬满了歪斜的诗行。他用手指着,眼里闪着光。如果我懂得,哪怕是一个肯定的字眼,我也应该表达出来。可那时的我正站在足球场旁边,双脚发痒,喉咙却被沉默死死抵住了。我看着他走远,像一片被风吹走的枯叶。焦点娱乐注册
车窗外,灰蒙蒙的,似要落雨。
早晨八点一刻,火车抵达广州。在出站口的位置,我看见了周正东,只是,我并不敢确定那就是他。他的变化实在太大,时间这个魔术师把他揉成了一团大肉球,他的身体越来越圆。圆起来的还有脸、嘴巴和眼睛。他的样子看上去陌生极了,这让我特别的无奈,时间真是一点也没亏待他。唯一让我熟悉的是他的笑容。他先认出了我,然后笑着给了我一个很大很结实的拥抱,我险些没站稳栽下去。他使劲拍打我的肩膀,这个画面分外感染人,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说点什么,像电话里聊天那样畅通无阻,可惜我们什么也没说,好像有什么阻隔在我们面前,我们只好长久静默。气氛有点凝重。大概我们谁也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重逢,重逢自然是惊喜的,可细如尘埃的一丁点惊喜还是被巨大的沉默吞掉了。毫无疑问,这和陈河有关。陈河本来也应该在的,他是我们这次碰面的主角,我们都希望他在,都希望他成为一个存在的主角。
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里,我拿着手机,给他看地址。
出租车很快融入浩大的车流中。周正东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手机,说,陈河到底怎么了?我和周正东都坐在后大座上,挨得很近,他的鼻息都差不多要喷到我的脸上了。我说,前天,就在我给你打电话的前十几分钟,有人给我打电话,说陈河不见了。谁?我说他叫王根。周正东说他不认识。当然我也不认识,王根大概知道陈河经常给我打电话,认为我和陈河很熟,起码,靠得住。焦点娱乐注册
其实,陈河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还是在半年前。那天下着很大的雨,雨声噼里啪啦,十分清晰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因此,陈河就把声音提高,他似乎要把那些话全部喊进我的耳朵里,让我永远记住。他说他近来老是想起他师父。他很多年前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很大的电厂。一个师父带他,每天挎着包走很长的路检查电线,日日如此。路也重复,次数多了就感觉相当无聊,好在路途中有一棵大树,树上有鸟巢,巢里有羽毛鲜艳的鸟,每次经过他都会爬上去看看。整个电厂很空旷,基本没什么人,除了工程师、一个大厨,还有他师父和另外一个电工,算上他,总共五个人。后来他师父死了,被电死的。他们把他师父埋掉,大厨特意做了一顿羊肉,没人吃,最后全部喂了草原上的野狗。他说,他师父才四十多,皮肤偏黑,国字脸,眉毛不黑,眼睛很小,一笑就没了,有点驼背,走路时,总要把一双手叠着放在身后。他永远记得。他师父爱抽十块钱一包的红塔山,每天一包。他说,他师父每天检查无数电线,无数电线通向了千家万户,可没有人认识他。他师父死的时候身边没有别人,死相极其难看,本来不长的头发呈爆炸之势,像愤怒的刺猬。他是他师父死之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他不害怕,真的,他只是难过。他说他师父叫丁贵山,死的那年儿子刚上大一。陈河说,他特别的孤独,那段时间让他想起自己的高中岁月。后来他就去了广州,他不想待在人少的地方,他要往人多的地方走。焦点娱乐注册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事实上,他跟我说了好多,可他说的大部分内容还是被我给忘掉了,只余下极少极少。高中毕业,他顺利考入重庆一所不好也不差的大学,环境变了,他的话也似乎多了。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四人间的宿舍,全班近五十人,还是没有人跟他说话。我劝他主动一些,尽管我也知道从小到大他一直被人家冷落,很难突破心理障碍。他坦言,似乎无济于事。后来,他又说,好像也没必要了,在自己的角落浸泡了那么久,早已习惯。他甚至感谢人们的冷漠、敌意、伤害,这让他感觉到了某种自由。寂寞又自由。他的毕业也并不顺利,由于高考分数低,他被补录调剂到文秘专业,并没有读自己心心念念的文学专业。也是周正东后来告诉我的,陈河的情绪由此受到很大影响,好多考试他并未好好准备,甚至都没有参加。具体内情我们并未清楚,只知道他的学分不够,没拿到毕业证。焦点娱乐注册
后来,我们都闯入社会,跌进各自的生活中,联系就越发少了。偶有联系,也只是说一两句简单的话彼此问候一下而已,不痛不痒,无关轻重,蜻蜓点水那样,似乎只是走个形式,最终还是要重新陷入各自的生活中。我们鲜少见面,只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很无奈,却似乎又必不可少。
我想,他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不然,以他耐忍的性格,是断然不会说出那些柔软的话来的。他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印象中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其实真的能狠得下心,他去了广州,五年都没有回过家。这倒不是说他不珍视家庭,相反,他极孝顺他的母亲,对他唯一的妹妹,也是爱护有加。他说,他每个月给他妹妹汇生活费,即使再苦再累,那一刻,他特别安心,特别舒服,心灵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妹妹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动力,不然,他会觉得自己活得很空。他在用爱填补内心不断塌陷的空缺。
之前他总是把这些憋在心底,鲜少与人说,也不跟我说。可是那天,他说了很多,我头一次觉得他是那么陌生,那么脆弱,又那么无助。我无能为力,我的心特别的疼,好像那些疼痛是从体内长出来的,越聚越多,越来越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疼痛感越深,愧疚感也越深。因为,那个电话之后,我们再也没联系过,而我,竟然都没有再主动给他打过一个电话。所以,坐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这次南下,从大同的一个小县城到广州,是为了找到他仅仅确认一下他还活着而已,还只是在安抚我内心的愧疚?焦点娱乐注册
我不会把这些告诉任何人,包括周正东。我和陈河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和周正东更是如此。或许,此次重逢正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我以为周正东还有很多话要问我,他没有。他把脑袋朝向车窗外,他的突然沉默让我不知所措。人总是会变的,我这样告诉自己。这些年,周正东起起伏伏,他一定有自己的经历。尽管他不说话,还较真,有时候情绪波动较大,可我知道,这就是他,骨子里他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容易动感情的人,对事情有特别虔诚的态度。我自然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固执地认为他的思考内容和陈河有关。
整个城市就是一条河,无数鱼在其中穿梭往来,寻找去处与归途。
出租车穿过无数条大道,进了一个巷子,又拐了个弯,终于停在了一个极细的巷子口。司机回过头,牙齿黄黄的,他没看我俩,说,进不去啦,这儿就这样,没办法。我和周正东下了车,看着司机倒车,出租车慢慢往后退,如果不是路旁坐着一个赤脚老头,倒车肯定不会这么慢。周正东指给我看那个老头。这时候,司机的脑袋从车窗伸出来,哎,记住,进了巷子一直往里走。焦点娱乐注册
我们便一直往里走去,感觉不太对劲。周正东问,你确定是这里?我说,应该没错,王根发来的地址。越往里,越窄。我还是决定给王根打个电话。电话一直响,没人接。周正东问,这个电话你打过没?我说没有。周正东说,咱俩一定他妈的疯了。我说,王根不会骗我的。
正说着,王根把电话打过来了。我接起来,正要说,周正东把手机抢过去,大声问,我们是陈河的朋友,陈河到底怎么了?那头传来一团浑浊的杂音,伴随着风声,呼啦啦,乱响不停。
我看了一眼周正东,拿过手机,说明了我们的来意。
王根的声音好像被风吹了似的,很破碎。我隐隐约约听他说他在送货,送完才能回来。我赶紧问,几点送完?王根说,到夜里了。
要不我们去找他?周正东喊。
我说,他送快递,满大街跑来跑去。
周正东突然笑了一下,说,我就觉得不靠谱嘛,你他妈还不信。
我想了想,说,我们先去吃点东西。
找了一家小吃店,要了两碗云吞面,味道有些寡。其间,周正东说他要再找找,问个人也行,心里一直不踏实,却很快又折回来,重新把自己放在椅子上,他松懈下来的样子像一滩水。我们都没有说话。后来他才把包拉开,从里面拿出一大袋砂糖桔。我捏了一只,一瓣一瓣吞下去。周正东看着我,拿起一只整个吞了下去。他连续吞掉十三只,我数得真切。我看着他把最后一枚橘子消灭掉,空气沉默又寒冷。焦点娱乐注册
这时候我听见周正东说,他妈的,你说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吧。
我说,那我们再去找找吧。周正东说,我刚刚绕了一圈,没问到人,碰到一个,他讲话,完全听不懂。停了一会,周正东又说,你再给王根打电话,我还就不信了。我就把手机拨通,置于耳边,嘟了一下,再没有别的声音。门外突然响起一阵鸣笛,放眼瞧去,一辆电瓶车突然刹住,其上坐一男人,以脚尖撑地,冲我们这边喊,谁是韩亮?我赶紧往外走。他看也不看我,说,我是王根,走,赶快走。我问,你怎么找到我们的?他说,我对这一片太熟悉了,找个人容易。电话里的他说话轻绵,嗓子细细的,没想到他胡子浓密,爬了满脸,以至于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他也不容我多看,用下巴示意我坐在后面,我回头看了一眼周正东,他正缓缓而来,像踩着云朵。王根说,那你们跟着我吧。电瓶车就朝前冲出去,我拉着周正东紧随其后。拐进一巷,极细,仅可容一人,电瓶车也勉强通过,他却骑得飞快,两面墙壁均未触碰,电瓶车发出一声巨响,飞了出去。周正东气喘吁吁,一直在骂,他妈的,这是催命呢。出之,视野一下开阔,却是一片排列密集的楼,逼仄、拥挤,分不清东南西北。电瓶车停下,王根仍以脚尖踮地,等我们赶来,他摸出一枚钥匙,说,四楼,右手边,最里那间,阿河的屋。我这才想起来,他把陈河叫作阿河,电话里他就是这么叫的。焦点娱乐注册
我问,他到底哪去了?
王根说,我不知道,鬼才知道。
周正东说,你好好说话。
王根说,我还有一大堆东西要送。临时路过的。要不我晚上回来再说。
我这时候才看见,电瓶车前面,他脚下的位置,放了若干小纸箱、塑料袋。
周正东说,我就问你一句,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王根说,最后一次?就几天前吧。我没注意,阿河那天就出去上班啊,送快递啊,晚上没见他回来。好多事情都这样,事前怎么能想到。就像丢了一件快递,你事后才知道它丢了。
周正东说,没有前兆?
王根问,啥?
我说,就是他有没有啥异常的行为之类的?
王根的右手放在把手上,一直在拧,电瓶车时不时发出呜呜声,一阵又一阵。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话很少的,我就不知道他心里想啥。
周正东说,你再想想啊。
王根说,要不等我晚上回来,我的时间不比你们的时间。
我和周正东互相看了对方一眼,都不说话。
王根又说,要不去他屋看看。
我点了点头,问,你报警没?
不知道为什么,王根的身体抖了一下,他却突然笑了出来,说,报了,没有用的,他们只问了些信息,一直也没个结果。他并没有看我们,他的眼睛盯着地面。你们知道,其实,每天都会有好多人不知所踪,谁也不知道他们哪里去了。焦点娱乐注册
你居然用“不知所踪”这个词。周正东说。
王根说,有一次我们一起爬那个塔,阿河说的。
就是那个广州塔?
图片
王根说,嗯。停了一下,他说,我真的得走了,你们去他屋看看,收拾收拾,房租到期了。
说完,他已骑着电瓶车飞去。我看着他和电瓶车一起越来越小,接近于无,最后消失在小巷的拐角处。我的心里突然很惆怅。陈河会不会也是这样和电瓶车一块消失的?周正东问我,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奇怪?我说,有点,说不出是哪里怪,总之别扭。
我们站在楼下,往上望,上面没有光,太阳被遮挡,当然不是阴天的缘故。楼层实在太密集。根本不知道哪里是院子,只有一条窄窄的楼梯,楼梯口旁放满了电瓶车、自行车,基本都上了锁,就拴在楼梯口的铁条上。周正东在前,我在后,我们开始爬楼。楼道黑暗,吼一声,想把声控灯吼亮,未果。终于爬上来,过道也窄,许多衣服从上面垂下来,密密麻麻,地上堆满杂物。抵门边,打开,一股沉闷之气扑来,迎面一张床,单人的,紧挨窗户,窗外有铁架,用来挂衣服,只是,铁架很空。床边一桌,极低,或可作木凳。几乎无立足之地,周正东就坐在床边,还在喘气,他妈的,这就是陈河住的地方?我很难受,没说话,看着他躺下,床咯吱了一声,周正东喊,不会坏了吧。说着,他又站起,床以巨大的声响回应了他。周正东说,我一直不知道他居然住在这样的环境。我说,漂泊在外的人,没有一个容易的,先看看他的东西吧。焦点娱乐注册
周正东不搭理我,说,他会不会被车撞死了?司机逃逸,他就躺在路边的草丛,可是没有任何人发现。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会不会突然累死了?前几天我上网看见一条新闻,说有一个人工作太累突然死在家中,过了好几天才被发现。
我也看到了那条新闻。那是一个写作者,每天伏案写作十几小时。死时还不到四十。
难道他自杀了?周正东盯着我。
我说,你到底想说啥?
对了。周正东不看我,大声问,你说,他会不会回家了?你有没有给他家里人打过电话啊?
我知道,陈河来广州已经五年,都没有回过家。期间我给他打过好几个电话,问及他回来与否,他也只是轻轻叹一口气。然后,他会非常兴奋地邀请我们到广州找他玩。我们嘴上说会去的,可从来也没安排过行程,见面遥遥无期。
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就被王根的电话打断。他确实奇怪,更甚者,他居然骗了我们。警察已经通知过他好几次了,让他去一次警察局,肯定是有事,具体是了解情况还是通知结果,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他是没去,就这样一直拖着逃避着,他也没有把这些详情跟我们说。这加大了我们的怀疑。可用他的话说,他是不敢面对,更不敢接受。他把电话打来,让我们去找他,碰面后,他说得特别快,你们知道吗?上次我们有个小伙子就不见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是警察告诉我们结果的,说他死了,就在送快递的途中,在夜里,突然死掉的,死在路边,第二天天亮才被人发现,他身体一直有毛病,可他每天都在上班,真的是这样,有一次他是打着点滴送快递的,这让我们特别的难受,我们让他请假休息,他说他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父亲的两条腿都断了,常年卧床,母亲没有工作,全家就靠着他这点工资,可是,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他父母的。听他说完,我和周正东都沉默了,我们都没想到王根一下子说了这么多,简直就是一口气说完的。事实上,他在电话里就说了一句,警察有消息了。大概他实在忍不住了。焦点娱乐注册
我跟周正东说,他不想接受这样的结果。
周正东说,我们也不想。
只有我和周正东去了警察局,王根没去,我们都没说他什么,他大概是不敢面对。一个中年男人先简单说了一下工作进展,接着就跟我们了解陈河的相关情况,基本是陈河多年前的一些事,我向他介绍了陈河的性格以及高中时的一些事情,周正东回顾了陈河步入社会的辛酸遭际。大概有些眉目。后来,他跟我们点了一下头,然后,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一个小伙子就进来了,中年男人看了我们一眼,说,让小邓带你们去认尸。与其说我刚开始没有听懂——我以为是“认识”二字,还一头雾水——不如说我不敢相信。我永远记得通向停尸房的那条长长的走廊,才走了不过几分钟,我却感觉走了好多个黑夜。等我看到那个人时,我才恍惚回到了现实。可是,这样的现实是多么的残忍。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陈河,他没有头发,面目扭曲,五官排列很不均匀,而且,极瘦,死神夺走了他的生命,连同他的肉身也一块榨干了,一点一点,直至荡然无存、灰飞烟灭。我想知道他的名字,小邓突然笑了,要是知道他的名字,就不需要别人来认领了。焦点娱乐注册
周正东悄悄和我说,他们都是无名者,只有一个又一个序号。
下一个是四七号,小邓把他从尸柜里拉出来,我看见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还有脸的轮廓,都和陈河极像。可我还是无法将其与陈河联系起来。他的身体塌陷下去,腰部那有一大片明显的凹槽。周正东却一直犹疑,他觉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他的身长和肤色看起来也好像吻合。周正东问,有没有他的基本信息?小邓说,我们要是知道,就好处理了。周正东更正他,我要的是他的死亡信息,比如,他的死因,死时的状态,等等。小邓又把他推进去,用手指给我们看,在“四七号”这三个字下面还有一行看起来特别小的字。男。年龄不详。坠楼死亡。3月18日送达。我突然感到一阵悲哀,还有恐惧。一个人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一件多么残暴的事情。他没有自己的名字、职业、家人等生前信息,人们只能根据那一行字想象他生前的境况。焦点娱乐注册
焦点娱乐平台:www.sdptzc.com
周正东说,他肯定不是。我问原因。周正东说,你看他的脚,没有那块黑色的胎痕。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陈河的右脚有一片暗黑色的胎痕。接下来认起来就很快了,我们看了八九号、五号、三六号,其右脚都无胎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陈河还是没有下落。
我和周正东从警察局出来,一路不说一句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我想的是那些无名者,他们躺在长长的尸柜里,很快就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我们决定回陈河住处,收拾陈河的东西,或许能找到一点消息。
陈河的东西并不多,他在这里生活了五年,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度过的。毕业后他先去了一个文化公司,压力巨大,经常加班。有一次他跟我诉苦,连续通宵好几晚,早晨走出单位,感觉自己就是刚从监狱出来的囚徒,看着明澈的蓝天,他突然哭了。文秘,采购,传菜,装卸,配单,销售,电工,他均干过,都没从一而终。命运给他打开过许多扇门,同时,也注定要给他诸多摔打。焦点娱乐注册
门后边有一个很大的黑色皮箱,里面全是小卡片,黑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窄的,还有圆的,绝大多数其实是些衣服的标签。周正东说,你怎么不说话了?里面有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陈河有搜集衣服标签的爱好。周正东这才把脑袋转过来,说,你不知道啊,他很喜欢书签,或许是当书签用的。我拿起一张,这不会是收件人的信息吧,好详细。你听听,刘耕,广州市黄埔区丰乐北路。这后面居然还有电话啊。周正东已经站到了我身后,说,我瞅瞅。他拿起一张,念着,章婷婷,广州市天河区上社村。又拿起一张,季大民,山西人,装卸工。又一张,徐树,吉林人,后厨配菜。周正东突然停住,问我,你说,他到底在干什么?记住这些人的信息?
这些标签上都是这样的信息。
我们陷入巨大的沉默。后来,周正东突然笑了,他说,他或许没事。
我看着他。
周正东说,你看他这屋子,不像突然消失的样子。焦点娱乐注册
我说,我不知道,总之他不见了。我问,你找到了什么?
周正东刚才一直在桌子那边翻抽屉,动作颇大,我有心喊他一下,见他的脑袋埋下去,我就没开口。
他说,看到一个本子,好像写了日记。
我说,他当年就一直写诗,还写日记。我们怎么把这个给遗漏了。
周正东说,也没多写,有的长有的短。我读给你听。
今天,心情真的不好,苦闷又压抑。又让王飞骂了,我不过就迟回来了十几分钟,可是,他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会知道正在和即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我没法跟他解释,当然,他也不会听。我也没法跟别人说,我想,这个世界上愿意听我说的人,几乎没有。我很失落。天一直下雨,真的很难让人忍受。这个小区,我来过很多次了。我永远记得。门口那排树很绿。要不是那个人,我也不会迟回来,没有迟回来也就不会让王飞骂。当然,他是我们的头儿,管着我们,无所谓了。让我难受的其实还不是这个,骂不骂就那几句话,我不放在心里也就罢了。真正让我难受的是一个人,他叫赵小军,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可他就那样死了,要不是我去送快递发现了他,他还不知道要在床上躺多久呢。要不是我闻到了一股臭味,我还不一定能发现他了呢。我报了警,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了警察,很快就有很多人围起来,法医也来了,他说赵小军已经死了76个小时了,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他才二十八岁。他家里人哪里去了?我不知道。我没时间知道了。警察还打算带我去做什么笔录,最后,就在赵小军的房间解决了。赵小军很快就被一大块白布覆盖,一下子就看不见了,可我一直记得,他的脸很圆,嘴巴扁扁的,嘴唇很厚,对了,嘴巴和鼻子都往外流那种黄颜色的水,他的头发乱七八糟,一定是很久没有洗头。我一直记得这些,记得他的名字,记得他的样子,记得他躺在床上的姿势。括号,括号里面写着侧躺,双腿弯曲那样。好多人的名字和样子我都努力记住,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做,好像是从我师父死了之后。我离开了,回头看见有些人也正渐渐离开,人们肯定只对他的死因感兴趣,没有结果,他们也就失去了兴趣,有的人还在捂着鼻子猜测,也不会猜出来。赵小军死了的样子和睡着没啥区别,可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是睡过去了。可惜的是,他太年轻了,比我还小。回去确实晚了十多分钟,王飞也是急了,还有一大堆快递等着我送,他骂我我能理解,但我真的没法解释。焦点娱乐注册
周正东把头抬起来,似乎读不下去了,刚才,他的声音就有些哽咽。我们都不说一句话,似乎,所有的口头语言都失去了表达的功效。
后来我才问他,完了?焦点娱乐注册
他似乎还陷在刚才的情绪中,只是点点头,把日记本递给我。
没有日期,全是零散的片段式的记录,有的一大段,有的几句话,有的只有几个字而已。
登塔。人很多,却又很小。不知所踪。
我不知道陈河想说什么。
我看着周正东,你给解释一下。
周正东没回应我,日记本没有封皮,最外面的那层白纸有点黑,已经卷了起来,周正东使劲将其铺平,未果,他就把手放上去,一直那样按着。按了好久。周正东说,再看看。
我没说话,又打开。发现了一首诗。
众生
要往人多的地方走
人多的地方你才更加孤独
而孤独,可以让你认清很多事物
不要大声讲话,要学谦卑的牧羊人
每一只低头吃草的羊
牧羊人都能喊出它们的名字
后面没了。我拿给周正东看。周正东眉头紧锁,牧羊人?我问,你发现了什么?许久,周正东才说,他大概有极深的痛苦。我说,可他从来也不说。周正东笑笑,其实,我们也不说。我感觉有一些东西被彻底折断了,根却还长在肉里,以疼的形式提醒着我们。周正东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痛苦有时候会带来清醒,他经历过不少,或许,他才是那个最清楚自己应该干什么的人。
我似乎有一点懂了。
周正东突然问,要不要去看看那个塔?我问去那儿干什么?他说把陈河走过的路走一遭,把陈河看过的地方看一遍。我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他。周正东说,不,最重要的是先了解他,知道他的想法,他或许没事。周正东沉默了。焦点娱乐注册
等了一会,他说,其实,我不知道。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我知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主动离开的人。
他对陈河的这个事情突然没那么伤心了,或者说不是很在乎了。反而很看得开。这让我惊讶又难受。
后来,我们登上了广州塔,我不敢往下看,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们脚下。
我说,我们还是没找到陈河。
周正东不看我,说,你知道吗,刚才我们乘电梯一点一点向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陈河。他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牧羊人的故事。那个牧羊人养了一群羊,经常带领它们去溪水边。可惜,这个牧羊人最后还是死了。
我听过这个故事。
我说,他被人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不,是他自己主动走上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救人。
救什么人?
众生。
我说,陈河的那首诗要表达这个意思?
周正东说,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起有这么一个故事。他让我想到,陈河、你、我,包括那些死者以及更多的生者,我们,都是众生里唯一的那一个,不该被遗忘。陈河一直处于被遗忘的地带,他的孤独、冷漠甚至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造成的。我看着周正东,他似乎也被什么东西击中了。可是,你也要知道,所有人本质上都处于遗忘地带,也没有人能够被长久留存,都要死的。焦点娱乐注册
我有些难过,巨大而又空虚的难过。
周正东说,陈河经历过,大概更懂得慈悲的分量。所以我才觉得,陈河想让我们做的,绝不是找到他。
那是什么?
记住他。
记住他?
周正东说,对,记住他,他就活着。
永远活着。
说完,他拿出一张照片,说,陈河日记本里找到的,本打算放你包里,一会上了火车告诉你,想了想,还是现在给你吧。我们都没有陈河做得好。但有一点,我们要记住彼此。
我把照片拿在手里,看着它。我永远记得,照片是周正东拍的,照片上有我和陈河。许多年前,陈河冲着我喊,来,快点上来,上面高,视线好,看得远。他那天心情特别好,一点也看不出是那个被很多同学歧视鄙夷的男孩。他的眼睛很明亮,四肢坚强有力。我咬咬牙,身体弯成弓,一下一下往上爬。快上来时,陈河伸过来一只手,拽着我,将我拉了上来。我和陈河并排坐在山顶,我们面前是一大片广阔的树,没有尽头。群山在我们身后长起来。只是,后来,它又陷落下去。
陈河一直留着这张照片。
周正东说,是的,他一直记得我们。一直。
他记住了很多人。他还会记住更多人。
我没再说话,心里很复杂。周正东说,该走了。我们从广州塔下来,径直去了火车站,无数人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周正东像见面时那样拥抱了我,这回很用力,很用力。然后,他就走了,他那么胖,我看着他一点一点消失,不见。像一滴水又重新回到水中。焦点娱乐注册
黑暗垂落下来,光一下一下隐没。
王根说过,走时要跟他说一声,我给他发去一条信息。他没回,他肯定在送快递的路上,骑着他的电动车,风驰电掣。我永远记得。我知道,陈河也会在路上。我也会在路上,带着我们的照片和全部过去,闯入茫茫黑夜。

李一默,生于1988年,山西右玉人,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漂泊者,写作者。有小说散见于《青年作家》《湖南文学》《黄河》《红岩》《天津文学》《福建文学》《南方文学》《安徽文学》《当代人》等,另有评论文章见于《文艺争鸣》《文艺报》等。
焦点娱乐登录: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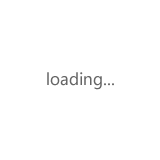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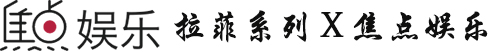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