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注册报道:
1
当钟楼和鼓楼在岛上高高耸起后,我走在晨雾和月光里,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那眼睛高高在上,让我无处可逃——莫非是两座楼阁里的钟和鼓,变成北斗岛的眼珠了?
北斗岛在大湖中,以前是芦苇疯长的荒岛,野水鸭摇摆着肥肥的臀部,成群结队地踱在滩涂上。三年前,岛上长出铜建筑、铜雕塑,就成了一座名为青铜国度的旅游区。野水鸭消失后,岛上没了原住民,酒店的服务生、铜街上的铜匠、博物馆的保安都是从外地而来的打工人,来来往往的游客全是陌生人——这样的岛是安全的。在钟鼓楼还没建起时,我不用担忧一扇扇窗户后有熟悉的眼睛审视我窥探我,也不用担心迎面相遇的人突然喊出我的真名或乳名,觉得四水环绕的小岛真是适合人居的地儿。你不用猜测我的身份——在岛上,我只是老铜匠的年轻徒弟,一个热爱北斗岛的雄性人类。
至少有大半年的时间,我跟着师傅在为岛上建钟楼。那是一座位于铜神广场左侧的新建筑,在花岗岩砌成的高台上,建起三层的铜楼阁,八角的重檐上挂着铜铃,一口大铜钟悬在三楼上。我们铜街上的铜匠五方杂处,南腔北调,有来自云南的斑铜艺人、北京的景泰蓝传人、皖地的失蜡法工匠,大多投身到这项工程中,有的制铜立柱铜门窗,有的做铜鱼檐铜瓦当,我和师傅铸的是大铜钟——据说师傅是岛上手艺最好的铜匠,只有他才能让铜发出黄钟大吕的声儿。我们一天天地熔铸、锻压、焊接着铜料,才把钟楼建了起来。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铜神广场的右侧也有一个花岗岩高台,与钟楼左右对称着,却一直没有工匠劳作的动静。那些天,我站在钟楼的脚手架上,看着另一个空空的高台,心里直犯嘀咕:那上面会建起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开工呢?甚至觉得脚下的岛因两座高台一轻一重失去平衡,轻轻摇晃起来。没想到就在钟楼竣工不久,一座楼阁在右边的平台上一夜之间耸立而出。那也是三层楼阁,却是砖木结构,木窗木梯木架瓦当,一面大鼓架设在三楼上。它突然而至,仿佛是从天外飞来的。其实,那是从别的地方收购来的旧鼓楼,拆运到岛上重新组装起来的。它是个不速之客,却总算跟钟楼一左一右,让湖中的岛平稳了。
我问过师傅:北斗岛是景区,建钟鼓楼做什么?是供游客登高远眺吗?可岛上已经有高高的观光塔了啊!
师傅脸上的皱纹比青铜器纹饰还深密,他沉着脸:钟楼是用来鸣钟报时的,鼓楼是用来敲鼓报警的,一方水土得有这两座楼。
我在心里暗笑:师傅真的老了,现在能报时的玩意多了,青铜时代大酒店大厅里就挂着数个时区的钟表,把时间搅乱了。而北斗岛上虽没有警察,却有保安在防火防盗防游客落水,还需要用鼓报警吗?——人老了,真的会变得多忧多虑。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不过,师傅有一句话说得对,重大的土木工程开工或竣工时,往往会发生献祭上苍的事儿——鼓楼落成那天,就有一只黑狗不知怎么被环岛绿皮小火车碾成了一张薄薄的皮——其实岛上禁止养狗,那只黑狗从哪儿来的呢?
2
我是在耳朵出了毛病之后来到北斗岛的。不知怎样的一声巨响,把我的耳蜗震坏了。我能听见声音,但有时会失聪或听出重音,甚至出现幻听,耳鼓里还会响起嗡嗡的回音。我的脑瓜也开始跟着耳朵犯迷糊,像是得了健忘症,把一些熟人的脸弄丢了,记忆乱成了并不连贯的碎片,就像调皮的孩子打水漂,用一块块石子掠过水面,击起一圈圈并不真切的涟漪。我到陌生的岛上,应该是逃避曾经熟稔的声儿。我天天对着镜子说话给自己听,跟做康复训练似的,想唤醒记忆,让自己重新耳聪目明起来。
我以前可能是不知名的乐队鼓手。我仍记得一些场景:小学操场上,小鸟从晨光中飞过,数棵小白杨排列成行。小模样的我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站在鼓队的行列里,跟着整齐划一的鼓点,奋力地敲打着挂在胸前的军乐鼓。鼓声从我胸膛里跳了出来,然后是红红绿绿的气球从面前学生队伍的头顶飘了起来——那是在欢庆儿童节吧?而在小城的古城墙上,数个刚长出胡子的少年抱着吉他敲着架子鼓弹唱着,他们歇斯底里地吼叫,奇形怪状地扭动,不知是似霜的月光还是城墙上的苔藓让他们脚底打滑儿。不远处,鼓楼突兀地立在断垣残瓦上,就像翅膀过于肥大的黑鸟。那里,一片旧街区已被黄色的推土机夷为平地,推倒的不只是民居店铺,还有明伦堂和城隍庙。那些毛头小伙中,有一个甩动长发敲着鼓的人,那就是我。最终,总有粗鲁的喊声从城墙下传来:你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学生伢,还不回去睡觉,在瞎折腾什么?——于是那个午夜的梦境就会在那高喝声中逝去。再后来,我应该是跟着乐队在酒吧里驻唱了。我能清晰地记得,在闪烁的光影里,贝斯手、吉他手、键盘手在如痴如醉地弹奏,我半眯着眼快速地敲打着面前的大鼓、小鼓和吊钗,恍惚在追赶飞奔的马群。忽而,一道闪电劈下来,灯光骤地熄灭,酒吧安静了片刻就成了黑色的海。贝斯、吉他、键盘都哑了,我知道那不是伙伴们停止了演奏,而是那些乐器都需要插电,没有电他们只能沉默下来。而架子鼓不需要电,我稍稍停滞了一秒,赶忙用力地敲起鼓。我的鼓槌是长了眼睛的,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准确无误地击向鼓钗。酒吧里人声喧嚣,尖叫声、怒骂声四起,器物的碰撞声、碎裂声响成一片。我敲得更认真了,想用带节奏的鼓声恢复有光时的秩序。我想也许有音乐世界就不会乱的,可敲出了一身汗,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徒劳的。我的鼓声并不能让酒吧平静下来,反而像在煽动更大的骚乱。我用另一双眼睛看着黑暗中的自己,觉得那个鼓手挥动鼓槌的样子就像垂死挣扎的溺水者。不知过了多久,警笛尖利地呼啸而起,灯光雪崩般地亮了起来,我像是患了雪盲症的兔子,在一阵撞击声中头晕目眩,跟着面前的架子鼓摔了下来——也许就是在那个撞击声中,我的耳朵被震坏了。现在面对架子鼓,我笨拙地举起鼓槌,却不知该如何下手,就跟没学过敲鼓一样,甚至一听鼓声就头晕。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为确认曾是鼓手的前史,我上网搜索了一些酒吧乐手的故事,来丰富自己的过往。在想象中,我从小就具有音乐天赋,刚会走路时就能用耳朵捕捉到唱针在密纹唱片上走动的舞步,中学时代跟同学弄了个小鸟乐队,开始逃课练习架子鼓,高考失利后漂在某座城市,游走在酒吧、咖啡店演出,维持着生活和梦想。我在酒吧还认识了一个女子,她刚到酒吧做服务生时,总背不熟酒单,对着吧台里的店长说:来一杯芝加哥!店长便笑,斟上一杯酒递过来:记住!是芝华士!女子就吐着舌头笑——这就是我认可的个人史,不知哪些来自记忆,哪些是来自别人的故事,我对前史的杜撰就像拙劣的抄袭者。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可是,总有一个记忆片段像骨刺一样不时钻出来,提醒我以前做过石匠。我隐约听见过有老人的声音风一样飘来:你得记住!真正的石匠无论是用石头雕狮雕人雕佛像,都是在雕自己。咱们一点点地琢去石头多余的部分,最终留下来的石头就是自己!我也多次在梦里听见炸药爆炸的巨响声,看见被炸得满天飞的石片,醒来时鼻尖上还萦绕着硝烟的气味——也许作为石匠的我,就是在那炸药的爆炸声中震坏耳朵的吧?也许我在北斗岛上做铜匠,不是毫无来由的。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3
我原本并不觉得钟楼和鼓楼像一双眼睛,而是从自称作家的男人上岛后,才有了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那个长头发的家伙应该是追踪旧鼓楼而来的,他在鼓楼下转悠,细长的身子就跟旗杆似的,被长发半遮的眼睛萦着雾气看上去像在梦游。他一遇见游客就说他知道鼓楼里大鼓的来历,力排众议地指出那面鼓不是牛皮鼓而是马皮鼓。可游客没有兴趣听他细说掌故,礼貌地笑笑就走开了。他只好把满肚子水泡咽回去,就像搁浅在岸上的鱼。我对长发家伙没有兴趣,见到他也不理睬,可他偶尔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我面前,就像是跟踪我的影子。北斗岛是铜的岛,岛上高楼大厦的铜幕墙在日光下就像一面面光滑的暗玻璃,四周湖水波光潋滟地荡漾着——这种光影绰绰的岛似乎为长发家伙的出现提供了绝好的场景。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走在岛上,你不用担心迷路,也不用担忧湖水会把岛淹没——这是湖中岛,不是大江大海里的岛屿,而且被一列供游客环岛观光的绿皮火车环绕着。岛上没了野水鸭,湖里没了鱼,却有一座动物园,那里有用铜铸造出来的奔马、大象、孔雀、长颈鹿,就连路灯的光亮也是从铜鸟的腹中闪出的。岛上有一座圆形的青铜博物馆,里面展示着古老的青铜器,那些铜鼎、铜剑、铜钟看上去铜锈斑驳,却不知是真件还是赝品。岛上当然还有酒店、广场、超市什么的,而我师傅的店铺就在铜街上,那是铜匠们打制和兜售铜工艺品的地儿,每一件铜工艺都有着好听的名字,譬如铜马的“马到成功”、铜猴的“辈辈封侯”、铜鹤的“松鹤长青”,据说它们能给游客捎去吉祥。我师傅出身铜匠世家,祖上参加过永乐大钟铸造工程。可老头不声不响,似乎是只会与铜说话的哑巴。邻铺古大师人高马大,扎着马尾辫穿着绸褂,嘴巴就像冒着热气的火车头,整日吹嘘他是紫铜铸法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说他打制的铜件不是工艺品而是艺术品,就连跟别的店里一模一样的铜佛像,都是经高僧开过光的——因而他的店里生意很红火。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在铜街上奔来跑去地嬉闹——我分辨不出两个孩子谁是谁,就此怀疑古大师是个高仿器的制造者。古大师与我师傅就像一对反义词,这没什么奇怪的,北斗岛不是总把倒影投在湖上么?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一上岛就成了师傅的房客——我没有钱去投宿大酒店,恰好师傅出租楼上的小房间,而且那房子里恰好有一面大镜子——我就长期租房住下了。没过多久,房东变成了师傅,我得找活干才能在岛上生存下来,而师傅觉得我对器物造型悟性好,似乎以前学过铜匠,就把我留了下来。我喜欢铜街,在满街叮叮当当的金石声中,耳朵的毛病好多了——难道那缓慢有力而又单调的敲铜声是一种药?我恍惚记得我在做鼓手时,疯狂地追求过一分钟330拍的速度,那是多么让人热血沸腾啊!师傅晓得我耳朵有毛病,也知道我去过城市医院找过乡下郎中都没法治好,为此眉头锁了好久。有一天,他突然说也许听瓮能治好我的病——就是铸一口大铜瓮,掩埋在地下,让我坐进瓮里,闭上眼睛去听。他说瓮是埋在地下的鼓,在没有钟鼓楼之前,有些地方为了防灾防盗,会在地下置一大瓮,让盲眼人坐在瓮里,一听到十里之外的山石洪水声、盗贼马蹄声,就钻出来报警,好守护一方平安。他说地下的铜瓮能把一些声音消弭,又能把一些响动放大,一个人坐在瓮里,听不到世上喧嚣的人声,却能听到地下的响动,比如湖水流动的纹路、草茎抽芽结籽的声儿,那些声音会洗净我的耳朵,让我的耳朵好起来。我并不相信师傅的话,笑他的疗法是野狐禅——因为他是铜匠,不是医生。师傅只得放弃打制铜瓮的念头,那个好面子的老头不肯承认自己的说法是无䅲之谈,只是叹了口气说:也是!如若让你听瓮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那就对天地不敬了!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在岛上还认识了个姑娘。那天的铜街阳光明媚,一个女孩突然站在我面前说:来一杯芝加哥!我脱口而出:记住!是芝华士!她露出两颗牙齿笑了。我愣愣地看了她半晌,才确定并不认识她。看来她是读到我博客上的酒吧乐手故事,才找到我说上这段对白的。我没事时喜欢发发博文,不是想成为不靠谱的作家,也不是想吸引粉丝,只是想把想象中的自己前史记录下来——也许文字是对抗遗忘的最好方式,要不这座才开发三年的景区,怎么会有个像派出所户籍科那样的档案室呢?渐渐,我跟姑娘相熟了,可我告诉她有个长发家伙总鬼鬼祟祟跟着我时,她却不肯相信,一个劲地摇着头。我赌咒发誓没有骗她,她只是浅浅地笑,循循善诱地说:你不是逃犯,也不是逃避高利贷的人,怎么会有人跟踪你呢?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我急了,真想把长发家伙揪出来给她看,可那家伙神出鬼没,想让他出现他却不见踪影,再说岛上那么多游客,我到哪里能找到他啊!她还建议我跟她玩游戏,说那样我就不会耽溺于幻想了。她跟我玩起那种小孩子的把戏——她说鼻子眼睛什么的,让我用手指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五官。如果我指错了,她就笑。如果我找对了,她就会在的额头上吻一下,就跟小鸟啄米似的。她的笑声很明亮,能把我脑瓜里的雾气驱散。她总是那么鲜活生动,我应该相信她,我有些怀疑长发家伙是我想象出来的了。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可某个夜晚,长发家伙又出现了。岛上灯火朦胧时,他扑进铜街13号店铺,跟我和师傅说起一则关于马皮鼓的故事,语速很快,像是在背诵诗篇。奇怪的是,他竟然像穿越剧那样成了故事里的人物,仿佛在说亲身经历的事儿。他说的故事太荒诞了,让人听得心绪不宁。正如你所知,作家往往有精神上的疾病,我怀疑他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谵妄症患者。长发家伙还没说完,我就忍不住打断他,把他推出门外,还给了黑夜。没想到他看上去很瘦弱,推搡起来却很费力。师傅对我的待客之道很不满意,深深地瞥了我一眼:你怎么能这样?他的故事还没说完呢!然后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长发家伙的身影消失。师傅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说话口音重难听懂,只喜欢用铁器跟铜叮叮当当说话儿。也许他是个厚道本分的人,觉得我不应该对人欠礼貌吧?也许铜匠和石工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才对长发家伙编的故事有了兴趣吧?可是长发家伙说的故事太荒唐了,不信,你听听——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长发男人说A
东魏武定四年深秋,天寒,露冷,霜白。
我和衰老的白马站在山塬上。寒风鞭子般抽来抽去,甩在石崖上就是一道尖利的哨响。老马驮着我的王从草原征战而来,不知怎么就老了,眼花了觅不见草儿,只能像狗一样嗅来嗅去,可秋风早把青草的气息带走了。这是老马的最后时光,王说,它的皮质尚好,要剥下来蒙战鼓。
这座山叫滏口,山峦绵亘,颇具嵯峨之势。可我知道,堆垒出那种气势的,不过是一些秃陋的石头,就如那风尘仆仆赶来的石工。那些石工是王朝最优秀的石匠,建造过太多的石窟,这次来滏口还是要开凿石窟的。我的王一直纵横在烽火狼烟中,可此时谣言四起,说他身中弩箭即将死去。为稳定军心,患病的王勉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会上,王仰卧座上,用苍老的喉咙唱起歌谣: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唱着唱着就流下了眼泪。是啊,在另一片天空下,草原辽阔,风吹草动,牛羊成群——那是我们云朵的故乡。罢宴后,我就奉王命带着他的老马来到滏口,来完成他的最后愿望了。我知道要建造什么,但不能说,为了王朝为了王,我所能做的就是噤口不语,并严令重兵驻守在山峦四周,不让一只聒噪的鸟飞出山谷。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夜色是个好东西,就像油漆掩盖去什么。当天空黑下来时,风缓了。山岭下亮起一地飘飘摇摇的火光,火光处石工们正在喝酒,毫不吝惜地将喧闹声砸了过来。我卸下冷硬的战袍,从岭上营帐向岭下灯火走去。我曾征战沙场,立过赫赫战功,可此时真想走进石工,混迹其间,长醉不醒。竹棚前,石工们此起彼伏地围坐在火堆前,面前数个庞大的釜里翻滚着肉花,冒出热气。他们用长竹棍挑起白花花的肉片,抚着滴着酒液的胡须,那种好胃口真让人羡慕。
我站在黑夜的一角,看向火光中的石工,目光跋涉过一张张脸,终停在一张年轻的脸上。那张脸上比别的石工明亮,还残留着绒绒的稚气,也许因为年少,被酒烧得像蓬松的火球。
有人笑他:民,这是你小子第一次上山凿洞吧?
少年抿口酒:诺!我家世代为石工,我身上流着石头的血。
又有人笑:民,你还是童子身吧?
少年一愣,有些羞涩,但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知不知,初次上山凿洞前,得找个女人开洞,破了童子身,这是咱石工的规矩呢。
是么?我怎地没听说过?少年睁大眼睛,着急起来:这满眼大山,哪里有女人呀?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众石工哄然笑起。
年老的石工贺爷笑得脸上皱纹卟卟纷落,摆摆手:莫要取笑民了,他还小。
渐渐,釜里的热气丝丝缕缕散去。火堆旁,石工们冷寂下来。
忽而,一年壮的石工灌口酒,站了起来,仰身朝着山顶喊起号来:哟嘿,哟嘿……
众石工应声而起,粗犷的喊号声直扑向无边的夜色。
焦点娱乐:www.sdptzc.com
我在那高亢的喊号声中,仿佛回到了伊阙。多年前,我曾在伊阙见过石窟。我不明白:王们为何总喜欢开山凿窟,难道他们以为把自己的模样刻成石像就能永垂不朽?
……
时光一天天流去,大山在叮叮当当地敲石声中醒来,陡峭的悬崖上渐渐露出洞窟来。石工们日夜不休地开山体,凿石洞,雕佛像。每每夜晚,崖上的火光与天上的星辰散落在旷寂的山谷里,而我的士卒兄弟们坚守着,没有让一点儿火星逃遁出去。
老马死了,我先剪去马鬃马毛,用锋利的剥皮刀划开它的腹部,放出八大瓮的血,再将刀尖抽出马骨,割去皮上残存的肉块,把马皮完好无损地剥了下来——其实老马已经很瘦,马皮就耷拉在嶙峋的骨架上,是很容易剥皮的。继而,我用杂草擦去皮上的污血,将整块马皮蒙在桑木做成的圆形鼓架上翻晒。秋日的阳光并不强烈,马皮经一日一日地晾晒收缩了,紧紧地绷在鼓架上。我还特意留下老马的四蹄腿骨,准备做成鼓槌。我想在滏口石窟完工之前,一面马皮大鼓就能制成了,鼓声正在我想象中呼之欲出。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那些日子,民常在夜晚跑到岭上看我制鼓。那个少年并不像石工们那样敬畏我和我的马鞭。他曾指责我对老马的残忍,为老马雕刻石像埋于西坡,祝老马灵魂安息;曾偷偷藏身马皮鼓内过夜,说那样他就会梦回故乡。我不忍责怪于他,他太年少了,年少得让我愧疚——他是不应该来到这里的。
民跟我说过石工们的故事,说得最多的是武阿仁——那个喜欢吹石埙的哑巴石工,总在他雕刻的石像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我多次用马鞭教训他,让他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可他总是抬着血痕纵横的脸冷冷地看着我。我深知一些小小的疏漏会毁掉宏大的工程,可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我又能把他怎样呢?民说,武阿仁在故乡有个健康可爱的儿子,不知那孩子是否也是哑巴。
不知过了多少时日,一洞洞石窟、一尊尊佛像,在山崖上展现出来。那些深幽的石窟沿山势洞开,洞内佛尊结跏跌坐于莲花座上,恍若天国。
此日风冷,大雪将至。刚刚建成的石窟寺前,众石工静静地围成一团,齐齐地仰望着头顶之上的石窟,那空空的石窟正在期待着最后一尊让人仰之弥高的佛尊。忽而,一声炮响,八个身强体壮的石工用麻绳束住石佛的手脚,将四根木杠穿过麻绳,肩顶木杠,在一声高喝中将大佛拔地而起,缓缓向石窟寺攀去。众石工紧随而上,“哦哦”欢呼。我知道他们很快活——终于盼到大功告成就要回家了。可我的心却一阵一阵紧缩,就像那蒙在桑木架上的马皮,绷得就要裂开了。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待大佛稳稳入坐于石窟寺后,我开口说话了。我说滏口石窟是王朝伟大的工程,定能佑天下太平,必将炳耀千秋。我说这些话时,嗓子干涩,觉得自己的嘴就是空洞的石窟。
众石工鸦雀无声,一张张木讷的脸聚向我,他们在静静地等待,等待我发布解冻的消息。我拖延了许久却说:虽然石窟已成,但朝廷快马来报,王令我等再在石窟寺后凿一隐洞,只要隐洞完工,大家就可回家抱老婆了。
一时间,天上大块大块的云朵僵滞了。众石工石雕木刻般,似乎在酝酿阴云密布的风暴。坊间早就盛传我们的王将逝的消息,而王之死必然要营建盛大的陵寝,这滏口石窟岂非最佳的陵墓?而建造帝王陵寝的人必须死去。那些石工虽低贱但并不傻,已然有了不祥之感。
我心悸动,竟然生出从未有过的怯意,便环视岭上环伺的士卒。他们的戈矛宛若森林,让我的心落定下来。我的脸慢慢冻结,冷冷地扫视一张张石工的脸。这是一种无声的对峙,弥散起一触即发的气息。
大山静了下来,没有风声,连秋虫的低吟声都冻住了。忽地,一阵“呜啦呜啦”的叫嚷声传出,我闻声寻去,那是哑巴武阿仁在叫喊。他一脸悲愤,指手画脚,却不知在说什么。他的喊声如一石击水,瞬间就泛起了波澜。石工们愤然高呼:返乡!返乡!返乡!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站在巨大的云朵阴影下,缓缓举起一面黄色的令旗。这面小旗是王赋予我的权力,我一生曾无数次摇动它,摇得血流成河。我举着黄旗在空中连挫三下,高喊:闹事者,杀无赦——
石工们骚动起来,年壮的石工将年老体弱者护在中间,手拎着铁锤铁錾,与士卒们相持起来。我自信手下的兄弟对付苍头百姓还是绰绰有余的,但不希望发生哗变,于是恰如其分地高声说话了。
我说:逃跑者,死!反抗者,死!
石工们不屑,攥住铁器的手更有力了。
我又说:尔等一死则已,可株连九族大罪,家中妻儿老小必死!
石工们的手松了,铁器当啷落地,蹲下身去抱头号啕,呜咽声在山谷里卷起一阵风。
天色暗了下来,我模模糊糊地想:漫长的夜终于来了!
4
夜已深,我想我得去找洁了——她就是那个爱玩游戏的姑娘。
洁是青铜时代大酒店的服务生。我不知道她是哪儿人,她说她是将九个旅游区的名字写在纸团上,随手抓阄抓到岛上的,反正都是异地打工,去哪儿都无所谓。她看上去很快乐,一笑就会露出两颗牙齿,总穿着红旗袍穿梭在那幢被铜幕墙包住的灯红酒绿的大楼里——我更想看到她被红旗袍裹着的什么。我经常找她玩,应该不是因为思念,而是想跟她玩玩游戏。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和洁相识后,她曾在我们店里购买过铜羊,说是要把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远方的朋友,可我看见那只卷毛的生肖羊一直摆在她的宿舍窗台上。她沉迷于手机游戏,好奇心爆棚。我俩一见面就想着法儿玩游戏,有时蓄谋已久,有时一时兴起,玩得不亦悦乎。我们曾在午夜举着手电筒,满岛寻找野水鸭,可一只肥鸭也没找到;曾带着望远镜到观光塔上眺望星星,看见一颗流星落入湖里;曾在湖里插下标尺观察水位,发现了岛在下沉的秘密,但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个小铜匠和一个服务生才是北斗岛上真正的游客。
这天晚上,我和洁相约去环岛小火车玩儿。那时,小火车已经停开,泊在码头车站里。抱着啤酒箱的我和拎着卤鸭爪的她碰面了,相视而笑,翻过铜栏杆钻进绿皮车厢里。那列绿皮火车是从对岸小城搬过来的。据说小城是在矿山和工厂上长出来的,很多年前一群群人从四面八方聚来,在对岸采矿冶铜,于是一列列小火车装满矿石、铜锭和工人穿过火红的年代。可现在小城铜矿枯竭了,矿山纷纷倒闭,绿皮火车早已废弃,这才被搬到岛上成了环岛而行的观光车。我和洁坐在火车茶吧里,边喝啤酒边啃鸭爪,晕头晕脑地说着话儿。我们先是比赛说寓言童话,我说《皇帝的新装》,她说《狼外婆和小红帽》;我说《独眼大盗》,她说《海的女儿》;我说葫芦娃,她说喵星人,仿佛滑行在平行的铁轨上。当我表扬她可以做幼儿园老师时,我俩都醉了。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正如你所期待,两个酒醉的人总想趁着夜色做点什么。
于是,我用纸巾擦干净嘴,用抓鸭爪的方式抓住了她的手,含糊地说:我爱你!
她嘻嘻一笑,笑得像猫。
我拥起她,抚摸她。她整个身子软软地贴近我,闭着眼睛睫毛颤动,嘴里散发出绿箭牌口香糖的气味。我热血沸腾,身子硬起来,急切地剥去她身上的红旗袍。就在我雄赳赳的小鸟要进入她的巢时,一声钟鸣传来,那是钟楼里的大铜钟发出来的,在为午夜十二点准点报时。我的小鸟仿佛受到了惊吓一下子就软了。我不甘心,勤奋地抚摸她。她愣了愣,也抚摸起我,可我终究没有坚挺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我放弃了努力。我虽然如愿以偿地看清了她旗袍下的秘密,却无能为力了。
我茫然地呆坐着,羞愧地垂下头。她兀自扭着赤裸的身子在车厢里走动起来,像是T形台上的模特——不知是在向我挑衅,还是在自我欣赏。我不能不看她,被她身体的白折磨着,渐渐由羞而怒。当她再一次招招摇摇走近时,我猛地站起,把她推倒在茶几上。她背对着我,兴奋地扭头看我。车厢墙上挂着的红色灭火筒晃了晃,我不管不顾,从裤袋里掏出一个铁印戳,哈了口热气,狠狠地盖在她的臀上。她惊叫一声,揉揉屁股逃开了。那个铁印戳是师傅的,那老头每铸好一件铜工艺品,无论铜奔马还是铜香炉,都要在上面烙下印记——那是物勒工名的行规,就是工匠要在自己打制的物件上烙上自己的名号。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游戏:我和洁穿好衣物,打开车窗向外看去。码头上有个游客也喝醉了,他摇晃着身子,举着白酒瓶,哦哦地喊叫着,像是在跟月亮干杯——游客中难免会有酒鬼的。
洁摸摸我的头柔声说:你莫要懊恼……也许喝了太多的酒,也许是场合不对,换个地儿你就能行……你怎么可能不是男人呢?
我眺向远处的铜神广场,目光恨恨地掠过钟鼓楼——为什么我总是被声音坏了事呢?
……
(本文为节选,全文见《延河》2022年第4期)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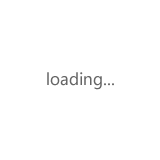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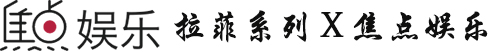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