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平台|错过
时间: 2023-06-10 03:07
浏览次数:
焦点注册报道: 我的姥姥是小脚。她缠足的时候已经快民国了。可生在穷乡僻壤的她仍没能逃过此劫。“你可不知道姥姥遭得那个罪啊!”姥姥对我说起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疼死我
焦点注册报道:
我的姥姥是小脚。她缠足的时候已经快民国了。可生在穷乡僻壤的她仍没能逃过此劫。“你可不知道姥姥遭得那个罪啊!”姥姥对我说起的时候仍然心有余悸。“疼死我了,疼得我直冒汗,成夜成夜的睡不着觉。不敢动。可上厕所的时候不行,得走过去。我就扶着墙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每挪一步我都疼得直哆嗦,脚像踩在插在火里的刀上似的。
姥姥的小脚注定她不能到田里做繁重的农活,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坐在家里享福。除了烧水做饭洗衣外,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纺线织布,做衣服做鞋。“你姥爷干活可真不惜力气。我给他做的褂子,不出俩月就被汗沤烂了。鞋啊,不到一个月就踩坏一双。我把鞋底弄得厚厚的,纳得密密的,可还是撑不过一个月。
姥姥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姥爷的,入洞房之前,他们只见过一面。我见过一张姥爷穿着马褂带着瓜皮帽的年轻时候的照片,那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奢华的装束,一米八几的个头,膀大腰圆的,倒也气宇轩昂。可他临死前在北京治病期间照的几张相片都是一副瘦骨嶙峋,饱经风霜的老农样儿。姥爷是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病死的,我对他全无印象。爸妈有时会争论姥爷在我家暂住的时候是否抱过我,但姥姥对我说“你姥爷可喜欢你了,他临死的时候躺在炕上,一叠声儿地问‘兴子来了没有,兴子来了没有,我老看见他对着我笑呢。’”姥爷没能看我一眼就归了西。因为经济拮据,我母亲兄妹几个只派了一个代表回去料理后事。我不知道姥姥说这话是为了让我高兴还是实有其事,但她的话突然间让那个照片上干扁的土得掉渣的老头鲜活了起来,有了血肉和温度,让我感触到血缘的纽带。被人牵挂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我扭过头去假装挠我的小腿肚子,不想让姥姥看到眼里泛起的泪花。
姥姥一共生了九个孩子,但只活下来四个。她讲起活到八岁才病死的二女儿,她的乖巧和懂事,虽然过去了五十多年,仍然掏出手绢擦眼泪。五个孩子死于非命,我不知几十年来她是如何应对的。但除了偶尔提起,她好像很少有抑郁的症状。姥姥没多少事儿可以做,所以家务活干得细致而又投入:她衣服叠得方方正正,每道折痕都用指甲卡过,平平整整的就象刚买回来的一样。她肉切得极薄且均匀,这样每个人都能吃到几片儿。实在找不出事儿做,她就趴在窗台上看来来往往的行人。那时候电视还不是全天都有节目,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她其实是很寂寞的。她时常会捧着报纸看上面的照片儿。有一次她对我说“我要是认字儿就好了,看看报纸也能解解闷儿。
姥姥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动荡,战乱和政权的更迭,民国,北伐,国共分裂,日本占领,内战,以及建国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历次运动和变迁。她讲起和小鬼子的遭遇平静而淡定。“小日本儿来的时候我让你姥爷拉着牲口带着孩子和家里值钱的东西逃到山里去了。”“你没逃到山里去?”我吃惊的问。
“都走了,家交给谁?”她不解地反问我,好像我的问题很奇怪。
“那小日本儿到咱们家来了?”
“来了。”
“他们干什么了”我的眼睛都瞪圆了。
“没干什么,看了看就走了。”
“他们没打你?”我觉得不可思议。
“我又没招他,他打我做什么?”姥姥一脸严肃地说。有时闲谈的时候她会突然漏出一两句让我吃惊的话,可如果我追问细节,她会推托说年代久远,记不清了。我想她其实是记得的,只是不想告诉我而已,那漏出的支言半语好像大多关乎生死,闪着残忍的寒光。大跃进的时候,家里所有的铁器都交公炼钢,全村人都去大食堂吃饭。姥爷病在床上,姥姥小脚跑不快,等赶到食堂,所有的吃的都被抢光了。“我就和邻居商议,到开饭的时候我帮她看孩子,她跑去食堂把她家和咱家的饭都打回来。亏得她是个好心人,要不然我和你姥爷等不到三年自然灾害就都饿死了。”
姥姥说话很轻柔,做事也是轻手轻脚的,家里有她没她,区别好像不大。她默默地做这做那,我们则毫无心肝的坐享其成,很少想是谁提供的方便。她很少发表意见,也从不抱怨什么,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就像忍受几十年大起大落的世事揉搓一样默默地应对生活的油盐酱醋。从来没听她说想吃点儿这个或那个,给她她就吃,没有她绝不会要。她从没说想买件这个或添件那个,儿女给的她都欣然接受,儿女想不到的,她会用家里的旧衣碎布做一个。她很少生病,或者说只要能扛过去的病,她都不让我们知道。因为是小脚,走不了多少道,我们去玩儿的时候常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可她送我们走迎我们回,就像接送我们上下班一样没有任何不乐意。
有一次家里一个买东西用的布袋子坏了,姥姥把两个当提手用的塑料环拆下来,她把其中一个套在手腕上,摇晃着说“瞧,像个大手镯子。”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儿,眼睛亮亮的,像孩子刚得到了新玩具。
“你以前也带过镯子?”我问她。
“带过啊,我出嫁的时候我爸爸给了我一根铜簪子,一对铜耳环,还有一对镀银的铜手镯。”
“过门儿以后没再添新首饰?”
“饭都吃不饱,哪有钱添首饰。”
“那些首饰还在吗?”
“没有了,破四旧的时候给收走了。”
“谁收走的?”
“村长带着民兵来,说这些都是四旧,要交出来,就都给他们了。”她依然盯着那个在手腕上摇荡的塑料环,女人对首饰天生喜爱的表露让我心里轻轻一动。
“我以后给你买对镯子吧。”我说。
姥姥说不要,说你哪有那个闲钱。我说花不了多少钱。几天前我在美术馆看展览的时候,看到那里的一对银手镯,记得标价是三十二块钱。姥姥说你又不挣钱,哪来的钱。我说等我工作了不就有钱了。姥姥没再说什么,停了好一会儿,突然轻声问“你真的能给我买对镯子?”然后嘟囔了一句“那我就等着跟我孙子享福了。”
那是我上高中时候的事儿,自那以后我和姥姥谁都没再提起。几年后我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刚开始工资没有多少,而我又有那么多买这买那的计划,虽然我还记得我的承诺,可那时候一对银镯子已绝非三十二块钱可以买得到。先等等吧,我给自己找借口,等以后钱多了再给姥姥买个好的。只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带着镯子的手的特写。姥姥说,瞧那大金镯子,这些人可真有钱。我不知姥姥只是随口一说,还是想提醒我曾经许下的承诺。它的确让我想到了我的承诺,可我坐在旁边,没吭声。
姥姥是在我工作后刚过一年的时候去世的。死得前一天,还吃了红烧带鱼,食欲很好。第二天中午姨父回家,发现她歪躺在洗手池子边上,已经没了呼吸。洗手池子上架着一个脸盆,脸盆里盛着半盆子血—姥姥死于消化道大出血。我们后来试图还原当时的情形:姥姥觉得嘴里涌上来东西,就到洗手池子吐了出来。她看见吐出来的是血,就打开水龙头把血冲走,然后擦了擦滴在池沿儿上的血。因为池子里和池沿儿上都留有淡淡的血迹,池沿儿上还有擦过的痕迹。姥姥然后拿了一个脸盆接着随后涌上来的血,那血真实汹涌澎湃,一口接一口,不一会儿就有半脸盆。等到血都吐完了,过多的失血让她觉得晕眩,她瘫坐在地上,背靠着墙,就这么慢慢地,慢慢地去了。除了嘴角,棉袄和棉裤上的几滴血外,所有的血都在脸盆里,屋子里干干净净的,姨父说。
姥姥的死横刀斩断了我和一个时代的联系,那是一个女人要被缠足折磨一生的时代。姥姥的死也让我的承诺没有了兑现的可能。我不知道姥姥是否一直想着我承诺的那对镯子,但是与不是都无法让我逃避自责和为自己的自私感到羞愧。一对镯子会不会给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带来些快乐和满足?当她独自在家的时候,会不会晃荡着手腕把玩那对镯子?我能想象她那因喜悦而发亮的眼睛和脸上花儿一般满足的笑容。可错过了,就不会在来!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镯子的时候,心里都会隐隐的痛一下。多想那双手还健在,能让我为它们套上一对镯子,然后抬眼看那心满意足的慈祥的笑脸。
下一篇:焦点注册|一个故事,一台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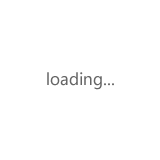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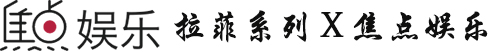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