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快讯:
编按
这篇小说似乎简单如题,一次相见。没有更多。只知道穆老师是文化名家,有抑郁症和自杀倾向,因果没有提及,包括他的所谓“处境”,留白大片。“我”的情况也省略了很多。作品始终是平淡叙述和闲散笔调,类似于民国散文风,对话也像古代人物画的撅头丁、曹衣描之类。有着一种介于可及和不可及之间的叙述状态。作家制造出来的想象空间,才是小说的独特味道。
四年前,徐畅在《野草》发的第一篇小说叫《苍白的心》,这篇《一次相见》的内质可能胜过一筹,效果是另一个问题。小说开头“我”提了个问题:人应该依靠什么去活着?这是所有人的困惑。短短六千字的小说透显着哲学意味,当下环境的信仰困惑,以及人事并不相通的悲欢和不确定性。这是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万物皆有来路和去向。开头“我”在办公室阳台上点的那把火,被匆忙踩灭,最后有了一个小说意义上的交待,也是回复开头的一种释然。花盆里那棵自然生长的桑树也有着一种哲学层面的指认。(朝潮)
一次相见
徐畅
一
寒风刮了一整夜。天空昏朦,几朵冷云聚在一起透不出一点光。往楼下望去,繁茂的银杏叶在一夜间落尽了。粗壮的树干上只剩下光秃秃的干枝。我打了个哆嗦,压抑着的情绪涌上心头。
我关上玻璃门,回到屋里。昏暗中,六个月大的婴孩正在妻子的怀里熟睡。走进厨房,倒了一杯白酒,我仰起头一口喝了下去,脸上火辣辣的。我走进卫生间,用冷水洗了把脸。抬起头时,我看到镜子里的那个人:他留着一头短发,一双小眼睛躲在硕大的眼镜身后。他三十多岁了,下巴上仍保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他不想留几根胡须遮住这股稚气,反而觉得稚气是他向往意气的一种证明。焦点娱乐
到了上班时间,我步行走进地铁。在车厢里找到站立的空间,那股酒气冲上头来。我抓紧冰凉的扶手,一个念头冒出来:人应该依靠什么去活着?感到一阵失落,我浑身燥热,用手背擦了一下额头。放下手时,手背上一大片汗水。
慢悠悠走进办公室,屋里昏暗不见一个人。我走到屋子尽头打开窗户。一阵冷风吹进来,身体凉爽了。我走到阳台上,点着一根烟。早上的那股的情绪又涌上来。看到墙角边爬山虎的枯片堆,我蹲下身子,将烟头缓缓伸进去。不一会,白烟带着刺鼻的焦味飘出来。一片叶子点着了,火苗顺势咬住了其他叶子。一时间,一团大火扑棱棱地冒出来。我惊讶地往后退了两步。这时,一位同事走进办公室。我慌慌张张地朝火苗踩了几脚。
我今天是怎么了?早上喝酒,又无缘无故点了一把火。回屋的那个刹那,我突然想到,今天的反常或许跟要见的那个人有关。焦点娱乐
昨晚临睡前,手机上蓦地跳出一条信息:明天我们还是见一面吧?迟疑的话语里透露着一丝坚定。他又发来一句:如果不妨碍你的话。他说这样的话,是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我回复说,可以的。不过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雨。
穆老师说,没有雨就见。有雨就不见。我本来也是来办事顺道见见你。我笑了笑,穆老师从来不说客套话。
约定好时间,我盖上被子躺下了。迷瞪中,我听到手机又响了一下。信息上写着:你有可能……算了,你已经睡了吧?我翻过身回复道,还没呢。
我有些受不了。跑了附近几个药房,也没有买到。这次出门有点急。他说。
买什么药?我问。
你知道哪里卖帕罗西汀吗?他说。我从没听说过这款药。我去网上查了查,发现这是一种抗抑郁的药物。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楼下的连锁药房应该关门了。
你急着用吗?我问。
有会更好。没有也能忍着。他回复说。
可以网上买的。不过得明天一早才能送到。我说。
那些软件,我搞不来的。他说。
我要来他的地址,帮他买药。看到他的地址,我感到诧异。那是在郊区的一家青年旅社。我有些疑惑,又不好多问。
在软件上找到了那款药,我问,买两盒?
买五盒吧。他说。
买这么多?我问。
吃着吃着就没了。他回复,并在话语后面加了一个笑脸。焦点娱乐
我心底里冷了一下。他对药物的依赖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了。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的?我想到他的模样,想到他说话时的神情。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不断浮现在眼前。
二
说起来,我跟穆老师的交往是从一次公务开始的。
二〇一五年的夏天,我为了编一套书系,跟领导跑了一趟顺城。当时,社里组织了一场阅读活动,邀约了许多名家,穆老师也是其中之一。
我头一次见他时,他穿着天蓝色牛仔裤,裹着一件棕色皮夹克。夹克两边的口袋鼓鼓的,仿佛随时能拿出一个笔记本或者一支钢笔。他有一头又长又黑的头发。
活动现场,人们围绕主题小心翼翼地寻找着话题。等话筒到了穆老师那里,他轻声说,大家怎么都不说话?我们又不来学习的。台上台下哈哈笑起来。在逐渐热闹起来的气氛中,穆老师讲起早年的求学经历,又从翻译小说讲到托尔斯泰和穆齐尔。接着,一口气从巴门尼德讲到“唯理论”。形而上学发展历程中的种种特征如同他手心里的玩物。活动越到后面,越成了他的独角戏。主持人在一旁,只会附和着:是是,对对。
活动过后,照例有一顿晚饭。嘉宾和主办方都到场了,却迟迟不见穆老师的身影。与我同去的钱主任说,这回穆老师救场了,他必须到。我一个箭步冲出去,在马路上寻找穆老师。寻找无果后,我只好拨通名单上的电话。电话响了两通,对方才接。我说明原委,对方冷冷地说,吃着、喝着,有什么意思啊?我愣住了。他笑笑说,我是说,我不适应那种场合。而且……我把手机贴紧耳朵。他说,而且,我要照顾家里。焦点娱乐
回到酒桌上,我把此事告诉了钱主任。旁边研究民俗的刘老师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女诗人搓着手掌说,他是一个怪人。她的话语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她又说,他母亲和妻子都病着,他家里都照顾不过来,却偏偏将小孩送出国。
他这是心高。刘老师附和道。女诗人摆摆手说,那倒说不准。他跟我们想得不一样。她用胳膊在桌上画了一个大圈,想把所有人包含进去。
过了一年,因为书展的事,我跟钱主任又跑了一趟顺城。
活动结束后,我们意外地接到穆老师的邀请。他说,他想约我们去海边看看。顺城虽然靠海,但是到海边也要三个小时车程。我有些迟疑了。我问了问钱主任。钱主任想了想说,去吧,该忙的都忙完了。
翌日下午,我们坐上了穆老师的车。跟上次不同,这一次他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
上路后,他双手握着方向盘说,我的驾照已经扣了十二分,但愿我们不会被警察拦下来。我以为他在讲笑话,可是等上路后,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在一个右转路口,他紧张地打了左转灯。我跟钱主任面面相觑。钱主任说,要不我来开?穆老师自信地摇摇头说,不用不用,这里的路,我很熟的。可是开了半个小时,车停在一处没有人烟的泥路上。焦点娱乐
借助导航,我们来到一片乱石丛生的滩涂边。目及处的海面浑浊,散发一股浓烈的海腥气。钱主任说,要不是导航说这是海,我还以为是江边呢。她拍了拍包说,我还特意在市里买了件泳衣。
穆老师摇摇头,丝毫不理会钱主任的心意。他充满激情地说,海滨的海,只是休闲的海。不是海的本色。你看这浪,又高又浑,把鱼、虾、贝类和泥沙都给搅进去。这才是真实的大海。说着,他爬上一块大石,朝着头顶举起拳头。我用手机给他照了一张相。照片中,穆老师的身型只有黑白的轮廓。一只胳膊徒劳地朝天空使着劲儿。
回程的路上,经过一棵巨大的榕树,穆老师猛地刹住车。他回头竖起食指说,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吃。在大榕树下,吃上一桌热乎菜,这感觉才最好。在榕树茂密的气根旁,我们找到一张四方桌。穆老师拿过菜单,用指头在菜品上寻找良久。他问,你们胃口如何?一顿能吃多少?钱主任捂着嘴笑了笑。我感觉受到了冒犯,低着头没有回答。穆老师像是感觉到空气中的尴尬,扶了扶眼镜说,我就是怕浪费了。
钱主任到底是见过世面的。她说,不麻烦穆老师,我们出差都可以报销的。穆老师皱起了眉头。他抹起袖子说,那不行。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我看了看钱主任。钱主任朝我耸了耸肩。焦点娱乐
一碟油炸鱼皮、一盘火爆蛏子和一碗西红柿炒鸡蛋端上来。穆老师进屋要了一张发票。他将发票推给我们。钱主任愣住了,我也不知所措。穆老师说,你们拿回去,就当……那句客套话憋得他脸上发红。他夹了一块炸鱼皮说,就是我一点心意。见我们收下了,他脸上的神情才舒展开来。
回到城里,天还没有完全黑。穆老师提议,再找个地方坐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他破费。钱主任脸上面露难色。穆老师说,要么就去我工作室坐坐吧?说着,他爽朗地大笑起来。我丝毫不知他为何大笑。等过了二十分钟,来到他的工作室,我也大笑起来。他所谓的工作室其实只有五平方米。原本是学校里的一个扫把间。屋里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值得一说的是墙上挂着的牌匾,上面写着两个粗狂的毛笔字:枕流。我嘴里念叨着,好像在哪里见过。钱主任说,漱石枕流嘛。我这才想起日本那位曾印在钞票上的大文学家。
我堆起两摞书,当作两张凳子。坐下后,穆老师泡了一壶大红袍。我们就着苦涩的茶味,闲聊到深夜。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穆老师。
我心想,他就是这样一个安心于书斋的人。可是不承想,从去年春天开始,他的坏消息时不时地传来。起初,有流言说他因言论遭到学校处分。后又传出消息说,他在某次会议上做了出格的事。而这出格的事,仅仅是因为别人举手赞成,而他举起的是拳头。过了一阵子,又传出他遭到当地报刊除名的事。他往日的好友,没有一个站出来。出事之后,他的朋友圈经常发一张黑色的图片。到后来,黑色的图也不发了,仿佛这个人就此消失了。焦点娱乐
三
午后两点多点钟的样子,外面下起了雨。没听到任何闪雷,只见大风带着雨朝白墙撞去。墙壁湿透,方砖地上积了一层水。我心想,下这么大的雨,他不过来了吧?我觉得有些遗憾,不过压在胸口的那块大石悄悄搁下了。
坐到下班时间,黑色座机响起来。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我匆匆跑下楼去,看到隔开雨幕的门廊底下站着一个人。那个人拎着棕色皮包,身上穿着一件灰色毛衣。他的脸庞有些浮肿,可这浮肿似乎跟肥胖无关,更像是长期服药的结果。原来蓬松的黑发,如今夹杂着许多白发显得干枯。走近后,我发现他下巴上竟也长出了白胡茬。
没有任何寒暄。穆老师带我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爬上二楼时,头顶安装一排射灯。穆老师的眼睛碰到强光,用力地扭向另一边。等爬完木楼梯,我看到他的眼睛有些发红。焦点娱乐
落座后,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说过的话是错的。我在课堂上讲课,总能听到耳边有个声音在反对我。他告诉我,我讲的都是错的。你知道康德的二律背反吗?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每当有了一个观念,就意识到它是对另一个观念的遮蔽。如此反复下去。
焦点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我望着桌面。桌上放着一只方口长身的小瓷瓶,瓷瓶里插着一小朵火红的康乃馨。花蕊皱缩在一起,周围有几片败花。
这就很像卡夫卡。他说,在卡夫卡那里,确定的观念都会被淘汰。世界是破碎的,是不确定的。你看,他的写作和人生都支离破碎。
服务生走过来。我点了一杯美式。穆老师随口说,跟你的一样就行。服务生走后,穆老师看着我说,有时候,我觉得人文教育是有局限的。它远没有宗教有力量。因为不管什么环境下,宗教有自己一套体系,能撼动它的力量是比较少见的。
我点了点,想到早上那阵痛苦。我说,像我们这样长大的人,很难有什么信仰。有信仰,人生更有着落。但它是有前提的……穆老师笑了笑,没有接我的话,而是质疑道:信仰是不能用利益来衡量的。如果用利益来衡量,人在选择信仰的时候,就自行下了赌注。
这跟赌博是一回事吗?我问。
性质是差不多的。要是抓了一手烂牌,我一分钱也不愿意押。如果是一把同花顺,我则会压上所有的钱。但是信仰的不同点在于,不管你押了哪一项,你都得拿起双手,而你向桌子中央押注的是整个人生。焦点娱乐
那我可以不选择吗?我说。
当然不可以。因为你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说。你不选择,你的人生也交付了出去。不过,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可以回避它。
怎么说呢?我问。我表现得有些迫切。
就像海德格尔讲的,人应该活在现世。人要去存在,去“成为”。
两杯美式端上来,白瓷杯里黑黢黢的。我琢磨着他的话,抿了一口咖啡。想到地铁上突如其来的紧张,内心踏实起来。
你家人都好吧?过了一会,想到他的遭遇,我问。
我孩子大了,也不用我去管他。他说。
那你还好吧?我问。
我现在每天都想打自己耳光。他突然说。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朝窗外望了一会,回过神来,又盯着那朵康乃馨。
其实,我的遭遇没什么可说的。你知道二战时的那张照片吧?他问。
什么照片?我问。
就是很多士兵站在那里敬礼,唯独一个人坐在原地,双手抱在怀里。他说。
我想起那张照片。
有时候,坐下是最难的。穆老师笑着说。
这有什么意味吗?我问。
有什么意味呢?他说,原来有意味的东西,现在也没有意味了。
你又没做什么。没有人替你说话吗?我说。他叹了一口气,有些不耐烦地说,鲁迅就说过的呀,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望向窗外,路上的车辆拥堵在一起,路边的伙计正利索地刷着木桶,行人们顶着伞在雨幕里穿行。跟屋里的气氛相比,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生机。焦点娱乐
我托人买过药。过了良久,穆老师开口说。
说话时,他看了我一眼,又将眼神移向别处。
治病的药吗?我问。
不是,是自杀的药。他说,我试了一次。结果剂量不对。第二天,我又醒了过来。
我惊讶地扶住了桌面。我望着他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前不久吧。他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皱起眉头。身体从脖子到脚踝打了个寒战。你还有家人。我心里想,但是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必定考虑过这个问题。看到他憔悴的神情,我心底里大胆起来。我想到了太宰治。我追问道:你后来还试过吧?
还试过一次。药一停的时候,我就有这念头。他说。
我想到昨天晚上的事,背脊上出了热汗。我想劝慰他,又觉得劝慰是徒劳的。一个旁观者说的话,他不会去听。我感到懊恼,意气用事般从书本里寻找说法。我说,尼采不是崇尚生命吗?他的思想对你没有启发吗?
见我有些着急,穆老师说,你跟我讲尼采,前提就错了。
我看着他。
那是对活人有用的哲学。他说。
对我这样一个死人而言,那就只是一些理论。他又说。
死人……我身体凉了一下。我想到故去的亲人,想到许多跟死有关的事情。在那一瞬间,在记忆的最深处,我蓦地想起少年时期的一个夏天。那个傍晚,我回家路上看到乡镇医院一片空地上围着许多人。我挤进去,看到碎石地上有一个婴儿。它裹着一件带血渍的床单,手脚还在动,不时传出轻微的啼哭声。旁边的人说,他还能活,他还有温度。另一个人说,他活不了。我转到一侧,看到婴孩的后脑上长着硕大的脓包。当天晚上,我躲在床单里感到万分的恐惧。那是什么?那就是死。与生同时降临的,那就是死。死不是未来的事。焦点娱乐
我隐藏起内心的波澜。眼前划过一个模糊又让人怜爱的面孔。
总归还有办法。我说。
总归?总归……他激动起来。这时,他猛烈地咳嗽,脸上顿时通红。他抓起一张餐巾纸,擦了一下嘴角。他深吸一口气,想要缓解突如其来的咳嗽,但是胸口的气流不停地打结。他咳嗽得耳廓都发红了。他扶着桌子站起身,从咳嗽的间歇里挤出一句话:我去个卫生间。
他急促地走下楼。咳嗽声渐行渐远。
等了一刻多钟,还没见他上来。我看时间不早了,于是走到收银台前买单。服务生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刚才那位在店里押了一百块钱。我问,什么时候的事?他说,你们来之前。他就押好了。服务生递给我一沓钞票说,这是五十六块钱。麻烦你带给他。
我在一楼等到了穆老师。他从卫生间里出来,脸上苍白。这是怎么了?我心想。他生了什么重病吗?他清了清喉咙说,我要回去休息了。焦点娱乐
你没事吧?我扶着他的肩膀。
没事。他说。现在我还能坚持。
我递给他零钱。他愣了一会,接到手里,卷成一团揣进兜里。
四
走进办公室,同事都下班了。我走到阳台上抽烟。阳台上的大花盆里长着一株桑树,枝头卷着的新叶正在缓缓舒展。这里怎么会有桑树呢?我想没有人会把桑树种在花盆里。看到屋顶的斑鸠,我心想,大概是鸟带来的。鸟吃了桑树的种子,又将粪便落在了花盆里。桑树就是这么来的。它或许来自郊区的一片旷野,也可能是南方哪个县城。我想到穆老师的话,世界是不确定的。我大脑清醒过来,咖啡馆里发生的事一下子澄明起来。
我掏出一根玉溪,摁打火机时,一阵大风吹过来,爬山虎的叶子往墙边飞走。我的目光跟着叶子,看到早上那片烟灰。如今,它被风吹散了,乱成一团。我走过去,用脚拨了拨,灰烬中露出一根还在焖烧的树枝。树枝的一多半已经成了黑炭,只剩一点还在燃烧。在风力的作用下,它烧出了火苗,紧跟着又被扑灭了。我捡起那根木炭,借着一丁点的火星点着了纸烟。
抽完一根烟,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那块木炭凉透了。我带着它回到屋里。心想,说不定,它可以做成摆件或是当个笔托呢。焦点娱乐
【作者简介:徐畅,江苏人,现居上海。曾在喜马拉雅山脉游历。作品发表于《收获》《江南》《野草》等。有小说集《鱼处于陆》。】
焦点: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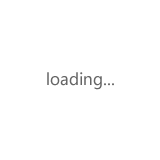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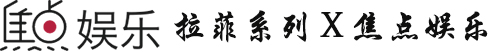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