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网快讯:

马 拉,197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重要选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余零图残卷》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广州美人》等三部,诗集《安静的先生》。
难以想象,再次回到这个地方是为了作一次演讲。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十八岁,刚刚懂得整理发型的必要性。那时,他的头发刺猬一样挺立着,还没有学会服从梳子和发胶的指令。他想梳一个时髦的三七分,大街上时尚的年轻人都留着那种发型,还穿着喇叭裤。夜市的大排档发达起来了,总会有人喝醉。路灯昏暗,似乎电力不足,每个转角处都有一个垃圾堆,堆满果皮、塑料瓶、食物残渣等等废物,它们散发着统一的恶心气味。那种气味没有国界,没有性别,它们有着统一而均匀的垃圾气息,和他在巴黎、新德里、加尔各答的垃圾堆旁闻到的味道一模一样。几乎每个年轻人,都在垃圾堆旁呕吐过,那是美妙的青春课堂。有时,他们独自呕吐,对着垃圾堆,把酒和刚刚吃下的烤土豆、烤肉、烤茄子烤韭菜统统吐个干净。有时,有人扶着他们呕吐,他们被人架着胳膊,把那些东西吐到自己的裤子上,鞋子上。最好的是被女孩子扶着,等你吐完,对女孩子说几句伤感的柔情的话。如果她的眼睛柔和起来,你不妨把你的手大胆地架到她们的肩膀上,或者搭在平时想搭又不敢搭的腰上。那么柔软的腰肢,是最好的醒酒汤。如果是女孩子喝醉了,她们通常喜欢蹲在地上呕吐,头发垂下来,几乎要掉到地上。要是你还没有喝醉,你可以蹲下来,拍拍她的背,摸摸她的头,给她递张纸巾。女孩子喝醉了容易哭,如果她哭,就让她哭吧。找个合适的机会,把她抱在怀里,谁都这么干过,谁都不说,一层薄纱,遮住的不仅是羞耻,还有难以言喻的内心秘密。焦点平台
他这么干过。那年,他十八岁。他把手伸向那个女孩时,女孩突然挺直了身体,从容地站了起来。这让他大惊失色。女孩对他说,其实我没有喝醉,我不是想你来扶我。女孩说,你表哥,他是个混蛋。他想对女孩说点什么又不知该说什么。女孩说,你别说了,我比你大几岁,你说的我都懂。他们靠在墙边,垃圾堆毫不疲倦地散发着气味。女孩说,我们回去吧,他们还没散。从垃圾堆到酒桌,大约三十米,就在垃圾堆旁边,有一条小巷,黑漆漆的,路灯的光斜切在墙上,没有光照到的地方漆黑一团。路过巷子,女孩拉住他的手,钻进巷子里。他们往巷子里面走了十几米,黑乎乎的,只看到模糊的砖墙。他的心跳得厉害,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女孩拉着他,站在墙边,尽管她比他大三岁,个头却只到他的眼睛处。女孩问他,你喜欢我?他的脸在黑暗中红了。女孩又问,你刚才是不是故意的?他的脸更热了。你的手在抖。女孩说,你害怕?他想再次把手抬起来,抱住她。女孩反手伸到背后,他像是听到什么声音。女孩又把手伸了过来,在他手上摸了摸,你还是个孩子呢。她说话的样子好像他的母亲。那时,她才二十一岁,太年轻了。他忍不住回想。他把手伸出来,五十三岁,他的手远比同龄人的手要细腻,他再也没有摸过那么好的东西。他忍不住用力握了握她的手,他的手心和她的皮肤上都是汗。从巷子里出来,他像是要虚脱了。他突然厌倦了这个城市,这个巴掌大的县城。夏天的蝙蝠忙碌地飞舞,光线中时时划过几近透明的飞虫。他和她都在用力地喝酒。很快,她喝醉了,再次离开桌子。他站了起来。一只手压住了他,我去吧,你喝多了。表哥扶着她回来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他突然想,我得离开这儿。焦点平台
这些年,他多次接到家乡的邀请,想请他回去看看。三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尽管,他多次在梦中回到过那个地方。草枯之后的田野,结冰的河流,春天刚刚抽芽的柳树,还有山野之间的野花,他熟悉那些气味。他有一群乡下亲戚,几乎每个暑假,他都在乡下度过。他的父亲进城之后,娶了同样来自乡下的媳妇。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纯粹的乡下人。父亲的婚姻,他懒得评价。他见过父亲和母亲吵架。据说,父亲爱上了供销社的同事,那是个在县城长大的姑娘。父亲爱上了她身上的城市气味。他见到那个姑娘时,她已经不再年轻,长得也并不漂亮。他猜想,父亲爱的也许是“城市”。至于母亲,他和她在电影院有过尴尬的偶遇。他讨厌那个县城,无所不在的压抑气息,又带着莫名的自大和野蛮生长的力量。和父母团聚,他会邀请父母过来,给他们买机票。对北方的寒冷,他们先是心存恐惧,享受过北方的暖气后,他们开始觉得南方才是真的冷。南方那种冷,你知道的,你小时候经常冻得手脚生疮。整个脚后跟,冻得都肿了,多大的鞋子都穿不上,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摸起来水汪汪的,像熟透了的柿子。他们穿着单薄的外套涮羊肉,屋外下着鹅毛般的雪。那是冬天,他们团聚的日子。他和父母能说的话很少,彼此都习惯了。偶尔,父亲会和他说一句,毕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哪里有那么大的仇恨,再说了,也没有人得罪你。父亲希望他回家看看,有一个功成名就的儿子,却从不回家看看,如衣锦夜行,没有了意义。他当然理解父亲的心思。进入五十岁,他慢慢有了松动,他有了怀乡感,或者说乡愁。这真是莫名其妙,他以前拼命拒绝的东西,不容拒绝地进入他的头脑,发动一次又一次冲击,他发现,他其实早已败下阵来,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当他再一次接到家乡的邀请,他的语气松动下来。湛慕水在电话里对他说,丁老师,您就当散散心,关心一下海城的晚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您不知道,梁总批评我几次了,说我工作不力,连邀请您回来看看都搞不定。兄弟我还想进步,梁总老是批评,那我这进步就是水中望月了。您就当帮兄弟我一个忙,好不好?他说,我想想。一听这话,湛慕水大喜,以前他从来没这么说过。都是说,湛部长的好意我心领了,就不打扰了。湛慕水赶紧说,丁老师,那就这么确定了,别的事情我来安排,凑您的时间。丁非民说,我也还没有确定。湛慕水说,丁老师,没事,我等你有空。放下电话,所有的记忆一下子涌到眼前。他想起了垃圾堆边的那个夜晚,还有巷子里湿漉漉的气味。县城瞬间鲜活起来。接下来几天,他时不时看看手机。他这才意识到,他在等湛慕水的电话,他其实已经在期待他的还乡之旅了。焦点平台
丁非民选在春天还乡,早春。一出机场大厅,他看到了湛慕水,矮矮胖胖的,戴着眼镜,脖子上还缠着一条火红的围巾。他和湛慕水认识多年了。第一次见面,还是在他家里。他的新书《岗村外史》刚刚获得一个重要奖项,英文版也由白鹅出版集团推向世界,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国内掀起了阅读狂潮。很多年了,终于又出现了这么一本现象级的文学巨著,评论家和读者都为此激动不已。那段时间,丁非民害怕出门,他拒绝了二十多所大学的邀请。强烈的荒谬感包围着他,什么时候他像个娱乐明星了?他收到了不计其数的读者来信,甚至还有不少女读者在信中向他表达爱慕之情,并随信寄来照片。那些照片,丁非民空闲时细细看过,那些年轻的身姿真是漂亮,健康放肆,爆发着那个年龄特有的热情,美得让人落泪。他想起了一句诗“她身上的泉水都是寂寞的”,他理解那种寂寞,却也不想要不合时宜的欢乐。他把照片都收藏了起来,放在书房的高处,装在一个发黄的牛皮纸档案袋里。每隔几个月,他会打开看看,或者添加新的照片。焦点平台
他还记得湛慕水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小心翼翼,像是怕说错了话。湛慕水坐在沙发上,双手放在腿上,坐立不安的样子。那时,湛慕水也还瘦。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次,他和湛慕水只说了几句话,打招呼的客套话,他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后来,他和湛慕水的联系慢慢多了起来,从业务上的联系变成朋友之间的交流。丁非民知道的海城消息,多半来自湛慕水。认识快十年了,湛慕水多次邀请丁非民回家看看。他甚至问过丁非民,家乡到底给了您什么不好的回忆,让您不想回家?他说,丁老师,您的书我都读了,我看不出来家乡对您有什么伤害。丁非民说,没有,我只是情感上有些抗拒。接到丁非民,湛慕水给了他一个拥抱,我们终于在家乡的土地上相聚了。湛慕水这句话说得煽情,奇怪,竟也激起了他游子归乡的情绪。接过丁非民的行李,湛慕水说,本来梁总要亲自来,但市里临时通知开会,梁总实在不好请假,就委托我来接您。再说,我们俩不也熟嘛,路上好说说话。丁非民说,没事没事,挺好的,麻烦了。湛慕水说,丁老师,您这就见外了,您是海城的骄傲,海城几百年才出您这么一个大文人大作家,能接待您,那是我们的荣幸。上了车,丁非民和湛慕水坐在后排聊天。聊了几句,湛慕水电话响了,一看号码,湛慕水挺直了身体,响亮地叫了声,梁总好,接着,一阵“嗯嗯啊啊”。放下电话,湛慕水说,丁老师,刚才梁总指示,一定要把您招待好。丁非民说,这就太打扰了,真是不好意思。湛慕水说,都是自家人,不说外人话。梁总说了,这几天我就交代给您了,您有什么需求,尽管开口。丁非民说,也不用那么麻烦,随意转转就好了。湛慕水说,把该干的事儿干了,别的随您。丁非民笑了,你倒是记得清楚。湛慕水说,不敢不清楚,对您来说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事儿。来之前,湛慕水反复跟他强调,要作一次公开演讲,见几个人。这几个人不说,大家也能想到。丁非民说,行。基本的规矩,他懂,他也不是不通人情世故的人。湛慕水说,晚上梁总请吃饭,丁老师,这个不能不去啊,不然我没法交代,您就当帮帮我。丁非民说,你倒是会说话。湛慕水说,那也是丁老师体谅。对了,丁老师,我们是直接回酒店还是怎样?丁非民想了想说,时间还早,到江边转转吧。湛慕水说,您看,丁老师,您还是想那条江了吧?喝过这条江里的水,一辈子是这里的人,跑不脱的。也许是的,丁非民捏了捏大腿,看着窗外,两边是春天的槐树,槐花开了,一串串地挂在树上,他记得那清新的香味。他的手更用力了一些,这是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小动作,他有些激动,他要保持表面的平静。焦点平台
春天的江水略有些浑浊,却也充满生机,它们和江堤上的柳树一样,再次显示出大自然恒稳的力。丁非民走在柳树林里,折了根新枝,打了个柳花儿。嫩绿的新叶挤在枝条的顶端,枝条滑润绿黄的内茎细细软软的。湛慕水也打了个柳花儿,拿在手里,刷了刷地上的青草。他望着丁非民说,倒是有好些年没打过柳花儿了,小时候为这个没少挨骂。丁非民拿着柳花儿晃了几个圈儿说,北方柳树也多,总觉得差点意思,只有南方的柳树才有春雨如酒柳如烟的感觉。湛部长,你看过北方的柳树没?湛慕水拿起柳花儿抖了抖说,丁老师,您可别湛部长湛部长的,我受不起,叫小湛就好了。说完,闻了闻柳花儿,说,真的,我倒没怎么在意,年年月月的,看得多了,没什么感觉。在江边逛了一会儿,湛慕水说,丁老师,您看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我们先回酒店休息一下,晚上梁总少不得敬您几杯。我先给您打个底,梁总的酒量,那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丁非民笑了起来,他总不能硬灌我吧。湛慕水说,那当然不能,梁总仰慕您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他上任说到现在,总说我们工作不力,这次总算有个交代了。回到酒店,湛慕水和丁非民核了一下行程。日程安排里有一次演讲,算是正式的公开活动,其他的都是饭局,总共有四场,都在晚上。湛慕水说,空余时间,我陪着您四处逛逛,您看您,也是二三十年没有回老家了,这变化可大了,您念想的那些地方,现在还真不一定都在。交代完,湛慕水看看表说,丁老师,那您先休息一下,晚点我来接您。丁非民和湛慕水握了下手说,那就麻烦你了。等湛慕水走出房间,丁非民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酒店正对着泮湖,海城最大的内湖,湖面开阔,像海一样。因为这个湖,丁非民第一次见到大海也没有丝毫激动。这就是大海吗?它看起来过于平静,也没有想象的开阔,它和泮湖到底有什么区别?和以前不一样了,丁非民记忆中的泮湖旁边没有这么多的房子,也没有那么多看起来绿得不真实的树木。终究还是回来了,丁非民拿起手机拍了张照。跑了一天,丁非民有点累了,他躺下睡了一会儿。听到手机响时,天隐隐黑了。他简单收拾了一下,下到大堂,湛慕水在那里等着。丁非民说,不好意思,久等了,你来了多久?也不早点打个电话。湛慕水说,我也没等,靠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正好补补精神。丁非民一愣,你一直在这儿?湛慕水说,这儿挺好,沙发也舒服,好睡觉。丁非民有点生气,湛部长,这就不好了,我们在房间聊聊天也很好嘛,不用这样。湛慕水说,您跑了一天,辛苦,休息一下,我无所谓。上了车,丁非民说,以后不准这样了,不然我马上回去。湛慕水说,不了不了,没有下次。天有点黑,路灯还没有亮,空气中有槐花湿润的气息,这是典型的海城的春天。焦点平台
演讲安排在海城中学,海城最好的中学。如果追溯历史的话,能追到八百年前,古老的泮湖书院。学校里面还保存着几栋古老破败的房子,说是书院旧址,平时都锁着门,有贵宾来才打开,散发着好闻的霉味儿,正是这点霉味儿增添了悠远的历史感。在海城中学读书时,丁非民对书院旧址有些好奇。他从来没有进去过,甚至,从来没有看到那门打开过。只有乌黑的树枝从院墙里面伸出来,树上的枝叶告诉外面的人,里面还有活气。站在门口,丁非民难掩好奇,他问校长,里面有什么?校长比丁非民低两届,知道了这层关系,他对丁非民的称呼从“丁老师”改成了“师兄”。要我说,也没什么,就是几间旧房子。不过,师兄可能不这么看,您是大文人,有历史感,我看不出来什么。校长打开门,做了个请进的手势。跨过门槛,丁非民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他想起了古代。一进门,只见院子中间种了一棵巨大的槐树,枝叶覆盖了整个院子上空,甜香压制住了湿润的潮气。书院比想象的要小得多,整个逛下来,不过半个小时。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几张椅子,几张桌子,墙上挂了几张画,一张孔子像。逛完出来,丁非民对校长说,学校里有这么一处古迹还是挺好的,一想到那么深远的历史,精神就有了皈依。校长说,师兄说得是,我从这边经过,经常会想,这几百年海城出的举人进士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做这个校长,能从我这儿走出什么人才?一想到这个,顿感责任重大,一刻不敢松懈,古人都在天上看着啊。我们学校能出师兄这样的人才,说明我们的文脉还在,吾辈更应奋发。丁非民说,你是校长,我是学生,不带这么取笑学生的。校长赶紧说,师兄哪里话,我这是发自内心的尊敬,都说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师兄就是那个“文”字。丁非民一笑,校长算是让我理解了什么叫“汗出如浆”。看完书院旧址,一行人到接待室坐了一会儿。焦点平台
焦点登录:www.sdptzc.com
来之前,湛慕水和丁非民沟通演讲题目,丁非民说,看学校的意思,我都可以。湛慕水说,学校看您的意思,他们哪敢指定您。丁非民想了想说,那就讲讲文学的精神吧,虽然是个老题目,也很难讲出新意思,但对孩子们来说好接受点儿,太专业的东西讲了他们一时也接受不了。湛慕水说,好,文学的精神好,这讲到本质了,学生们能听懂一句是一句,能理解一句是一句。就算现在听得不大明白,以后想起来,听过丁老师的课,那也是不一样的。丁非民说,哪有那么夸张。湛慕水说,丁老师,学校对您的演讲那是相当相当重视。梁总说了,他要到场学习的。您可能不了解,泮湖讲堂是海城中学的金字招牌,搞了二十年,登堂演讲的不到十个人,都是国内外一流的学者。海城中学您知道,那也是出了不少人才,要上这个讲堂,门槛高得很。丁非民说,惭愧惭愧。湛慕水说,丁老师谦虚了,您是给泮湖讲堂增光添彩,而且,我告诉丁老师一个秘密,您是第一个登上泮湖讲堂的本校毕业生。丁非民说,当真?湛慕水说,当然,我还敢骗您不成。丁非民说,这就过了。喝了口水,丁非民问湛慕水,你看过《儒林外史》没?湛慕水说,翻过,没有细看。丁非民说,你还记得一个细节吧?周进对王举人说,他一个朋友梦见大红日头落到他身上,果然就进了学。王举人耻笑道,进个学就日头落在身上,要是像他中了举人,那岂不是天都要掉下来让他顶着?湛慕水笑了起来,这段我还记得,这王举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装神弄鬼的,还说什么文章后两股不是他作的,也不是人作的,贡院里真有鬼神。我看他就是鬼神。丁非民说,我现在有种感觉,我就是那书里的人物,不是王举人,就是张举人李举人,荒唐可笑。湛慕水说,丁老师,有时不能想得太多太透。丁非民说,看来湛部长也是戏中人。湛慕水说,谁不是呢。焦点平台
演讲完,应酬完,将近十一点了。校长把丁非民和湛若水送上车,站在车边上向他们挥手道别。丁非民喝了点酒,不算多,他的酒量其实还不错。不过,和梁总比起来,简直不堪一击。前天晚上,接风宴上,梁总喝了怕是有两斤,他也喝了七八两。换在以前,他怕是早有了醉意。酒喝到中途,梁总拿了一叠书过来,请丁非民签名。梁总翻开书说,丁老师,我这可不是临时去书店买的,您看书都翻旧了,我还在边上写了读后感。梁总连翻了几本说,我这是真粉丝,真爱啊。丁非民心里一热,说,梁总不要嫌我字丑。梁总说,丁老师,您这是给粉丝派福利啊。丁非民签完名,梁总收好书,倒了满满一杯洋酒说,丁老师,这杯酒我敬您。说罢,一昂脖喝干了。丁非民有点为难,还是一口喝了。梁总还想再加,丁非民用手遮住酒杯说,梁总,不能再这么喝了,不然得吐了。梁总说,加一点,慢慢喝。他的手放开了,梁总果然只加了一口。他放下心来。酒毕,送丁非民回房间,湛慕水问,丁老师,您没事吧?湛慕水说,我还好。湛慕水说,我看出来了,丁老师的酒量那是深不可测。丁非民说,能喝一点,多了不行。心情好就不一样了,湛慕水说,我能看出来丁老师回来也是高兴的。说罢,又补充了句,梁总这次真是用了心了,他酒量虽然大,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拿这么多酒敬人。丁非民说,我也是舍命陪君子了。海城中学演讲完,梁总握着丁非民的手说,丁老师,今晚我就不能陪您了,您在海城有什么事情,尽管给我打电话,只要是我能解决的,我全力以赴。丁非民说,谢谢梁总,这次回来太烦您了。梁总大笑,这种麻烦越多越好,我热烈欢迎。说罢,又委托校长,一定要把丁老师招待好。校长高声回答,请梁总放心。宴席上校长一口一个“师兄”,好像他们认识很多年一样。他们回忆了当时在校的情景,校长认定他当时认识丁非民,丁非民却怎么也想不起他认识这个人。照例,他又签了一堆书,崭新崭新的,散发出新书还未被翻阅的油墨香气。接待结束后,湛慕水陪丁非民回酒店。车到了酒店门口,丁非民对湛慕水说,你让司机先回去吧。湛慕水笑了起来,丁老师还有什么想法?丁非民说,确实有点想法。湛慕水说,那行,我陪着您。焦点平台
他俩坐在马路边上,这是海城的老城区,街道狭窄弯曲,随着山势起伏,房屋高低错落有致。街灯依旧昏黄暗淡,街道上散发着怀旧的气息。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山在黑暗中,雨要来未来。大排档生意正好,一米见方的小桌子排满了整条长街。从的士上下来,湛慕水说,丁老师,说实话,这地方我也是好久没来了。丁非民看了一眼说,这儿倒和以前差不多。湛慕水说,没怎么变,老样子,到了夜里,还是这里热闹。丁非民问,你有多久没来了?湛慕水说,那真想不起来,还是年轻的时候吧。丁非民说,怕是因为身份变了吧。湛慕水说,在丁老师面前说什么身份,那不是丢人吗。他们找了个烧烤摊坐了下来。椅子太矮了,丁非民的大腿顶着肚子,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海城的大排档、烧烤摊要用这么矮的椅子?他去过那么多地方,只有海城的大排档、烧烤摊用这么矮的椅子,比幼儿园小朋友坐的椅子略大,高度却差不多。他们面对面坐了下来,湛慕水问,来点啤的?丁非民说,来点儿。湛慕水说,丁老师果然好酒量。叫了啤酒,丁非民问,你有烟吗?湛慕水有点惊讶,丁老师您抽烟?丁非民说,一般不抽。湛慕水把手伸进口袋说,我以为您不抽烟,这几天一直没当您面抽,忍惨了。丁非民说,我闻到你身上烟味了。给丁非民点上烟,湛慕水说,丁老师,是不是有点怀旧的感觉?丁非民点了点头,岂止一点,很多很多。到这儿一坐下,以前的岁月都回来了。湛慕水叫了一打啤酒,丁非民说,叫那么多干嘛,怎么喝得完。湛慕水一边开瓶子一边说,喝多少算多少,反正明天也没什么事儿,我们都睡到自然醒。我这些天都交代给您了,不用上班,只要你不催我,没人催我。丁非民说,我也没什么事儿,你睡醒了电话我。喝了几杯,湛慕水问,丁老师要不要叫几个老朋友过来?丁非民说,我哪有什么老朋友,海城我最熟的就是你了。年轻时候的朋友,联系都断了。湛慕水说,这是自然,不要说您,就算我,在海城土生土长的,很多同学朋友都不联系了,毕竟各自道路不一样,见了面也没有什么话说,时间长了,也就断了。几瓶酒下去,丁非民有了醉意,他对湛慕水说,湛部长,我遇到了件事儿,想听听你意见。湛慕水连忙说,您千万别这样叫我,小湛,小湛就好,有什么事儿您说。丁非民说,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到酒店房间的。按说,我回来的事儿知道的人不多,知道房间号的更少,她是怎么知道的?湛慕水有点紧张,说了什么?要不要我查一下?丁非民说,你别紧张,我只是好奇,听话里的语气,好像是个熟人,但又说得含含糊糊,让人摸不着头脑。湛慕水问,男的女的?丁非民说,女的。一听说是女的,湛慕水舒了口气,打趣道,丁老师,说不定是您的女粉丝。丁非民说,她约我见面,我还在犹豫。湛慕水说,既然还在犹豫,那就见吧。丁非民说,这怎么说?湛慕水说,既然犹豫,那说明是想见的,不过心里没底。这就像猜谜,您要是没兴趣,您就不猜了,还在猜,就说明您是想知道谜底的。既然想知道,干脆揭开它好了。丁非民举起杯子,和湛慕水碰了下杯,湛部长是个通透人啊。焦点平台
早上起来,丁非民状态还不错,除开嗓子有点干,头略有点大,别的还好。等他刷完牙,喝了杯热茶,精气神都回到了他身上。他打了个电话,叫楼下餐厅给他送份早餐上来。这几天,都是湛慕水陪着他吃早餐,念想了多年的小吃一一吃过了。人的胃口比脑子诚实得多,他不想回海城,对那些吃食却还惦记着。比如说海城的豆皮,他在网上买过几次,总觉得差点意思。味道有没有?有的,到底差点什么,他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对。这次回来尝了一口,味道对了,和记忆中的分毫不差。都是普通的吃食,老百姓桌子上常见的便宜东西,差的可能就是这口地气。就说昨天晚上,他和湛慕水坐在路边吃烧烤,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臭豆腐、土豆片、藕夹,还有随着物流的发达远道而来的鱿鱼须、生蚝、濑尿虾。他吃得最舒服的还是一碗土豆片。土豆切片,油锅里炸过,然后淋上一勺黏糊糊黑乎乎的料汁,味道古怪又深刻。即使他如此成熟的舌头,也还是分析不出那碗料汁里到底有些什么东西,这味道是海城所独有的。在外的同乡,偶尔遇到,聊起这碗土豆片,总是百感交集。再多的好东西,也抵不过那碗莫名其妙的土豆片。湛慕水也吃了一碗,吃完感叹道,这玩意儿从小吃到大,味道从没变过。不吃倒还好,吃上一口,胃口一下子醒了,山珍海味都不作数了。丁非民也是这种感觉。吃完早餐,又洗了个澡,重新泡了杯茶,丁非民的身体调整到了舒适状态。望着阳台外的泮湖,他想起了前天接到的电话,他本以为打错了,对方却喊出了他的名字。悦耳的女声,听声音的厚度,想必不年轻了。他搜索了他的记忆,这些年,他没有和海城任何一个女性联系过,除开母亲。湛若水打电话给他时,他还在猜测,电话里透露的信息太少了。她说想见见他,至于原因,没有细讲,她甚至没要讲的意思,好像确信他会答应和她见面。她说,见面聊吧。湛慕水问丁非民,丁老师,今天您想去哪儿?丁非民说,随便逛逛吧。这几天的天气好得不自然,连丁非民这么宅的人都想走到自然中去。天太蓝了,春天,阳光和空气都有着独特的味道,土地像是充满了蓬勃的张力,无数秘密的生命正在破土而出。接到丁非民,湛慕水说,丁老师,您看今天去哪儿?城区周边基本都逛过了,包括古老的江心洲和年轻的博物馆,陶器、青铜器、铁器和各色的瓷器。他们去了城外的山上。吃过午饭,两人缓步上山,松涛阵阵,青草的味道沁人心脾。他们在半山腰找了块平缓的大石头,先是坐着聊天,坐了一会儿,两人躺了下来,眯上了眼睛,眼前一片明亮的血红色。身体温暖,大腿和肚子有点痒,像是连身上的细菌都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忍不住躁动起来。湛慕水的声音软懒起来,丁老师,晚上真不用我陪您过去?丁非民说,嗯,不用,又不是谈判。那您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要不要帮您订位置?您见完了给我电话,我去接您。我打个车就行,你早点回去,陪了几天了。没事,应该的。嗯,丁老师——丁——等丁非民醒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他身上冷了。睡得太舒服了,他还做了个梦,他不想说。湛慕水还眯着眼。丁非民坐了起来,这片松树林可真美啊。他该回城了,约的时间快到了。焦点平台
到了约定地点,丁非民看了看表,他提前了十分钟。又看了看手机,他还没有收到她的信息。我可以多等五分钟,丁非民想,超过约定时间五分钟就不等了。餐厅是她订的,包括这个小包间。这是一家日式料理店,环境清幽干净,倒也适合聊天。从外面进来时,他一眼看到了熟悉的槐花,这个季节,海城的槐花算得上景致。小小的院子里还做了水景,红黑白黄的锦鲤在翡翠般的水里缓缓游动,荷叶正嫩,散发团团的青气。丁非民坐了下来,他想起了下午他在山上的梦,他梦到了一个女人。她进来时,她的形象和他梦中见到的形象快速重叠,这让他有点激动。见到丁非民,她放下手包,坐下来,看着丁非民说,我知道你会来。说完,给丁非民倒了杯水,我看过你的书。丁非民拿起水杯说,谢谢。他抿了口水,他还不习惯单独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约会。这些年,只要出门,他身边几乎都是一群人,喧闹不堪。丁非民说,我有些好奇,我不知道你到底要和我说些什么。她笑了笑,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我约你当然是有话想和你说。除开这个,我们还能干什么?她把“干什么”说得很重,像是暗示,又像是挑衅。她的样子在丁非民眼里清晰起来,尽管不再年轻,她依然有迷人的脸,特别是嘴唇,像是深渊,或者蹦极台。他说,什么也干不了。她又笑了笑,你对我感到好奇?丁非民点了点头。很快你就知道了。她说,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开头没有让丁非民意外,他多次听到类似的话。很多人当面或者发信息告诉他,要给他讲一个故事,并且信誓旦旦,这会是一个超棒的小说。想多了,几乎没有几个人的现实生活能够构成小说。小说中杀人放火再稀松平常不过了,而作为普通人,多数人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种不幸。这不会是一个让人意外的故事,他不在意,但是由她来讲,会不会有所不同?他面色平静地说,很多人给我讲过故事。她说,我讲的这个不一样,它非常简短。焦点平台
很久以前,我认识一个男人。允许我抒情一下,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男人,直到今天,我没有见过比他更好的男人。我无数次梦想过嫁给他。你看看我,我长得就算说不上漂亮,至少也称得上五官端正。(不,你很漂亮,哪怕是此刻,你已不再年轻,你还是很漂亮。)他后来娶了一个外地姑娘。据说那姑娘来自西北,家里养了一群骆驼。他第一次吃驼掌、驼峰就是在她家。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旅游?笔友?还是朋友介绍?我不知道。他给我描叙过她家,苍茫的大山脚下,一个小小的县城。他们结婚时,我还送了礼物,他们客厅的电视机和沙发都是我送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是最慷慨的前女友。他们说错了,我连前女友都算不上。如果是前女友,至少还有让人回忆的地方。他对我真的就像对自己的妹妹,无可挑剔,但都不是我想要的。他们过得很好,没有故事,没有冲突,没有第三者和外遇,也没有贫困和试探。本来,他们可以度过如此美好的一生。我虽然羡慕,却也愿意送上祝福。后来,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嫁人。你是不是觉得我讲了这么久等于什么都没讲?(不不不,你讲得很好,很有文学性,故事铺得很好。我们可以先叫点吃的,边吃边讲,你喝什么酒?)我以前喜欢喝烈酒,现在红酒喝得多了。(我都可以,今晚我也想喝一点。)我不喜欢他女儿嫁的那个小子,我认识他。那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那混蛋长得非常帅气,还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收入不错,还非常清闲。小崽子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从小到大,坏得流脓。我找人狠狠教训过他,那会儿他大概十八九岁,你猜为什么?有天回家,他在路上拦住我,说愿意出五千块钱要我跟了他。这混蛋怎么想的?我做他妈都绰绰有余。我反复和我心里的那个男人讲,一定要阻止女儿嫁给那个混蛋。但没有用,一向乖顺的女儿铁了心要嫁。那混蛋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女孩儿?婚后没多久,他就开始打她,几乎隔几天就要揍她一次。每次揍她,就像一次花式表演,有时绑起来揍,有时在酒桌上抓着头发揍。打的次数多了,消息自然传了出来。男人气坏了,一次次警告那个混蛋,但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男人劝女儿离婚,女儿怎么都不肯。这实在让人迷惑。你能猜到原因吗?我至今都想不明白。(我也猜不到,但我知道人性的复杂,内心的世界过于微妙,没有人能写出正确答案。如果硬要解释,它有一万种可能性,都具有逻辑的合理性。这种沙盘推演,只是逻辑的延伸,它在生活中其实都是小概率事件。一个作家的写作,往往会关注小概率事件,它的独特性容易勾起读者的好奇心。过于庸常的生活,我们很难书写,它与生活过于平行而让人失去兴趣。)你猜猜,这位父亲会怎么干?他杀了他。没错,他杀了他。那是在冬天,那混蛋又在狠狠地揍她。他剥光了她的衣裳,狠狠地揍她,然后还把她推到门外。天特别冷,前一晚刚刚下过雪,春节就快到了。那时我正坐在窗台边喝酒,夜光中,雪带着青灰色,树枝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连没有南飞的留鸟都躲在巢中。大院里每个房间都亮着灯,外面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冷的天,又是深夜,谁会在院子里闲逛。我正看着屋外的风景,那女孩从拐角处走进我的视野。我以为我眼花了,或者出现了奇迹。很快,我认出了她,我也像爱女儿一样爱过她。我连忙抱着件长长的羽绒服跑出了门,把她抱进家。真的,几乎是抱,我一看到她,她就僵硬在那里,像是失去了意识。我给她套上羽绒服,想扶着她回家,她僵硬在那里。我只好把她抱起来。进了家门,不要说她,我都吓坏了。我全身都在发抖,活了几十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恶劣的事情。我气得发抖。她一句话没说,我问她什么她都不说话。第二天早上,我给男人打了个电话。女儿还在睡觉,他在我家客厅抽了整整一包烟。老实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很快就听到了他杀人的消息,他杀了那个混蛋,只用了一刀。他女儿从未去探监,我每个月去两次。我的故事讲完了,她说。焦点平台
她给丁非民倒了杯酒,你会不会以为我给你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勾起你的兴趣?长条形的木桌上摆了盐烧三文鱼头、炭烧猪颈肉、寿司拼盘、象拔蚌和北极贝刺身。丁非民举起酒杯闻了闻,要不然呢?他调好芥末汁,蘸了片象拔蚌,鲜甜爽口,没想到海城也有这么好的海鲜。他的情绪平稳下来,刚见到她时的激动已变得理性。她说,你觉得这个故事怎样?挺好的,丁非民说,如果不是虚构的话。她笑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虚构,你信不信?我信,丁非民笑了,这像个小说,它和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女人?丁非民又笑了,那我一定也是疯了。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完善一下这个故事,让它变得更合理?不,我不想。如果这是一个故事,我对它没有兴趣。如果这是生活,发生的一切都不容修改。女人笑得有点羞涩,那你也给我讲一个故事?丁非民想起了他的十八岁,那条幽深的,像是没有尽头的小巷子。他记忆中的脸和眼前的女人重合起来,和下午在山上梦到的女人重合起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具有她们所有的美好特征。焦点平台
(补记:第二天,丁非民对湛慕水讲了一遍听来的故事。他问湛慕水,有这事儿吗?湛慕水说,丁老师,这事儿您从哪里听来的?不瞒您说,这事儿当时轰动整个海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街头巷尾角角落落到处都传遍了。这事儿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丁老师,您可能被骗了,人家拿一个海城尽人皆知的故事逗你玩儿呢。这么说,故事中的女儿还在海城?早就不在了,湛慕水说。丁非民说,见了鬼。他想起了女人临走时说的一句话,其实,你一直记得我。)焦点平台
焦点娱乐登录: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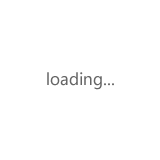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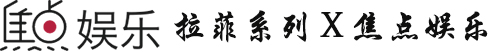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