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网快讯:

杨知寒,生于1994年,作品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等,曾获豆瓣阅读征文大赛“最佳人物奖”、萧红青年文学奖。现居杭州。
我十六岁那一年每晚都做梦,做噩梦。像香港三段式老鬼片,梦由几个情节清楚、互不相干的小故事构成,却能一直延续恐怖的疑思。等到了白天,梦中的画面就像盯了太阳一阵后眼前会出现的色块,不知什么时候突然浮现,叫人心中一凛,忘记手上要做的事。我问身边的塔米,现在每晚几点睡?这个问题颇有侦查的意思,在竞争激烈的文科小A班里,几乎每个人都想闹清楚身边人是几点睡觉,睡前做什么题,来对照自己学习的进度,做到知己知彼。塔米从正写字儿的纸上回看我一眼,她有一双单眼皮的大眼睛,五官都是扁平的,仍能算得上好看,起码是可爱,厚实的前头帘下鼻头隐约翘起,鼻梁像一截儿童滑梯,弯得不像样。她没回答我,只是笑了一下,嘴角也弯得厉害,在她身上似乎缠绕数不清的曲线和弯道,让人刹不住闸,只能在她带来的感觉里飘然滑出去,抓不住一点儿牢靠的东西。我看着她继续笨拙地握笔,在白纸上分行写字,跟她讲了我现在还能想起的一个梦。梦里有个中年女人,我不认识,看不清面孔,但气质很好,人也亲和。她手里捏着个褐色的小瓶子,瓶子上贴有张白标签,字儿被她捏着的手挡住了。女人说,孩儿,过来,闻一下。我和女人面面相觑,沉默中对峙了很久。她知道我闻了就要死,我知道我闻了就要死,死生不是能容易决定的事,可我们更能达成的共识是,彼此都对这天准备已久。我上前闻了一下她拔开瓶盖的小瓶子,只一下,无任何痛苦,甚至无任何感觉。我拼命想记住,闻之前和闻之后我整个人的差别在哪儿,却只记住了双耳茅塞顿开的感觉,像两只耳朵里的陈年耵聍同时被化学溶剂稀释,震出,蒸腾,升华。死亡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于听见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塔米突然再回头看我,问,李芜,你听着什么了?我回答她,我听见了巨大的空间。焦点娱乐平台
她将圆珠笔顶在一侧太阳穴上,发出按响的滴答声,像她太阳穴上藏着一个按钮,不停按着启动键。我说,再这样下去我得让我妈带我去看看了。她说,我觉得你以后会怀念这些梦。应该趁现在没忘,都给记下来。我瞥了一眼她在纸上写的东西,大概是歌词,她总爱整页整页地抄歌词,字体儿童般规整,有点儿笨拙。对她的话,我不置可否,毕竟做梦的不是她,感到困扰的也不是她。塔米觉察到我的不乐意,摩挲我的手臂说,跟我讲讲,你每晚睡前干什么?我说,做作业。洗漱。睡前看会儿外国名著。犹豫片刻,我还是都讲给她听,我会给床上所有的娃娃盖被子,叫它们的名字,一一说晚安。塔米果然没有笑我,她弯弯眼的样子像一个年轻母亲,拥有和女儿相差无多的纯真,或者说相信。她相信我这样做不止是出于幼稚。我想起有次母亲推门进来,正看见我给娃娃们布置睡觉的地方,脸上露出的表情。她没表情,仅仅是伸出手数了数,我床上共有多少个娃娃,乘以二,我床上共有多少只眼睛。在我告诉给塔米这个梦的当天,放学回到家,我的床单上已空空荡荡,娃娃们在一日之间完成了迁徙,迁徙到的终点是我家车库里的壁橱。想到那里的暗无天日,想到我的小奇,蓝娃,明美,老博士,还有内心最敏感脆弱的娜娜——那个扎两条棕色辫子一脸雀斑的洋娃娃,将终日躺在那儿,我站在床前,像又再吸入了小棕瓶里的气体。母亲在我身后站住,满意地叉腰,诉说她白天是多么不易,一趟趟地搬运,将那些她认为是困扰我睡眠的元凶移走,床上终于只剩我一双眼睛了。这下你指定不做噩梦了,你看着。她这么说。这时我耳朵里有细弱的、平日听不见的声音鼓叫,那是塔米。学校里塔米最后一次按响太阳穴上的按钮后,女巫一样凝着我说,她准备去哈尔滨走一趟。当天回来,不告诉任何人。我们应该一起去一次,看看另一个城市。当时我没有回答她,现在我在心里回答她,得去一趟了。不去医院,也得去趟哈尔滨。焦点娱乐平台
当晚我的确没做噩梦,我压根也没睡。我们准备坐周六早上七点二十的火车,坐两个半小时,到哈尔滨差不多十点。清晨六点,我蹑手蹑脚洗漱,拎上背包出门,在书桌上给我妈留了张字条,写道:有集体活动,晚上回来。早饭集体吃了。焦点娱乐平台
说是那么说,就算有个集体,也不过三个人。到火车站时,我看见塔米和一个男生并排坐在早晨的候车室里,他俩对身后扛大包的民工和卖茶叶蛋的小贩熟视无睹。若只截取他俩相处时的画面,此处更像是电影《北非谍影》中鲍嘉和褒曼分别时的机场。男生的名字我叫不准,记得是两个字,塔米给他起了个更好记的名字,小怪兽。小怪兽人如其名,个头不高,有点黑瘦,倒是剑眉星目,在一众奶声奶气的男孩子里容易脱颖而出,因他脸上总带有一种坚毅而沧桑的神态,如果身量高大点,披件风衣,大约会很像母亲喜欢的高仓健:凝着眉,将手上抽了半根的香烟送到嘴边,对眼前即将永别的女人,吐出一阵沉默的紫烟。小怪兽和塔米是什么时候好上的,没人知道,有关塔米的一切都来得像风,你看到时,她已在风中旋转了好一阵。我默默坐到与他们隔了点距离的地方,心说你们下一步干什么呢?我是想跟着学学,我也有一个男朋友,彼此都是初恋,两人摸对方的手过河,双方都不是很牢靠。一步步艰难探索着,在探索中失去赏风景的乐趣,和对方开展恋爱关系,更像上了注定要去的一个兴趣班,一个锻炼营。我无法掩饰自己对塔米的羡慕,就比如今天,我也和陈朴说了白天要去哈尔滨这件事,可他没有来,也没想到该来送。昨晚我们发着短信,他回答我说,行啊,出去玩玩。你加小心,看好车次,别当天回不来。我说,我没你想得那么傻。陈朴回每条短信,基本都间隔五分钟,每个五分钟里,我会把手机扣过去,来抑制自己频频注意的眼神,上面没有信息,没有他也是个活人的沟通感。陈朴回复说,去哈尔滨,给我带点什么?我说,如果你去外地,给我带什么?他说,不知道。这是我问你的问题,你应该先回答。我说,如果你去外地,我不会问你要东西。之后我起身,木偶一样去上厕所,冲水,洗脸,刷牙,经过父母卧室门口时,大喊一声晚安。回到卧室,我往背包里装了些面巾纸和巧克力棒,拿出衣柜里一套背带裤白T恤,摊在床单上。我受不了此刻床单上空无一物,和我受不了此刻手机上空无回复是一种心情。站到窗口,吹了一会儿夜风,想象自己已是二十六岁,明天会出现在纽约或者香港,对于频繁离开一个地方,已经不太有知觉。焦点娱乐平台
在距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时,我走向塔米和小怪兽,塔米看见我,拍了拍右手边的空座儿,示意我不着急,还能一起聊会天。我们看见其他候车的人在面前来回走过,他们有的痴痴张望挂在候车大厅里的挂表,有的打起电话,跟对方一口一个哥,说着我不能、你放心、没什么过不去的。还有几个和我们母亲岁数差不多的妇女,紧紧挎着皮包,鬼祟地每坐几分钟就换个位置,眼神侦查兵一般逡巡着每个进入她视野的人,好像她们此刻没出现在早市、没出现在自家灶台前,是种重大的神秘。我和塔米互相牵着彼此一只手,小怪兽向我看去,塔米对他说,这是和我坐一桌的姑娘。这是我对象,总和你提的,十三班的小怪兽。我说,你好。小怪兽噗嗤笑出一声,他笑的时候倒是和其他男孩不见差别了,和陈朴一样退化成了七八岁,哪怕笑声无法持续,嘴也一直咧着。小怪兽说,麻烦你照顾点儿塔米。我和塔米互看一眼,听她问我,陈朴不知道你去?她问的不是一句悄悄话,小怪兽听了,露出若有所知的表情,我也只好装成豁然的样子,说,那个死猪,别指他。他俩这回一块笑了,脸孔相对着,眼神牵连到一处,像一截看不见的桥,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建设,最终凝结在中点。塔米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车票和临时身份证,交到我手里,说,给李芜保管,她稳当儿。小怪兽微微侧头,嘉许她这样做。我不知道塔米为什么想出这个逃离一日的计划,她看来没任何需要逃离的事,反而有更多该迷恋的理由。她挥挥手跟到了我的身后,替我提上有些下滑了的背包带,我不再回头看,回头看的画面只该属于塔米一个人。她在和我检过车票、登上站台时,念诗一样说,小怪兽的眼神像卫星,无法不围着她转。我不禁想象他俩相处时更多的画面,有时能在校园里看到,有时是在校外。他俩从不避讳。小怪兽踩着自行车,载塔米在后座上,他俩男女声二重唱,唱塔米喜欢的台湾民谣,名字是《归人沙城》。我只记得这一首,因我对那个场景印象格外深刻,嫉妒也来得更热烈。塔米在纸上摹写的歌词里有一句,不知道是歌里就这样,还是她爱重复,同一句写了好几行,如果我记得不错,是“沙河又在缭绕”。焦点娱乐平台
我和塔米分坐在车窗的一侧,早上这班人不多,车厢大半是空的。塔米拧了瓶矿泉水,递给我,问我昨晚又做了什么怪梦。车上时间多,都给她讲讲,她爱听。我闭了下眼睛,让那些恐怖的色块儿都回到眼前,给她讲了一个飞升在灵堂里的梦。梦里我飘着,别人看不到我,我能看见他们匍匐在深宅大院里,穿着戴孝的白衣,簇拥一口棺材。棺材里是我另一张脸,和现在不是一个模样,但那只能是我,细抿着眼睛和嘴唇。我飞升过每个人的头顶,最后坐在房梁上,晃荡两条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盈。我在空中盘旋了很久,并非那多有乐趣,而是不知该去往何处。塔米吃着我带的巧克力棒,嘴角溢出棕色的糖浆,默默地听。窗外建筑物逐渐消失掉,平原开始出现,北方一片萧索,几乎每棵经过的树的枯枝上,都藏有蓬乱的鸟巢。她昏昏欲睡,我一直听广播里的报站。焦点娱乐平台
塔米姓塔,这就是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世上有塔这个姓氏。塔米的名字叫起来像一种零食,塔形米饼一类的东西,嚼在嘴里嘎吱响。她来自我们都不熟悉的十五中,在重点高中里,大家此前上的初中无非那几所,十五中从未听闻,也许在外县。据说她是十五中里唯一考进这所高中的学生,考取他们学校大榜第一名,人和姓氏一样,具有传说中的色彩。塔米和我在彼此从理科班分别考进小A的第一天,就被分到了一张桌子上。总穿紫色卫衣的她,手常缩在袖子里,梳小丸子短发,比小丸子的还长一些,爱时不时刷下额前的刘海,即便它们那么厚实,基本纹丝不乱。我那时饱受青春痘的困扰,它们此消彼长不说,还分散生长;离远了看,像脸上布满了红豆。班上讨厌的男生曾经起哄说,李芜他爸往李芜脸上浇了一勺油,李芜拿漏勺挡脸,留下了这么个情况。有次学校组织大合唱,人人都要往脸上扑粉,针对那些青春痘,我扑上一层,它们露出一层,最后形成火山似的效果,白粉在火山口下堆成层叠的地皮,只让那些痘更醒目。塔米在我身边拿出她的小镜子,趁我扑粉的时候卷起自己的刘海,我瞥了一眼,看到原来她也长痘的。原来那些痘都长在她的刘海下面,集中分布于额头。连她的青春痘都那么会找地方生长,平时根本看不出。塔米此时睡醒了,最先去拨弄她的刘海,仿佛想让下面那些隐藏的生命体透口气,轻轻抓挠了几下。我说,快到站了,还有十分钟。她懒洋洋地支起一只胳膊,瞧着窗外,以和她平时上课没有差别的姿势,眺望我们的省会那些高人一等的楼群。她说,得先去吃点东西,我饿了。我说,还没计划今天去什么地方呢。你想去哪?她想也没想说,中央大街。我知道中央大街,那很出名,街两侧有许多俄式建筑,还有俄式西餐厅、俄式教堂。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她说打车去,但我们必须先吃饭。我偷偷摸了下裤兜里的钱,并不多,感觉我们吃不起俄餐,不然我干吗带那么多巧克力。焦点娱乐平台
我们迷失在站外复杂的人群里,不由自主向着招呼我俩上车的喊声走去。那是等在站口的黑车司机,他撇下烟头看了我和塔米一眼,知道我们可能会去的地方,问是索菲亚大教堂还是731旧址。我和塔米异口同声,在后座上密切地贴着彼此说,中央大街。车在我俩眼中梦幻般行驶着,和塔米不再交谈,我们的视线为新奇的景观占据,不知道她是怎样想,在我心里,哈尔滨比想象中更繁华现代,拥有我们那儿永远也不会存在的一种气质,似乎所有建筑都能彼此交流,谈论得海阔天空,与未来相连接。连接我们那儿的则只有过去。车子最终在一个人潮汹涌的巷口停下,司机说车只能到这儿了,要我们五十。塔米把钱递出,正好一张五十,我不禁怀疑,她是否携了巨款出门。等下车她却告诉我说,现在她身上还剩二十。好在我们早已买好返程的车票,也不预备在哈尔滨买什么东西,我带的钱足够一顿平常的午饭。我们没直接走入中央大街里熙攘的人群,即便是周围一条狭窄的小街,走在其中,也有在异国探索的兴奋。街上有几家饭店,透过玻璃窗,能看见店里坐着许多疲惫的大人,有些在喝中午酒,绿色的瓶子摆了一地。那不是我俩该去的地方。塔米拽了下我的手,脚步停在一家叫玉英的烧烤店门前,说不行吃烧烤吧。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有胆量在她的提议下先走进店门,毕竟离开了小怪兽的塔米,需要我的照顾,需要我承担满足她愿望的责任。店里只有两桌客人,我们努力表现得适应,坐在窗边的台子上,目睹眼前还闪着油花的桌子,点了两盘家庭拌肉,一盘金针菇。不能再看菜单了,再看只会暴露我俩的饥饿,它根本不是这点儿东西就能够缓解的。点完菜,塔米瞪着眼睛看向另一桌的客人,是个自斟自饮的小伙子,他抿了口杯里琥珀色的啤酒,也不掩饰地看向我俩。塔米说,要瓶酒。我思索怎么拒绝她,听她又补充一句,说,我俩是在进行一场梦中的旅行啊。喝点酒,就更像梦了。焦点娱乐平台
来,你提一杯。肉滋啦滋啦在烤盘上变色,塔米举起酒杯,向我点头。我说,祝咱俩旅途愉快?还能咋说。塔米往嘴里快速填着肉片,我看着她,不觉得这里的肉有多好吃,要论烧烤,还得是我们那儿。只有酒,是塔米坚持的正确选择,哈啤,名不虚传,虽然我也不怎么懂酒,只觉得滑入口中,确如塔米所说,人很快热腾起来,红脸,心跳,有着梦中一样的,被未知在身后追赶的悸动,兴奋如缓慢地过电。小伙儿遥遥向我俩举起杯,我有点恍惚,看到塔米也把杯举起,他俩隔空碰了一下,小伙儿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四下看看,人连凳子一起搬过来坐。我下意识躲了躲。他似乎已经吃好了,可能感到寂寞,跷着二郎腿,手里掂量一杯酒,又管服务员叫来两瓶,搁到了我和塔米的桌子上。这人很壮实,有和小怪兽或者陈朴都不一样的身材。他的气质状态也不像学生,流里流气,起身时带动腰上一圈钥匙,哗啦哗啦直响。他坐下抖着腿,钥匙跟着响,我瞄了眼他穿的特步运动鞋,鞋底沾了一层泥,猜他也许是来哈尔滨打工的。小伙儿眼睛始终向着塔米,偶尔雨露均沾投向我说,他一人儿喝实是没意思。焦点娱乐平台
你俩多大?小伙儿问。十八。你呢?塔米懒洋洋地抬眼皮,肉也不往盘里夹了。小伙儿说他二十四。寻思片刻,他站起来,向我俩伸出手,说自己叫齐德利,齐齐哈尔的。他发音不太清楚,我听不清是齐得意还是齐德利,与塔米相视一笑。塔米说了自己的名字,又指指我,说她叫小怪兽。齐得意转脸笑了,说我俩不用这么警惕,咋还都用化名。他和起初的我一样,都以为塔米的名字是昵称,像网络上新用户注册时必须绞尽脑汁想出的一个代号。塔米不置可否,齐得意用自己买的酒给她斟满一杯,我的基本没动,不用再倒。他问,你俩是学生吧?哈市哪所高中的?塔米说,反正是重点。你呢,干什么工作?他说他眼下没活儿干。能在这碰上就是缘分。两个老妹儿,还想点点儿什么不?看你俩也不够吃的,不行再来盘燕翅。他总来这儿,知道这家别看生意不好,其实酒香巷子深,燕翅肉不错。齐得意回身,叫了盘他说的燕翅,又拆开副一次性筷子,拨弄我俩烤盘里的肉,该翻面翻面,出奇自来熟。给我盘里夹了一块,给塔米盘里夹了一块,过会儿又给塔米夹了一块。夹肉的时候,我没抬头看他,只抬头看着塔米,他俩眼光相对时,有我不能参与的较量。焦点娱乐平台
齐得意说,他在哈尔滨待了八年,初中毕业就过来找活干,去过好几个工程队,眼瞅能接包工头的活儿了,工程出了岔子,工程队立地解散,经理给每个人塞了点儿钱,算是遣散。他将杯举起来,示意我们都少来一点,抿一口意思意思。碰完这杯酒,他又自顾自说了些自己的事,听不出真假,但大意是希望我们明白,虽然眼下他混得不好,可全不必担忧,挣钱的道儿他还有不少,兜里不紧。塔米始终微笑听他讲,当后上来的燕翅也差不多吃空盘时,齐得意腰间的钥匙又响了,他紧着张罗下一步,将手在圆桌上做了个囫囵的手势说,这顿他请。难得两个妹妹看得起他,话怎么说的?相请不如偶遇,这是多大的缘分呐。我看了眼塔米,已经搁在钱包上的手被她在桌底下按住了。服务员过来结账的工夫,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听他的呗。反正一会儿咱就撤。齐得意给我们一人递了张餐巾纸擦嘴,他站起来大约有一米八,脖子上一圈亮晶晶的细毛汗,始终笑盈盈。说他下半天儿也没事,可以陪我俩逛逛。他身板可以,能做好护花使者的角色。最次也能帮着拿东西。焦点娱乐平台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我们要去中央大街,溜达,塔米说。我讨厌她和齐得意说下去,如果真像她刚才说的一会儿就撤,我们应该礼貌地在饭店门口挥挥手,随便找个借口甩掉他。可是塔米好像没意识到她的话前后矛盾,这人已经跟上了我们,在进入那条遍地石砖的中央大街时,齐得意得意洋洋地一会儿窜到我俩左边,一会儿窜到我俩右边,视线和过路的男人会合,仿佛漫不经心地炫耀,他一下得俩,俩都是他的。和塔米俩手拉着手,身后的齐得意就像截尾巴,我们尽量不去想他的存在。当终于来到这个地方,我俩的笑容和兴奋很容易就出卖了自己的年龄和见识。下午风很凉爽,随着我俩不断的跑跳,将头发一下下地吹起来。到马迭尔冰棍柜台前,我和塔米挑了两只原味的,迫不及待放进嘴里咂吧,浓厚的奶香从舌尖开始流窜,沁入五脏六腑,我俩闻着彼此身上的气味儿,感觉又都乳臭未干了,像突然从手抱的婴儿坠入了成长的高速路,十几年成长中的时光一如梦境般碎裂被剪辑,不成头绪。只有出生和眼下,是最真实的记忆,永远难忘却。塔米找了个树荫下的座位,我们一起坐在那儿,齐得意默默看我俩将冰棍筷子上最后一点雪糕吮吸净,沉默了许多。塔米突然说,要去趟厕所,就去对面的麦当劳里,让我们在这儿等着她。她说话时尽管平静,感觉又是刻不容缓,也是,吃了那么多油腻的,又突然吃凉,肚子一定不舒服。我担心她是否需要伴儿,又犹豫,像塔米那么轻盈神秘的女孩,哪会需要我在门口拿着卷纸等呢。她很快消失在了巨大的黄色M里。我呆呆想,因为没吃过,不知道麦当劳是不是和肯德基一样,也卖炸鸡呀?焦点娱乐平台
齐得意掏出口袋里的钱,一摞,红色大票在外面,里面夹些彩色的,一张张地数,似乎我是团空气。数到一半儿他抬头看我,对上我没来得及收回的视线。焦点娱乐平台
你俩缺钱,对吧。他说。我点头,又摇头,说,还没挣钱呢。他又问,她有没有对象?我说,有。齐得意看着我,那你呢?我还在想怎么回答,犹豫的工夫里,已赋予他某种勇气,肩膀靠得离我更近了。你也看着了,我有点子儿。他盯着我的耳垂说,或许是盯着发梢、脖子,视线慢慢上移,在我布满青春痘的脸上短短逗留几秒后,更多地看去我身上。我目不转睛张望着麦当劳的门,期待塔米现在出现。他的运动鞋尖儿碰上了我的鞋,说,跟我玩儿去吧?去找个地方歇一脚。我说不去。他把脸又再转走,工作日的午后,烈日当空,是一天最炎热的时候,适合昏昏欲睡。齐得意将一双黑黢黢的手猛地压在我膝盖上,不止按压,还旋转,在我膝头狠狠揉搓了一把,说,又不差你钱。不都十八了吗,学也逃了,饭也吃了,还想怎么挣钱啊?我看了一眼街上,还有人,但没人留意这边,大家要么步履匆匆,要么欢声笑语,我沉入的似乎并非是齐得意的纠缠,而是又一度的,梦的纠缠。麦当劳的门开了又关,午餐时段已过,店里窗边座位上,一个始终抱头沉默的男人突然转脸过来。我一动不动,感觉齐得意的手正在我一些关节上挪移,他在用手上的力气试探我,告诫我,你已经死了,你没有知觉,知觉都是假象。太过宁静的世界总给人一种布景板的感觉,眼下我们正在拍戏用的摄影棚里。窗里的男人盯着我,嘴惊讶地合上,又张开。焦点娱乐平台
我猛地甩开齐得意,在大街上疯跑,穿过友谊路上的人行地道桥,直跑过了防洪纪念塔,终点是斯大林公园,再远就是广阔的江面。我不知道自己跑得是不是够远了,在走向一辆空车之前,鬼使神差地先走进了一家专卖俄罗斯小玩意的商店。架子上一排排色彩缤纷的套娃,像一排保龄球,大差不差。我看了会儿,突然决定买一个。打上车后,我一人坐在后排,慢慢拆解那只套娃。直拆到了里面一个最小的,只比我的小拇指盖大一圈。我将这个最小的套娃收好,揣进裤兜,和来时一样看着窗外,想到塔米,想她会找不到我的。可她的身份证、车票都在我这里,回去的车是下午四点半,还有两小时。我们会在车站见到彼此,对吧?默默坐在候车大厅里,我看着挂钟上秒针弹跳的样子,想象塔米此时一屁股坐到了我的身边,她会露出松口气的表情,再捶我一拳头。她会说,怎么不叫我一起跑?我会如实告诉她,我害怕。捏着裤兜里最小的套娃,手汗沁出来,在上面形成了第一道包浆,心乱如麻。发车时间到了,塔米还没有出现。我跟随人群,排队,呈上车票,人堆里陌生的气味儿搅乱了我的思绪,陌生人的脚在后头紧踩着我的脚印,感觉只能不断向前,四面都堵塞,只有往前,这一个方向。上车后,我还是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对面却换成了个抱着婴儿的少妇。我们面对面看了一眼婴儿不时发出闹钟般哭叫的脸,它一直哭,来提醒别人注意它,勤着注意它,一直注意它。我想去厕所洗把脸,可列车员过来说,要发车了。站台上,送站的人逐渐离开,只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固定的位置,面无表情等待发车的讯号。我们都面无表情。我无法再想象塔米,却忍不住在想,想她能否在最后一刻跳进车厢,气喘吁吁,跳到我的面前说。她会说,你可真不够意思。没有她,没有人出现,只有婴儿在哭,火车行驶的震荡声稀释了一切的变化。焦点娱乐平台
家里没人在等我,周遭就和我每日放学进屋时一样没有改换。我发愣地看钟点。给塔米家里打了十来个电话,始终没人接,我甚至怀疑她给我的电话号码是不是假的。窗外夜已沉了,家中只有我的卧室里亮着灯,时间静谧没有响动,像个死物。电话终于响了,我跑到客厅里心虚又兴奋地接听,却是母亲打回来告诉我,她和父亲今晚有饭局,要晚回来。问我的晚饭是不是也集体解决了,我怔怔说是。这一刻我谁也指望不上,如果娃娃们在,也许我还能匍匐到她们周围哭一场,在心里倾听她们琐碎却清晰的八国语言,我全可解读,也全部受用,我们的交流全赖一种神力,是她们选择了我,赋予我这一种神力。可她们也不在了。世界的摄影棚里,工作人员都已回家。焦点娱乐平台
倒是陈朴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讲电话时声音很小,估计是躲在自己卧室里,我们所有的交流总是断裂又鬼祟。听他说话的时候,我手里捏着那个花生仁儿大小的套娃,像捏着我自己的模型。他问我今天都去了哪里玩儿,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我盯着书桌上那个唯一在家里发亮的护眼灯的灯泡说,我们碰上了一个流氓。流氓?陈朴怀疑地问。灯泡盯了一阵,眼前又有无数的色块儿,这次色块仅仅是色块,没有梦的召唤和前后呼应。我不让自己的眼睛离开对灯泡的注视,仿佛一旦退缩了,就连自己犯下的错误都不可直视,更别说日后能被谁原谅。我说,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流氓。他请我们吃饭,带我们逛中央大街,但是他很坏。他捏我的膝盖,手劲儿很大,他是个干力气活的工人;还给我看了他兜里有多少钱,说他想在我身上花掉一点钱。他非常坏。陈朴问我,塔米呢?塔米不是跟着你?我说,塔米中途回家了。她应该是回家了,我们中途走散了。陈朴在那胡猜,问,你们闹矛盾了?我对电话摇头,说没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她怎么回事。他那边似乎有人来,讯号被断掉一阵。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我们都不能防备什么时候就此失联。换成小怪兽和塔米会怎样呢?小怪兽会直接要求见面的,自由如他们两个,见面总是很容易。就算被家长老师抓到了,也没人拿他们有办法。没人拿有主意的人有办法。我在心里念着绕口的一句话,等了一会儿,等到一条陈朴的短信。他说,我妈刚才进屋了。他在信息里安抚我,乖?我默默说,乖着呢。拿座机又给塔米家打了两个电话,无人接听的嘟嘟声中,陈朴问我,人呢?我说,陈朴,我给你带了东西的。你猜是什么?他发了个微笑的表情,后面跟着问号。我看了眼桌上的小套娃,它已脱离母体,它的母体就在我带回来的背包里,我没有去把它拿出来把玩的渴望。我说,一个俄罗斯套娃。隔了约十分钟,他回了句,喜欢啊。在这十分钟里,我又给塔米家打了五个电话,给班主任打了一个。班主任没接。匍匐在满是书山题海的桌子上,我哭了喘不上气的一大场。焦点娱乐平台
父母还没有到家。昨晚一夜没睡,加上一天的奔波,我在等待中不知不觉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又再听到了《归人沙城》这首歌,之前除了听塔米唱过,并没其他的印象。梦里也是塔米在唱,她坐在一块黑色的礁石上,光着脚,像我之前形容给她的那个遇见自己死亡的画面一样,双腿放松,荡秋千一样晃着,偶然打起的浪花拍湿了她的腿和脚。天空看不清白天还是夜晚,也许是黎明,远处有昏暗的雨云。我从未见过海,一步步走向塔米,也脱了鞋子,让双脚感受绵软的沙的触感。塔米突然停下不唱,盯着我道,别再往前走了。我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走近你?我们应该一起回家的。转过头来的塔米换了一个发型,改成梳两条棕色辫子,不知她什么时候染的发,学校不允许,但也许会允许她,谁让她是塔米。她指给我看,就在我约莫再走两步就到的地方,立有一个沙堆。我小心翼翼凑过去,蹲下来瞧,那是个小巧而精致的沙堆,俨然艺术品,不,是座沙的城堡,像微缩的一处遗迹,某个不知何时消失在了历史风沙里的古城池。塔米说,我堆了无数个日夜。我说,怎么可能?你每天都和我一样去上学。塔米说,别用你的想法判断我;我说能行,就是能行。要不是我堆的,你考我,我怎么知道沙城上左侧三个窗户,右侧五个窗户?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外沿,天色晦暗,窗子数不清,得靠摸的,果然也都叫塔米说得对。她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那块礁石,越走越远,也许就在我数窗子的时候,不信她的时候,她已没一丝留恋走远了。我跟她身后叫塔米,塔米的名字像一句对应风浪高低的咒语,很快有一阵黑色的浪头打来,冲垮沙城,淹没我的上肢。我努力求救,水下突然出现一双手,将我托起,让我的头露出水面,能大口大口喘气。抱着那人温热有力的身体,我双脚也纠缠他,摩挲去脸上的水,与他四目相对;却是齐得意的脸。他紧箍着我的身体,感觉我们生而一体,听他在我耳边悄悄说,开个价吧,小怪兽。焦点娱乐平台
塔米看着我,怎么了你今天?我好多次在上课时忍不住瞧身边的她,每次她都注意到,因我看她比看黑板更专注,让人难忽略。本来以为,第二天去学校时,我身边只会有个空荡荡的椅子,我还会因最终受不了良心上的谴责而找到老师,坦白昨天发生的一切。可塔米还是如常出现了,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在课堂上认认真真记笔记,偶尔举手回答问题。课间她打开自己桌前的本子,继续在上面记录一行行歌词,拿一只手捂着,怕被人看到。我在课间时更着魔地观察她,直到她忍无可忍,转头向我。我问她,你的刘海呢?她今天将刘海别到了头发上,额头上什么也没有,一片平坦和干净。那些青春痘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总不会是一夜之间,可我越来越相信这个答案,事实就是一夜之间,改换发生,梦境替代了真实。她从桌膛里取了些面纸,四下看看,问我去不去上厕所。我摇摇头,见她平静地起身,姿态女妖般优雅又轻盈。厕所简直像她一个秘密的藏身所,是她施展法术的地方,在哈尔滨,她就是走进了同样的地方,从此悄然消失。我想叫她,抬头瞥见她摊在桌上的笔记本,看到上面那句咒语般的歌词,以她细弱蚊蝇的字体哼唱,“沙河又在缭绕。”焦点娱乐平台
陈朴在课间来到我们班门口,托人带话叫我出来。我将送他的套娃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到他手上,陈朴笑嘻嘻地收了。看着他即将消失于人头攒动,消失于那些下了课从各自班里窜出来、无处可去的少男少女之间,陈朴的后脑勺即将消失。他早晚要消失在成长的单行道上,我们都如此。我突然很想追上去,在众目睽睽里将他拥抱。想象中,我是这样做了,想象中,他一定推开我,困惑地,为难地,你干吗呀?我说,陈朴,我昨晚做了个可怕的梦。我梦见自己在海边,涨潮了,把我身边所有一切都淹没,包括我自己。我希望救我的那个人是你,至少是我希望看见的一张脸。他说,你看见了谁?我说,我看见了那个流氓。记得吗?在电话里我和你说过的。陈朴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好像在摸他收下的套娃,轻轻丢下一句,少做点梦吧你。眼前任何人都消失了,课铃打过三遍,我路过班级门口没进去,走向走廊尽头的女厕所。厕所里没有镜子,老师怕我们在爱美的年纪里过于在意美丑,一面镜子也不安。我在白瓷砖之间来回兜旋,接水拍了拍脸。厕所里只有水流偶尔抽疯似的流淌声,静静听着,感觉就是缭绕的沙河了。塔米不在厕所里,她到底有没有和我去哈尔滨?我们又是否遭逢齐得意?如果一切都不曾发生,又在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焦点娱乐平台
我独自往教室门口走,发现走廊上一个男生在颠球,用他的运动鞋尖,一下下操控着球的起落。小怪兽木然地看向我,走廊上只有我俩,球滚去远处,能听见它顺着楼梯一级级向下蹦的声响。小怪兽穿着件大人的风衣,双手插进口袋,越走越近,越近越不像高仓健。我感觉自己被空气中某只拳头揍了两下,在他到来之前,身体已乖顺地靠在了墙上。我让你照顾她,他盯着我脸上的红豆粒问,塔米呢?我指指墙壁后头的教室,塔米在上课了,这节是她最喜欢的历史课,你听,她在读课文。小怪兽不置可否,非常丧气地蹲下,抬头以困惑的眼神看我。我知道他不信,我也有不相信的事,在十六岁那一年,我很难说对什么事情是相信的,只感到海浪一直在冲刷,而身体里一切感官,皆如泥水中的沙城,每块砖瓦都危机四伏,无力自保。小怪兽向我招招手,示意我也蹲下,我发现他脸上有眼泪滑过的印痕,他眼睛一眨也不眨,好像我才是塔米。焦点娱乐平台
塔米呢?他又问了一遍,我只是咬紧牙关,即便在我心里有无数个答案,即便无数个答案每一个都像是真的。我不能告诉小怪兽,我把塔米留在了哈尔滨,他一定只信这个,信我从裤兜里掏出来的车票和身份证。临时身份证上黑白的塔米的肖像,像被人关进了壁橱,或藏进了口袋。我从来也不曾了解她,她也没给我机会。我们都只能了解时间准许人了解的事情,小怪兽,你听到没有?他又陪我默默蹲了一会儿,我们不再说话,一直挺到下课,我一直等待着某个气急败坏的人出来寻找我的缺席,谁也没有出来找。世界以陌生的方式开拓着,如死后,如一座大宅里无数的空房间,一扇扇去推门,路线蜿蜒又闭合。此时下课的铃声在我耳边咒语一样回响,也响在所有房间的墙壁上、砖缝里,响声伴随风里的砂砾,冲刷上岸,缭绕不绝休。焦点娱乐平台
焦点: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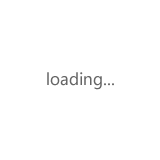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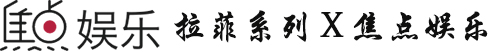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