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快讯:
人们惊奇地发现:事情并未变得更糟。
——阿信《经幡隧道》
拉鲁,一座汉藏交界的小镇——对此我也并无太大的把握。所谓“交界”,可能事关行政区划,还事关深奥的民俗学,而我,不过是凭着直觉作出了轻率的结论。
喏,它有一个藏语镇名,也许不是,但一目了然,镇上的人基本都是汉族,尽管他们也有着特殊的古铜色皮肤,不少人手里也常年攥着油光发亮的念珠。站在镇子任何角落,不用极目远眺,就能够张望到迥异于汉地的风光。众神逍遥的草原;远在天边却轮廓分明的雪峰;经幡,万籁俱寂时,你听得到它们在风中猎猎作响;当然,还有点缀在山坡上一动不动的牦牛。这一切,近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如同我当时的处境——没被什么明确的界线阻隔,看上去迈开腿就能一往无前地走向风景深处,但却有巨大的斥力令我踌躇难前。
晨昏之际,九月的高原已有了寒意,下了雨就尤甚。我在镇上逗留了一月有余,住在一家有着白色墙裙院子的小旅馆。房间的四壁涂抹着光滑的涂抹着水泥,让人不禁叹服泥瓦匠的手艺;老板是个看不出实际年龄的男人,说话时总要不断地交叉和分开手指,他给我生了炉子,烧整段的松木,让我的身上也散发出了木头焚毁后的气味。
入住第一天我就引起了镇上人的注意。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能感到他们被好奇心驱使的热情即将燃至沸点。这让九月里已经有了寒意的高原都显得燥热。有天我在镇上唯一的街道踽踽独行,斜刺里冲出一个小孩,目标明确地给我下了个绊子。我还算敏捷,踉跄一下,并没栽倒。街边几个男人用得意的大笑告知我,这正是他们策划的一个小把戏。是啊,他们受不了啦,一个单身女人,动机不明地来到他们的地盘,摆出一副长期扎根的架势,究竟是为了哪般?一周后,这种小把戏就层出不穷了。只要我在街上露头,便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故发生。像是一场小小的狂欢,我觉得他们倒也没什么恶意,不过是唆使小孩冲撞你一下,吹吹口哨,或者突然在你身后引吭高歌,也不知道想要收获礼貌的赞美还是惊慌的呵斥。我多少有些歉意,觉得自己的确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活,给大伙制造了没来由的疑惑。焦点
可我该如何平息他们的焦灼、打消他们的困惑呢?没办法,我总不能告诉他们:千里万里,这女人一路向西,只是为了寻找一位莫须有的藏族汉子。对此我自己都难以确信。我连那汉子叫什么都不知道。
结果镇上的人干脆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她是来收藏獒的。”我在街上开始听到这样的议论。有人很大声地宣布,分明就是说给我听的。继而,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宣告大家达成的共识:错不了,几年前不就老有东北人来干这买卖吗?好吧,既然如此,这可以当做是一个定论,因为白山黑水,我还真是从东北来的。焦点
一切好像名正言顺了,但我还是感到窘迫,尽管走在街头,我已经都不自觉地摆出了一副狗贩子的气派。实际上,我知道自己有多心虚。日甚一日,令我窘迫着的,是对自己的质疑:所谓的藏族汉子,不过是你在飞机上的一个邻座,简单的交谈,大约也就三五句吧,使你记下了“拉鲁”,时隔三年,心事懆懆地循迹而来。你不知道他叫什么——他肯定是说了,但随即被你忘却,可见并未走心;你不知道他究竟住在高原上哪一顶帐篷里——他放牧,住帐篷,这差不多就是那三五句话里全部的信息;你只知道,他身上的气味压根不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那么,看上去你就是个疯子啊。这并未给我增加额外的痛苦,只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处在分裂的困境里。表面上,我的行为姑且可被视作一个女人轻率而任性的盲动之举,但内心深处,那个讨厌且顽固的理性又会不时地跳出来,以一种堪称残酷的尖锐,对我进行人身羞辱,让我将自己的荒谬与可悲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刚刚遭到了背叛的女人,丧魂落魄,既要忍受着自怜的折磨,又要克服着自戕的冲动,甚而还怀着某种古怪的欲火。她不惜以身试难,巴望在一场极端的行动中一劳永逸地解决自己。没错,就是解决自己,而不是解决问题。焦点
那个三年前在旅途中偶遇的藏族汉子,我只记得他只是有些凛冽的气味而已,但他却无辜地成了我的目标。我妄想找到他,在找到他的过程中,一股脑地解决自怜,解决自戕,解决欲火和解决自己。这番妄想能让我在某种扭曲而非凡的、自大的美感中获得满足,继而重拾一点点经不起检验的自信。
然而,来到拉鲁我却像是来到了世界的尽头。这个尽头,不过就是我全部能力与全部见识的边际,我的情感,我意气用事的蛮劲儿,以及既往对自我与世界的所有把握,到此都已穷尽。也许是累了吧,我分明是泄了气。总之,在拉鲁张望既近且远的草原,我只能裹足不前。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限度。这个限度决定了我即便已经认定自己陷入了落难者的悲惨绝境,也只能在假象中对世界来一次抗议或者冒犯。那个启程时被一腔情绪注满、如同一个充饱了气的皮球一般的女人,意志萎靡地卡在了这块“交界”之地。
计划到此几乎是终结了。“找到一个气味凛冽的藏族汉子”这个鼓舞人心的目标,渐渐变得不那么确凿了。可我不知道该去向何处,滞留在此,每天无所事事,惶然间,还真的有点将自己当做了一个来自东北的、收藏獒的女贩子。当我从小旅馆出来,我会刻意给自己扣上一顶中性的遮阳帽,并且将丝巾在脖子上打出很短的结,那样子,是我从某些西部片里借鉴来的。在那类电影中,牛仔们都是这种架势。焦点
后来发生的事情,竟真的让我进入了一个狗贩子的角色。我确信,对我而言,那是殊为重要的一天,它令我在31岁的时候,于刹那之间扩展了生命的意志。说得更准确一些就是:我因之拥有了片刻的、真正的自由,成了一个不再苦受命运摆布和宰制的人。
那天中午,我被小旅馆的老板从午睡中叫醒。他趴在窗户上兴奋地朝我喊“来了,来了”。当天清晨下了半个小时密不透风的大雨,一个早上都被我用来写信了,那是一封非常消耗人心力的信,我写得很艰难,但最终又将其撕碎扔掉了。我原想让收到这封信的人感到一头雾水,结果却把自己写得一头雾水了,就是如此。所以此刻我还陷在梦碎与信碎后的双重困顿中,费了些劲才大致听明白,老板是在告诉我有一头流浪的藏獒窜到了镇上,并敦促我现在就挺身出马,将其一举拿下——“野狗还能让你省一笔钱呢。”我的确是没睡醒,对“流浪的藏獒”与“野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辨析得并不是很分明。我只是估摸着觉得,前者似乎有些美感,而后者,则意味着凶残。但老板的意思我算是听明白了,他是在严肃地向我指出:对于一个狗贩子而言,逮到一条野狗不啻为捞到了一笔。焦点
焦点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被一种强大的、逻辑的力量推搡着,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走了。出门前,我照旧给自己扣上了扮演牛仔的遮阳帽、系上了丝巾。就是说,这时候,我不过是在一个给定了的角色里行动。
小旅馆的门外挤了不少人,由于清晨的那场大雨,大家都穿上了大衣。而我却还是傻乎乎地穿着一件白衬衫。看到我,他们就激动地向我宣告那是一头多么可怕的大家伙。它是一头流浪的藏獒,或者干脆说,就是一条野狗。“全是让你们东北人闹的!你明白了吗?这是你们惹下的祸!”一个肯定是刚喝了青稞酒的男人一边给自己编着辫子,一边酒气熏天地冲我抱怨。理由是:数年前藏獒的价格不菲,“你们东北人”蜂拥而至,哄抬了市场,于是,草原上质朴的藏族同胞大量饲养起藏獒来;现如今行情大跌,獒场破产,无数的藏獒便沦为了野生的流浪狗。它们成群结队,浪迹于广袤的牧场,与天斗与地斗,既攻击野狼,也攻击牛羊,物竞天择,竟酿成了生态的灾难。我茫然地听着,神思恍惚,但也依稀感到了一丝愧疚,好似对于这番糟糕的局面,这个烂摊子,我委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种自罪的心情,一段日子以来,恰好也正是我这弃妇一般的心情。焦点
大多数时候,野狗是不会闯进镇子里来的,它们恪守着大自然的秩序,自觉地归属于自己的领地,即便沦为了野生的物种,也绝不轻易穿越人间。于是结论就有了:这不仅仅是一头流浪的藏獒,一条野狗,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一条疯狗,一头失常了的猛兽。拉鲁镇上的汉人对它束手无策——至少,这是他们着力想要渲染给我的。他们像告状一般地对我数落:这家伙趁着大家午睡的时候咬死了两头牛,毁掉了好几家人的猪圈,现在,险恶地盘桓于镇子中央的小学门前,正伺机要冲进去。
一边说,一边走,我身不由己地被簇拥在了一支队伍的前列,俨然一位飒爽的领头人。大伙都兴高采烈,急着想看我如何手到擒来地拿下一条疯狗。小学门前,两个镇派出所的警察居然也像是在恭候着我。他俩都垂手拎着警棍。我认为他们肯定还怀揣着枪。你知道,小镇上的警察其实与老百姓的区别并不是那么大,就算穿着制服,你也很容易将他们与群众混淆在一起。在我看来,他俩和所有人一样,都穿着军大衣,都有些笑嘻嘻的。所有的人都不紧张,顶多是装得有点紧张。周遭的气氛有股默契,而这股默契让我感知到了自己的孤立。我并没有看到一头流浪的藏獒,或者一条野狗。我只看到了一个恍恍惚惚、不知所以然的自己。焦点
午后的高原空气干爽,万物都过分地清晰,一切好像忽然间定格了。我的意识也有瞬间的空白,整个人都是失重着的。直到天空飘来大块的乌云,随着光影的变化,地上的人群才复苏过来。大伙开始议论藏獒的下落,夸大其词,七嘴八舌,统一后的口径是——跑了。我在拉鲁住了段日子,多少习惯了他们的语言方式,就像现在,他们用一个动词简洁地替代了名词。那失常的猛兽,它的去向不是朝东也不是朝西,而是朝向“跑了”。这令一切仿佛子虚乌有,或者是一个传说,那疯癫的藏獒是否真的来过都令人怀疑。
我正努力确认是否身在梦境或者一场恶作剧之中,街边一家杂货店的背面冲出个惊慌失措的妇女。她一头扎进了人群,双手高举,对着天而不是对着人大声地吁求:“看看吧,看看吧,看看我都倒了什么霉!”她的嗓门极富动员力,搞得所有人都跟着她抬头向天。那块很大的乌云依然悬在天上。高原上的乌云即使很大,也不会遮天蔽日,因为高原上的天实在太大了,所以乌云之外的天空反倒会被衬托得愈发明亮。就是这样,在高原,所有的乌云仅仅只是你“头顶上的乌云”。
镇上建筑的布局都是前屋后院,我被人群裹挟着绕过杂货店的门脸,在木头围出的院子中看到一头庞大的动物死尸倒毙于烂泥里。我挤在人堆,经过辨认,确定那是一头牦牛,一头身长足足有两米多的大牦牛。可能是它倒毙的样子无端放大了它的体形,在我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具世界上最大、最不可思议的动物尸体。之所以需要先辨认一下,只因为它的头不见了,脖颈被撕裂出一个空洞的血窟窿,实在不太能让人一眼看出是头牦牛。好吧,看看吧,看看吧,那失常的猛兽咬断了它的脖子,还叼走了它的头。焦点
下意识地,我用眼睛寻找小旅馆的老板。他是我在镇上唯一的熟人,我需要被保护。这一刻,我不再是那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落难者了,我感到了冷,感到了穿着件衬衫挤在一群大衣之间的不合时宜。回到了所有女人面对一头死牦牛时应有的恐惧中,那些所谓背叛施加给人的伤害,在一头实打实的、没了脑袋的牛尸面前,好像一下子无足轻重了。但我找不到我的老板。没错,他是我在此地唯一的熟人,但挤在一群人当中,我就辨认不出他了,因为我压根看不到有谁的手指在不断地交叉和分开。这群人开始蜂拥着往镇子的东边跑,因为那个向天吁求的妇女开始往东边跑。作为苦主,现在她替代了我的角色,成了领袖。她一边仰天呼号,一边发足狂奔,充满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大伙没有理由不紧紧地跟从。
我又一次被遗弃了,只有和这支人间的大部队背道而驰,朝着镇子的西面跑去。我落脚的那家小旅馆坐落在小镇西面的边缘地带。现在,拉鲁镇的人不需要我了。也许他们只是想看到一个女人徒手降服一条疯狗,至于这位天选之人是谁,他们并不在乎。对他们而言,这好像也是人之常情;那么,被我视为生死荣辱一般重大的背叛,是否也可算作是人间的常情?这类念头当时在我心里并非条分缕析,我只是忽然获得了一些置身事外的解脱感。至少在那一瞬间是这样的,所有的,都无所谓了。焦点
我用手扶着自己的遮阳帽,一路小跑着奔回小旅馆。宛如拥有了一种俯瞰的视角,我看到,在这九月的高原小镇上,一个乔装打扮的女人沿着窄街仓皇而凄凉地独自跑着;随着视角地不断升高,小镇被漫无边际的草原淹没;继而,大块的乌云遮住了地上的一切,但从乌云的上方来看,那大块的云朵却因反射了猛烈的阳光而令人倏忽目盲。
那头藏獒站在炫目的光里。我一脚迈入小旅馆洞开着的大门,就看到它雄踞于四面雪白的墙裙正中,宛如光芒四射的王。

弋舟,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小说专业创作委员会委员,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历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焦点: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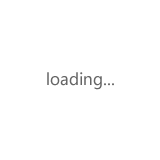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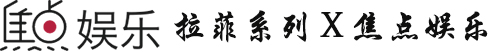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