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登录发布:
暴雨被风卷着如斜扯的布匹决裂开来一般,摔打下来,飞溅起无数的泥浆。世界一片苍茫。院子里混混沌沌的,雨幕遮蔽着人的视线,看不清远处。一会儿,院子就蓄满了水,地上被激起无数的水泡泡。那些汇集起来的雨水慢慢地,最终恣意汪洋般流向那低洼的地方。
一个火焰般的闪电过去,紧接着炸雷就像从头顶猛劈下来,随之雷声如黑山碾米的碾道里被拉着转动的石磨一样,咯噔噔,咯噔噔,唬人地在向山的南面滚了过去,又滚了回来,让人胆战心惊。男人章永旺问:“娃娃们不知道安全着吗?”
女人说:“大的几个都到砖瓦厂打工去了,砖瓦厂应该都安全着呢,小的伊斯哈格还在红山羊村小学念书没有回来,在学校里有老师应该是安全的。”
老章说:“你把我的伊斯哈格惯坏了,都那么大了,整天还骑在羊背子里。羊能驮动吗?把羊都压死了!”
小儿子伊斯哈格整天骑的这头雪白雪白的母山羊,其实是伊斯哈格真正的奶妈,是它把伊斯哈格一直从婴儿哺养成一个走进村小学的少年儿童。就是读书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偷偷嘬山羊妈妈的奶,惹得家里外面的人都笑话他:“不知道羞,多大的人了,还吊在乳头蛋子上!”
伊斯哈格去学校的时候,骑马一样骑着自己的奶妈白雪,白雪就是那只母山羊。在学校里,他把它拴在学校教室后面的一片草坪上,那片草坪的辣辣草、苦苦菜、枯籽蔓、短冰草长得多。羊笼头的尼龙绳似乎有意放得特别长,绳头上绑有一个尖尖的木橛,为了牢靠,不致白雪跑丢了,伊斯哈格找一块石头把木橛砸着深深钉入泥土深处。白雪会抬起头看看伊斯哈格,仿佛明白他要去教室里干什么,伊斯哈格只轻轻叫唤一下,它就变得乖乖地自顾吃草去了,不再跟随和追赶往教室里跑去的伊斯哈格。焦点平台
一放学,伊斯哈格就跑到教室后面山坡的草坪上拔出木橛。白雪已经吃饱了,在静静地等待着。伊斯哈格把绳子绕到胳膊上,绕几圈,爬上羊背,骑在羊背子里,双手抓着山羊向上且略向外弯曲的双角,跟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一样回家去。
学校老师发现了那只白山羊,知道是谁带来的,很宽容,没有责备,因为那只羊非常有灵性,在学生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叫过。
在伊斯哈格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兰芝就用双手抱着把他架在白雪的背子里让他把白雪当小马骑着玩。每次妈妈抱着伊斯哈格嘬完羊奶,就让他骑一会儿白雪。伊斯哈格在羊背子里,抓着羊妈妈蓬松柔软细腻的羊毛,乐得一边打着奶饱嗝儿,一边呵呵呵地笑得娇甜。
等到伊斯哈格上小学三年级,羊妈妈已经驮不动他了,他也变懂事了,知道心疼自己的羊妈妈了,就只是牵着羊的笼头,羊就踩着小碎步,欢快地跟着他行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这只毛色雪一样洁净的母山羊陪伴着这个东乡族孩子一天天长大。焦点平台
兰芝突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说:“咱家哈格,都上三年级了,还连一双鞋子也没有,时常精脚片子,脚上到处都扎得烂烂的,一到晚上我拿钢针给娃娃脚上一根一根挑刺棍。冬天那双小脚冻得烂得没眼看,我给脚片子挤出许多脓水,再用棉花烧成灰给流血流脓的地方止止血。你一个当场长的大,把娃娃也管管,你跟个驴一样,光寻驴驹子,却不管驴娃子!”老章就嘿儿嘿儿地笑,说:“等我什么时候去县里,给我娃买一双黄球鞋。”
片刻,雷声就又缓缓地滚远了。听着头顶上的炸雷转来转去时,老章和女人觉得一台石磨子从心头压过来压过去,内心忐忑不安。但一声声沉闷的炸雷刚响过,更加吓人的冰雹又铺天盖地一般砸下来。顿时,门前几棵杨树上的叶子被一扫而光。冰雹落下的声音听上去就跟巨型收割机在迅速地收割着地上的粮食,嚓嚓嚓、嚓嚓嚓地响着,就连碗口粗的树也被齐刷刷地打折,倒在了地上。整个村子变得惨不忍睹,山上有些人种在阴洼田地里尚未来得及收回的庄稼被冰雹打得贴在地上,有一部分干脆被砸进泥里面去了,连头尾都找不见。没办法,农民们只好用犁铧把它们翻耕进土地里充作肥料。焦点平台
章永旺家院子靠近大门洞流水的地方,被冰雹疙瘩砸出了一个深深的大坑,里面顿时注满雨水。房上的瓦就像无数的鸡蛋掉在了上面,发出一种古怪的刺耳的碎裂声。但是,令人诧异的是,这些冰雹却没有使一些岌岌可危的房屋倒塌,也没有把那些瓦片全部砸碎。红羊村人建造的房屋,就跟这里的人一样,善于承受一切世上的考验和磨难。只一刹那的时间,冰雹疙瘩在地上就铺了白茫茫一片。
章永旺说:“咱们这里生态破坏太严重了,干旱的时候,一点子雨都不落,到收粮食的几天,就下起雷阵雨,不是羊眼珠子大的密密麻麻的冰雹,就是鸡蛋大的冷子疙瘩,把人可害惨了。”
妻子兰芝说:“可不是嘛。”
雷雨过去了,天慢慢转晴,太阳从西南边露出来,到处跟雨水洗过一样清新自然。
中午,在班主任李长徳老师的帮助下,伊斯哈格把母山羊牵进教室里和同学们一起避雨。那些娃娃们有男孩也有女孩,都把手悄悄伸过去摸母山羊的毛,还有人去摸它光滑的石棍一样耸立的略微有点弯曲的羊角。伊斯哈格感到非常自豪。孩子们一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各自带了土豆和玉米面甜馍馍。玉米面甜馍馍就是在玉麦面里面适当掺和一点野生的马灰条籽儿,这样做出来的玉米面甜馍馍,油浸浸的,不仅香甜,还非常顶饱。娃娃们大多数吃的这个,再吃两个煮土豆,喝一马勺老师宿舍洋皮提桶里的凉水,中午这一顿就算是对付过去了。白山羊往往到晚上回到家里才给饮水。焦点平台
晚上,伊斯哈格牵着白雪山羊妈妈回来了,兰芝赶紧到石槽里用铁桶倒了些水饮羊。母山羊喝得咕儿咕儿响,肚子上那个窝窝逐渐像一个球体一样饱起来了,最后羊变得圆实,就像一个吃饱后有点慵懒但贤惠而又温柔成熟的妇女。
兰芝到伙房挂在房梁的馍馍笼子里拿下半块玉米面甜馍馍,走出来塞给伊斯哈格。伊斯哈格把甜馍馍掰成两半,一半给哺乳过他的白雪妈妈。一直都是这样,兰芝从不指责儿子,她觉得没有这只母山羊就没有这个儿子。
生伊斯哈格的时候,村子里接生的田奶奶让章永旺在门口等着,让他在窗户外面听着,也可能是他没有听清,以为是田奶奶要他把伙房烧的热水端进去给新生的婴儿沐浴,孩子没生下来他就闯了进去。后来伊斯哈格生下来,兰芝竟然没有奶。田奶奶非常愤怒,指责章永旺,说:“让你别进来,别进来,你干吗闯进来?现在你女人的奶水下不来了。没有奶水,咋办呢?你赶紧想办法去,看看村子里谁家女人生了娃娃,有没有多余的奶水,让你家娃娃先吃上点,把命保住。”
章永旺在村子跑着打问了一圈。他平时在牧场里工作,不常在村子住,也不知道谁家的女人在哺乳期,就是问到了,人家掌柜的不一定能愿意。有一家女人有,人家的男人说:“奶好像也不多,我家娃都不够吃,哭哭啼啼的,把疝气也挣下来了,他奶奶给用艾灸往上灸呢。”焦点平台
这时,章永旺听说马六舍家有一只奶山羊,刚下了一只小羊羔,羊羔下不下来,被马六舍硬拽了出来,羊羔子死了,母山羊失去了孩子,失魂落魄一般叫唤着,奶一胀叫得更凶。章永旺的眼睛一亮。他去马六舍家买羊奶,说:“快呀,我们家的娃娃就要饿死了,给我买上点你家的羊奶吧,看能把我家娃娃的命拉扯活吗!”
马六舍二话没说,就给挤了一碗山羊奶。章永旺给钱,马六舍说:“都邻里邻居的,要啥钱呢!”章永旺端着羊奶慌慌张张跑回家用勺子给儿子一点一点喂羊奶。伊斯哈格就是这样吃上了羊奶。但是经常去人家马六舍家里要奶,人家一直不要钱,回数一多,章永旺就不好意思了,干脆跟马六舍商量:“他爸,你行行好,干脆就把你家的这只母山羊卖给我算了,这样我家娃娃就有奶吃了,不然经常打扰你,也不是个办法。”马六舍听着这只失去羊羔子的母山羊白天黑夜没命地叫唤,也有些心烦意乱,就说:“那就卖给你吧!”章永旺付了钱,把母山羊牵回了家,并给它取名白雪。自从有了母山羊,伊斯哈格再也不愁没奶吃了。后来,兰芝就抱着小儿子在母山羊肚子下面吊着吃羊奶。从此,母山羊成了伊斯哈格形影不离的伙伴,等于他的命就是母山羊救下的。每次,伊斯哈格吃馍馍时,都要给母山羊妈妈掰半块吃。就这样,伊斯哈格和母山羊一起玩耍,一起到山坡上摔跤,一起赛跑,他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焦点平台
红羊村太干旱了,找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到处都干透了,植被被破坏得十分严重,因为大家缺柴禾,把草都又铲又扫,当做柴禾烧了。
章永旺就把白雪用绳子系在自行车后尾架子上,拉着去了后躺牧场。因为那个牧场靠近大山,水草丰美。章永旺把白雪拴在宿舍后院的一个土圈圈子里面,亲自拔草喂养和照料。
有一次,男人回来了,晚上女人说:“咱们好久没一起扯磨(聊天)了,你每次一走,成年累月在牧场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你枕到我胳膊上来,让我听得清楚些。”男人说。
“这么近还听不清吗?”女人嗔笑着。
男人嘿儿嘿儿地笑,说:“男人,难认,认不准,一辈子就瞎了。你找了我,真把罪受了,也撇在家里把苦下了。”
“这就是我的命,你只要在外头心里能记着你的娃娃们,我就心满意足了。”
男人说:“咱们的伊斯哈格,这个娃娃刚生下时真的差点饿死了,若不是那只母山羊就真的饿死了。”焦点平台
“母山羊现在怎么样啦,你儿子经常嚷着假期要去后躺牧场看他的羊妈妈呢。多好的羊呀!有一次,你儿子梦里梦见他的羊妈妈被狼吃了,那个哭呀,把我听着都惹伤心了,我听他在梦里哭着喊‘羊妈妈、羊妈妈’,听他对一只羊这么爱,都要落泪了。”男人说:“万物一理嘛,人呀,猫呀,狗呀,马牛羊,样样出气的物儿,时间长了,都会生感情的。”女人点头说:“你啥时间把儿子的羊妈妈带回来让他看喀。”
老章像是陷入沉思,思考了一会儿,慢慢地说:“没有白雪,就没有咱家的这个儿子。”
“是啊。暑假,让儿子到牧场里去看他的羊妈妈去。”“好的,山羊好着呢,后躺牧场那边的草好,羊变得更壮实了,精神着呢!”
“刚说让娃去你们的后躺牧场呢,可娃娃可怜着连一双鞋子也没有,让人说起来娃有个当干部的大呢,竟然连一双鞋子也买不起,你让娃羞着咋去牧场呢?要是碰见你们场里的职工干部都不好意思的。人家要是说‘这就是场长老章的儿子吗?脚烂得像刚从战场上吃了败仗下来的’,说心里话,娃娃会自卑的。”
“我有机会到县上开会时,给娃娃买。唉,现在我的负担还重着呢,两个大的儿子,眼看马上要娶媳妇了,得给攒钱说媳妇啊!”
“你还说呢,现在说个媳妇子,你以为像我那时候那么容易呢,就那么白领着来了。现在的说头多着呢,刚几大件就要了人的命,什么自行车、缝纫机、录音机、黑白电视,你说你那两个瘦工资,一月连不住一月,鸡沟子里等着掏蛋,能顶啥用?你看看人家那些人,不知道咋回事,只要沾住公家的边边子,几年就富着翻过了。可你工作了半辈辈子,给娃娃们啥事都没解决。看看和你一块工作的马凤山、马云波等几个职工的娃娃,你们商量着给人家的娃娃把商品粮都解决了,还给报了工人,你咋就不管自己的娃娃呢?为啥不给自己的娃娃报上个商品粮,报上一个半个工人啥的,你这个人咋老是胳膊肘子向外弯呢?我们娘儿们指望不上个你!”女人说着就哭了起来,眼泪多得擦不干。焦点平台
老章心里也特别难受,坐起来,在口袋里搜腾来搜腾去,找了一张旧日历上撕下来的纸,在中山服口袋里挖出一点旱烟沫子,卷了一根旱烟抽了起来。他说:“我这个人,从参加工作,就怕占公家的便宜,也不爱薅羊毛。”他突然有点生气,“有些人,你薅羊毛就薅羊毛,可是太过分了,不但薅羊毛,还把羊活活薅死,最后连羊也不见了,老百姓的意见那真叫个大。我们这层人,被公家教育成这样了,就是不爱占便宜,也不要谁来监督,不爱薅个公家的羊毛。上梁不正下梁才歪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点平台
兰芝说:“反正这辈子,我等你发财是没指望了,只要你平顺比啥都强。咱们赶紧睡吧,太晚了。”
兰芝就枕着老章的胳膊腕子睡了,很快就听见章永旺扯呼打鼾的声音。
暑假的一天,村子里跑新疆做生意的羊绒贩子老马回来了。他和老婆在炕上扯磨聊天,老婆说:“那个章永旺,现在还在后躺牧场当场长,还兼了书记,当了半辈子场长,娃娃一个都没工作,真是个老实人。”“那我去他家问问,看他家的人能不能引我去找章永旺把场里的羊绒便宜处理给我,我可以给老章提点成嘛,让他也发点财,不要那么一天苦哈哈的,把那个场长白浪费了。”
“那个人是个超子,养下的娃娃肯定也不打硬。”
“我有让超子变机捻(聪明)的办法呢,”他做数钱的手势,“有钱了自然就机捻了。”
老马到了章永旺家,兰芝在,听了老马的来意,说:“我们那个男人犟得很,恐怕办不成。”老马说:“只要把场里羊绒低价卖给我,我就给他一笔钱,不会亏他的。”
“你不了解老章,他不爱占便宜。”兰芝说。
老马不信,走了出去,在场院里看见放假正玩耍的伊斯哈格,他灵机一动,心想:再不贪财的人,总会心疼自己的娃娃吧,我把老章的儿子带过去,看老章给不给面子。他对光着脚丫子的伊斯哈格说:“娃娃,你过来一下,你想不想去你大的牧场里耍?那里的牛羊马匹一群一群的,就是个动物世界,我去那里收羊绒,正好带你去那里玩耍。”焦点平台
“太远了,我没钱坐车,又走不动路。我还没有鞋子呢,走那么远,脚片子会被扎成蚂蚁窝的。”
“我们可以坐班车去,车费我管上,只要你大能让我便宜收到羊绒,我保证给你一双好球鞋的钱,让你穿上球鞋,参加体育竞赛准得第一名。”
伊斯哈格一听高兴得跳起来,说:“我正好要去牧场看我的羊妈妈呢。”
“那还给你妈说不说了?”
“不说了,说了她又不让我去了,咱们去浪一两天就回来了。”
老马说:“好好好,说走就走。”
老马回去拿了个黑提包,还找了一些蛇皮袋子,用塑料绳捆绑起来夹在腋窝下,带着伊斯哈格先到堡子门前的公路上等班车。他们坐上班车沿着一条土沙石路走到土沟,在土沟卫生院门口下了班车,一老一少又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坐上手扶拖拉机拖车厢的沿子,抓住靠背那里的挡杆,过了一条大河的浮桥,向东面的一道沙石沟进发。这条沙石沟太长了,这一程路太远了,走得伊斯哈格着急。手扶拖拉机的水箱好像出现了问题,天气热得要命,太阳毒毒地在头顶晒着,一会儿水箱开始冒烟。司机是一个红脸老汉,他熄灭了拖拉机,提着水桶去找水,在一个山沟沟发现一眼细小的山泉,只提了不到半桶水,山泉里的水就没有了,那里只有比针还细小的一丝泉眼。羊绒贩子老马催促司机抓紧时间赶路,“赶紧走吧,雇了你这么个司机,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把人热死在路上了!”焦点平台
“你这个人说话咋这么难听,你不雇了,把钱给我,你们自己走着去。”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走了我给你个毛线你要吗?你不走了还要钱呢?你说你咋那么爱钱?”老马生气了。
那个红脸老汉脸更红了,不敢吱声,给水箱添上水,继续拉着他们前行。又走了一程,水箱又一次冒起了烟,手扶拖拉机再次抛锚,司机说:“让车凉一会儿吧。”老马嘴里骂骂咧咧的,说:“我这次咋雇了这么个东西,简直耽误人的事情呢。”
那个拖拉机司机年龄比老马大,红着脸,听到老马的骂声,无可奈何地摇着头,好像是在说,我这次咋遇上了这么个难缠的家伙,偷偷嘀咕着。
他们都从车上下来,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司机说:“水箱里的水不多了!”他说着爬上车轮胎,站上去解开裤带,向水箱里尿了一泡尿,老马也来了兴致,说:“你赶紧下来,你那个鸡儿一样的能尿多少,你看我的。”他爬上去站到手扶拖拉机的车头上,解开裤带,对准水箱的那个口口,挣着挣着尿,挣着挣着尿,好像尿不完似的,惹得那个司机捂着嘴笑了说:“你这家伙,比大河里的水还大!”伊斯哈格差点笑死过去。老马很得意,面无表情地笑了一下,说:“该到伊斯哈格了。”伊斯哈格快快站到手扶拖拉机头上,憋得面红耳赤,但怎么都尿不下来。老马说:“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黄鼠窟窿,你心里想着要把黄鼠用尿尿灌出来。”果然,伊斯哈格就真的尿出来了,但细小的尿流被风吹拂着,飘飘洒洒的,没有多少能够进入到水箱里去,但也就这样了。焦点平台
司机重新摇起手扶拖拉机,拉着他们又走了一程。因为是沙石路,车轮压上去就陷下去了,加上到处都是大石头,路不好走,只能走得慢,手扶拖拉机的水箱又一次黑烟黄扬的,看样子要着火,因为太阳快要把大地点燃了。司机说:“走不成了,你们下来走着去吧。”老马一看这情形,也觉得车不行了,就打发了司机,提着包包,夹着蛇皮袋子,领着伊斯哈格沿着沙石沟继续进发。
山谷里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地上的各种草木在日头的照晒下,无精打采和低头纳闷的样子。碧蓝碧蓝的天空,挂着几朵羊绒般蓬松的白云,大地裸露出它的奇形怪状和黄土高原的壮美。因为这里逐渐接近大山,路边布满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和面目凌乱的石头。一股燎毛蒿和百里香夹杂在一起的香味扑入伊斯哈格的鼻孔,伊斯哈格感觉香香的,但也有一种陌生的苦涩。沟两边的悬崖上爬满了藤蔓,一阵叫蚂蚱的声音从不远的一大垛子席芨草丛里传了出来。焦点平台
贪玩的伊斯哈格立即驻足谛听。叫蚂蚱一会儿叫,一会儿停,但那叫声实在是好听,伊斯哈格发现大自然原来是这么香这么奇妙这么美,他对那些野花野草闻不够,对那些大自然美声音听不够。“大叔,我能不能抓个叫蚂蚱玩?”
老马显得不耐烦的样子,说:“抓那个干啥呢,那是一个生命,害命得跟啥一样。咱们赶紧赶路,办正事要紧。”伊斯哈格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向草丛中张望,一边挪动脚步跟着老马前行。
老马五十岁左右,窄狭脸,黄眼仁子,还有一口黄板板牙。他对小伊斯哈格再次承诺说:“只要你这次引我把你大牧场的羊绒便宜收上,鞋子的事我保证了,说不定我一高兴,还给你再买一身新运动服呢。”
“那要是我大不同意咋办?”
“没事,生意不成仁义在,不成了,咱就当去牧场旅游了一趟子。当然,如果成了,少不了你的!”
伊斯哈格光着脚丫子,只能踮着脚尖跳着走路,生怕被砾石和刺棍给扎伤了脚。
老马看了一下,笑笑说:“不要紧,等咱们这次去你大的羊场挣钱了,给你买一双最好的球鞋,到时候,你个球子小娃可就要享福喽!”焦点平台
他们终于从沟里爬上了一个平台,到处绿树成荫,大片大片的杏树和杨树,茂密而接壤远山和云天。他们沿着一条通向场部的路,绕过林木,到达了后躺牧场的场部。那里有两排房子,都是红砖房,就是那种砖木结构的能滚雨水的小安架房。问了几个人才找到章场长的宿舍,门开着,里面却没有人,偏头桌子的台历上有场长章永旺记着的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比如今年哪个羊把式放的羊下了多少羊羔,被寒流侵袭冻死糟蹋了几只羊羔,增了几只羊羔,减了几只羊羔,羊绒抓了多少斤,卖了多少钱,粮食收成情况,打了多少粮,卖了多少,给羊把式和工人凑着发了多少工资,等等。章永旺的确是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
宿舍里还有一张木床,一床薄被子,几件章永旺的旧的蓝布棉袄和衣衫。伊斯哈格伏在衣服上嗅闻父亲身上的那种味道,他觉得温暖,感到熟悉和亲切,希望能赶紧看到父亲章永旺,还有他的羊妈妈。
大约过去半个时辰,可能场部有人发现章永旺房里有人,告知了章永旺。章永旺就回来了,一见面,章永旺就批评伊斯哈格:“你在家里不好好写寒假作业,不帮着你妈做点活计,跑到这里干啥来了?”
伊斯哈格感到特别委屈,说:“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吗?我看看我的山羊不行吗?”
焦点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这时,老马说话了:“娃娃来了就来了嘛,来了看看你有啥不好?你这个人见了自己的娃娃还不高兴啊?你没见你儿子看到你的衣裳,亲得趴在衣裳上嗅啊闻啊,亲成个啥样子了。你儿子不像我们家那几个娃娃,一点都想不起他老子,我一年四季在外面跑,他们也想不起我,我回去了也把我当空气。”焦点平台
章永旺听了,看看儿子,突然心里一酸,他是怕娃娃在路上受罪,“这一程路,还不把他累死,走一趟几天都缓不过来。”又笑着问,“你们是怎么来的?”
最后,老马终于说明了来意。
章永旺说:“你来迟了,两三天前来了一帮羊绒贩子,把些积攒的羊绒全收走了。”他顿一顿,又说:“你的好心我心领了,但不论卖给你还是卖给别人,市场啥价,还就啥价。我就这么个穷命,把原疤疤保住就行了。”
老马情绪低落,一脸不高兴,说:“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你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嘛,你不看咱乡里乡亲的面子,也往你儿子的脸上看嘛,你想办法再给我抓点羊绒吧,行吗?我也不占你的便宜了,你们对别人啥价就给我还是啥价,不能叫我白跑了这一趟。”
老章说:“我晚上问一下羊把式,看最近羊上绒的情况咋样。有些你们不知道,羊绒也不能过分地抓,抓得太干净了,到了寒冬腊月,老北风吹上,羊就给活活冻死了,羊绒就跟人身上贴身的衣裳一样,你不穿,冬天出门就冻成硬冰棒了。再比如说那山梁顶上,如果没有一点植被和柴草,没有林木作为遮掩,山梁大地都要裸露在外面,风沙吹上,几年下来,很快到处就都沙化了,一切虫虫鸟鸟就都没处躲藏,没法生活了。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咱们这里就彻底毁了!”他又说:“你们在进到场部时应该看见了,这些年我带着场里职工干部在周围不停植树造林,种的杏树和杨树漫山遍野,光我个人已经栽了有几百棵杏树了,杏树的成活率特别高。场部的外围,还住着一些老百姓,看见我们种树,就也跟着在自家的房前屋后都种上了杏树和杨树。现在他们种的树都长大了,既能遮风挡雨,阻挡沙尘,同时可口的杏子也吃上了。”焦点平台
老马说:“你说的我都懂,那就明天抓着看吧,能抓多少抓多少。价格市场多少就给我多少吧。”
老章说:“别人为非作歹没人管,也没人干涉,但是咱们啥都没干,都还有人造谣迫害呢。真要是有点失误,不把咱打下课,那才怪事呢。”
“这个你放心,一定不叫你为难!”
伊斯哈格嚷嚷着要去看他的羊:“大,我的羊妈妈在哪儿?我看看咋样了!”
老章说:“在后院呢,走,看看去!”老章领着老马和儿子到后院的一个土块垒的圈圈子里,母山羊就在圈圈子的空地上吃着一些拔来的长草,有许多是苦苦菜和芦子草,还有枯籽蔓。“这些草,都是我抽空在附近植树时顺带寻回来的,羊可爱吃了。”焦点平台
白雪看见了伊斯哈格,站定审视了一下,认出来了,“咩干干、咩干干”地叫唤着往伊斯哈格这边走来。伊斯哈格激动地钻过土圈圈去,一把抱住了母山羊,把脸贴在白雪的身上,蹭过来蹭过去,说:“你认出我了吗?认出我了吗?我是哈哈。”
晚上,他们吃了一顿场部灶上的土豆熬糊糊,还有一个花卷。老马对章永旺说:“你们牧场就这么个生活水平啊?土豆菜里连指头蛋子大的一疙瘩肉都没,你说你们养那么多牛羊干啥呢?你这个场长,在咱们村子人的眼里,觉得了不得,他们要是来一看你这样可怜,就笑死了。你说你捞不上油水子情有可原,但你吃好一点,把生活改善改善也算数,我真是服了你了。”
老章没生气,只是嘿儿嘿儿笑,说:“吃肉得自己掏钱买,工资都不高,工资每涨一点,物价就要往上涨,靠那点瘦工资能把一大家子人生活维系住,就不错了,一天吃了肉,嘴就得吊起来了。”
老马说:“我这个人,和你不一样,我这辈子就不能把自己亏下了,我每隔两天就得吃一回肉。哦,你们这里的羊靠近大山,肉应该特别香,我买上一个,明天给我煮上吃。”
“场里的牛羊不处理。”章永旺说。
老马想了一会儿说:“那干脆把你养的这只羊卖给我,我明天宰了吃了算了。”焦点平台
“你这个人,嘴咋这么馋?但是,说实在的,这只羊也着实把我拴死了,一直要跟上照看,跑得我都有了伤痨病了。”说着他用过期台历纸卷了一根旱烟,抽着,并“哐哐哐、哐哐哐”地发出咳嗽,咳嗽憋得他红头胀脑,“我一天光找草都找不及。这羊迟早得卖,不能看它老死了,反正那一刀子是躲不脱的,迟卖不如早卖,你要的话就买走吧!”
伊斯哈格立即抢过话茬说:“白雪不准卖,我要养着!”
“白雪是我儿子的,得问他同意不同意,我不好做主。”章永旺说着又咳嗽起来,“哐哐哐,哐哐哐,真的,寻草喂羊把我寻得慌慌张张的,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我要工作,还要引着大家植树,每次我个人掏钱让羊把式带几天,羊把式也不愿意,因为他们在我这里得不到啥好处。这些天我一直考虑把羊卖了算了,卖了我好腾出身子,一边工作,一边带场里职工干部多种些树!”老章看着儿子脸色特别难看,也来气了,“你不卖,你自己咋不放羊去,干脆你书不要念了,放羊去算了。”
“放就放,放羊有啥不好的,比念书松活多了!”伊斯哈格说。
“你再不要羞你家先人吧,赶紧好好把你的书念好,有些不念书的,后来长大了后悔得哭得旺旺的,狗一样。”焦点平台
“我不会出去打工吗?”
“你以为工那么好打吗?你看看你两个哥哥,不好好念书,指望我给报工人,还不是给耽搁了?如今出门打工,在工地上苦死苦活,一个月连嘴都混不住,还要向我要钱。你不趁早好好念书,将来啥出息都没,你不要指望我了,我你是指望不上的。”章永旺说的时候,好像特别伤心,但又似乎没有办法。
伊斯哈格有点语塞,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想要是母亲在,会因为疼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把白雪卖掉的。
老马趁机对伊斯哈格说:“买了,我解了馋,你也可以拿着钱买一双好球鞋,你要是穿上那种军绿色的球鞋,去学校念书,谁不稀罕,谁不羡慕。你让你大,后躺牧场的大场长,一天拉着个山羊,就跟拉扯一个娃娃似的,多丢人现眼,你难道不懂得心疼大人吗?”
伊斯哈格看看父亲瘦小的身子,还有那张瘦削的面孔,再看看他的那些旧洼洼的衣衫,心里突然特别疼自己的父亲。他就再没有说什么。
老马说:“就这么定了。”他怕老章和伊斯哈格反悔,就要和老章在袖筒里揣手说价。老章有些不好意思,就说:“羊你也见了,你看着给吧。”
老马就说了一个价,老章没有讨价还价,老马把钱直接戳进了伊斯哈格的衣服口袋,说:“你的羊,钱给你,你拿上买鞋子,多出的你下学期缴学费去。”焦点平台
晚上,老马和伊斯哈格睡在里面一间房子的土炕上,炕上只有一张席子,他们和衣而眠,倒也不冷,凑合了一晚上。一夜无话。
第二天,章永旺叫来两个羊把式,一个是老赛,一个是八十子,请他们把山羊从附近的草山上赶回场部的羊圈里,再一起来帮忙抓羊绒。老赛以前在农业社的时候是个赶马车的车把式,这个人一辈子连夜里做睡梦都想着找婆姨的事情,然而到老都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女人。他跟章永旺的年岁差不多大。老赛每每遇上一个人,不管是熟悉不熟悉,见面张口就请人家张罗着找女人。大家站在场部的羊圈里,围着一群山羊,老赛看见老马说:“马师傅,你走南闯北,经见得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能给我在哪达寻上个贤惠媳妇吗?”
老马呵呵大笑,说:“你都这么一大把年龄了,咋还是个老光棍汉。你还要个贤惠媳妇呢,就你这么个条件,能有个母的陪着就已经把天叫言喘了!”
老赛一下子脸红得跟个茄子似的,都快变紫了,说:“你咋这么个人?简直胡说着呢,我还不老,咋就不能寻个媳妇呢?”
听到这,老马双手拍着膝盖大笑了一场。把个伊斯哈格也笑得嘴都合不拢。老赛难为情的,站起了,又蹲倒了,不知如何是好,“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不要看我老汉的笑摊,你们要是换成我,腰都拉不来了,还说寻媳妇呢!”惹得在场的人又是美美一阵笑。把伊斯哈格都笑得挣出一个屁来了。这一下,大家又是一阵欢笑。章永旺脸上有些难堪,对儿子说:“你没带寒假作业来吗?去,我抽屉里面有纸,去写你的作文去。大人说的话,娃娃不要听。”焦点平台
伊斯哈格不情愿地走出羊圈,在羊圈门口旋了几圈,不知啥时候又踅摸着钻进羊圈来了。
老马说:“好呀,只要你今天好好给咱抓羊绒,我给你寻一个攒劲媳妇!”说着,老马给章永旺挤了个眼。老章无奈地笑笑。老赛兴奋异常,高兴地说:“今儿你看我的,看我给你咋薅羊绒,你们也学着点。”说得老马心花怒放。但是老赛有些不踏实,又说:“马师傅,我寻媳妇的事,就全托靠你了。”
老赛和八十子几个羊把式把羊圈羊粪扫开,扫出一片干净空地,就开始逮羊了。老赛虽然年岁有点大,但力气不小,手一伸就把一只强壮的山羊给拽住了。那只羊咩咩叫着,蹬着腿子,但无济于事,很快就被绳子捆住了腿子和蹄子。老赛一个人就可以轻松把一只山羊搞定。八十子从墙缝子拿出几个抓羊绒的爪子。老赛说:“这个场子里的职工干部,几乎每个人都藏着这么一两个羊绒爪子,只要机会一来,随时就能薅羊毛,抓羊绒。”他拿起一个爪子伸进刚刚绑定的那只山羊的皮毛中,来回抓了几下。拿出来看看说:“绒特别好!”焦点平台
章永旺说:“不要把绒抓得太净了,羊和人一样,也需要衣裳过冬呢。就像那个山梁,植被彻底破坏了,风沙洪水泛滥,大自然就要报复人类了。所以,你们抓绒的时候轻一点。你们看,这抓羊绒的爪子多吓人,尖尖的,利利的,抓在羊身上,羊就疼得全身都抖动起来了。”
伊斯哈格看见那些被薅羊绒的山羊,收紧了身子,瑟缩发抖,发出叫娘一般的声音,“妈啊——妈啊”地叫唤着。山羊们不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伊斯哈格吓得脸色都变了。
大家把抓下来的羊绒陆续放进备好的蛇皮袋子里。
章永旺听见羊的叫声,心里特别难受,说:“你们先抓,我喝口水去!”就出了羊圈去场部了。
羊的叫声吓得伊斯哈格躲在羊圈门口,趴在门框上往里面心惊肉跳地张望着。
老赛拿着羊绒爪子,在那只白山羊的身上有顺序地猛烈地抓了起来。
老马乐呵呵地笑着说:“我努力给你访查,一定给你寻个好女人。”
老赛立即接上说:“他爸,记着,女人一定要贤惠善良!”
老马笑笑说:“怎么,还要个贤惠的?一定,一定。”
老赛说:“不过,差不多就行了,太好了,人家也嫌弹咱呢!”老赛的话音刚落,不知是因为什么心理,手劲儿突然使得大了,只听见那只山羊发出没命的叫唤。老赛没管,好像羊的叫声越大,越能显示出他在卖力地薅羊绒。焦点平台
伊斯哈格听着羊的惨叫声,他脑袋贴在羊圈门上,心突突跳着,不时够着看那些受刑的羊。正是这些羊,养育了这个场子里所有职工干部,因为这个场子只有一半工资是财政拨款,另一半就靠场子里这些牛羊的收入。此刻,那些山羊的腿子被两两相交绑在一起,半卧半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嚎叫和哭泣。羊不断地叫唤,叫得声音越大,越是证明它受到了巨大的创伤,疼得受不了了。有时候,老赛不小心会把那非常尖锐的钩绒的钢爪子不慎塞到羊肉里面去,猛钩几下,羊就会发出死声拉气的叫唤。爪子把皮肉钩烂了,血也流出来了,很快羊毛都被染成了一片红色,白山羊顿时变作了红山羊。那些山羊每叫唤一声,伊斯哈格的头皮子就一阵发麻发紧,浑身像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都要抽筋了。
章永旺走回羊圈,听到羊的哭泣,对老赛说:“你跟个羊有啥过不去的,抓羊绒不是那么个抓法,你看那个羊哭得哇啊哇的,听得人头皮子发麻,心里瘆得慌!”
老赛说:“场长,不这样薅羊绒,羊绒就出不来,你以为羊绒自己会跑出来吗?得下狠手薅,才能薅出羊绒来!”
章永旺说:“你这样薅羊绒,会把羊薅死的,再说你薅得太干净了,它们冬天还怎么活呀?”
老马笑着说:“章场长,你让他薅吧,卖上钱了,工人的工资不就有了吗?要以人为本嘛!”焦点平台
章永旺:“你这个人心瞎了,那羊不疼啊?老赛,你慢点薅,慢点薅行吗?”
老赛点点头。
老马突然想起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办呢,一圈羊得薅到晚上才能薅完,今晚无论如何得吃一顿肉,所以他对章永旺说:“我还有个事情呢,现在得去办一下。”章永旺明白老马说的意思,就向他努努嘴,意思不要叫儿子听见了。老马诡诈地笑一笑,装着出去解手去了。
日头走到山畔的时候,照在那些杏树上,红色的,绿色的,就像是一幅凄惨暗淡的水墨画。羊绒终于抓完了,满圈的山羊浑身都被抓得烂洼不糟的,白山羊统统都变成了红山羊。
老马过了很久才回到羊圈,进了羊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偷偷地看看吓得脸色煞白的伊斯哈格,心里突然有些同情他,就抚摸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表示歉意。
他出去那会儿,在场部周边掏钱雇了一个宰羊的人,把那只叫白雪的母山羊,那只曾哺养伊斯哈格长大,对章家有恩情的母山羊宰了,又让那人帮忙收拾了,找了一口锅,在圈白雪的那个土圈圈子煮起羊肉来了。
羊绒一袋子一袋子过了秤,钱款由会计入账,和前次来的那些羊绒贩子是一个价,每斤五十元,这个价是现在的行情。
晚上,大家从羊圈忙完,回到场部,伊斯哈格突然想起他的羊妈妈,就去宿舍后面的土圈圈子看。寻找了半天,羊妈妈白雪早已不知去向。他焦急地转来转去,突然他在后院,借着月光看见一张拔得展展的贴在墙上的山羊皮,那张羊皮已经被血染得红透了。伊斯哈格猛地扑到羊皮上,放声痛哭,那一声声的哭泣,传到章永旺的耳朵里,每哭一声,章永旺的心就颤动一下,脸上的肉就弹跳一下,他的眼泪也不由得落下来。他想起给儿子寻奶的事情,他第一次看见这只搭救过他儿子性命的母山羊的样子,毛那么白,那么俊美,那一幕幕往日的镜头从他眼前掠过。他躲进套房子,尽力克制着,但是各种人生的遭际一起涌上心头:儿时给人放牧扛活儿;成人参加工作后,妻子是自己用半口袋豌豆换来的,但跟了他一辈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穷愁潦倒的他,当了半辈子场长却窝窝囊囊的,至今啥也没给儿女置办下,一直被别人瞧不起。种种屈辱和伤心的事一股脑儿涌上心头,激荡和拍打着他的灵魂和精神,使得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竟然老泪纵横,趴在套房的炕上抽咽起来,看上去比儿子伊斯哈格还哭得绝望和伤心。焦点平台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是,会计和保管晚上竟叫来把他们的话奉作圣旨的另几个羊把式偷偷溜进羊圈,就着昏暗的路灯,把白天已经薅过羊绒的那些山羊又偷偷用绒爪子薅了一遍。焦点平台
老马请几位辛苦了的羊把式吃羊肉时,给章永旺和伊斯哈格各端去半碗。
章永旺擦了眼泪,强撑着端出去还给了老马,老马不解地看一眼,摇摇头,苦笑了一下,说:“羊也有它的命,它造化到世上就是要被吃的,吃了,他的灵魂才能回到一个好的地方去,这就是每个生命的宿命。”
章永旺什么也没有说。
伊斯哈格看到羊肉,哭得一抽一抽的,气都上不来了。他骂老马:“你这个骗子,你还我的羊妈妈,还我的羊妈妈!”他后悔上了老马的当,让他的羊妈妈惨遭毒害。
那天晚上,伊斯哈格怎么也睡不着,最后泪流干了,也哭累了,才昏昏沉沉睡着。睡着后就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漫山遍野是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在草木葱茏的山上,有一群欢蹦乱跳的红山羊,其中就有他的那只羊妈妈,它全身雪白雪白的皮毛已经完全变成了红色,它昂着头,在深情地注视着他。
过了几年,因为移民大搬迁,红山羊村有许多人要搬走了,后躺牧场退耕还林还草,场子也关了,职工干部被县畜牧局重新分流安插到县里的草原站、畜牧站等部门。这时,章永旺已经病故。他被埋在后躺牧场的山上,守护着他生前种的那些花草树木,同时也被山林包围着。送他的那天,正是春天,天气晴朗,杏花和各种野花开得十分红火,这些花儿仿佛是在迎接他回归大地,同时也像是在为他戴上了孝。他的墓穴前立有一块墓碑,上面有他成才的儿子伊斯哈格书写的两行魏碑大字:“白云挽碧树,翠岭锁金谷!”焦点平台
夜里,伊斯哈格遥望着远方满天的星空和一轮明月,他隐隐约约仿佛看见在那洁净的明月里,有一位老人坐在树下,旁边是曾哺育过他的那头母山羊白雪。
了一容,本名张根粹,东乡族,出生于宁夏西海固,一级作家。小说曾获中国第三届春天文学奖、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十年《飞天》文学奖、十五省市自治区优秀图书奖等奖项。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选刊转载。出版小说集《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玉狮子》等,部分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焦点娱乐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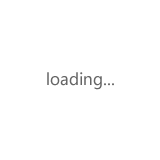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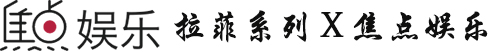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