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平台快讯:
一
五爷用一把靠背小木椅挨墙坐在门前,双眼似闭似睁,仿佛一尊雕塑。虽然路口挂着一块“内有地磅”牌子,但进来过磅的车辆并没有五爷想象的多。一天一天坐在门前,五爷常常一守一个空。五爷也一点都不急。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样子,常常让看见他的人怀疑,他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五爷当然活着。
间或,他的右手就会伸向旁边一块石板,探寻着,摸索着,端过搪瓷茶杯来喝上一口茶。待他再探寻着摸索着将茶杯放回石板上后,就又还原成了雕塑状,一动不动,双眼似闭似睁。
这个时候,五爷其实是在他的脑海里放电影。只有他一个人看的电影。他和张小芊的那些过往,连贯,或者不连贯地相继在他的脑海里闪闪烁烁,摇摇曳曳。
靠近他,俯下身去细看一阵,就能看到五爷脸上会一忽儿喜悦,一忽儿悲伤,一忽儿茫然,一忽儿阴云密布,一忽儿阳光灿烂。
门前那条小河已经不见踪影。小河,连同两边一块一块的稻田,都已经被人们在上面建的建了房、修的修了路。五爷的房子旁边,是一条柏油路。柏油路往外不远有一岔路,一边通往西凉山片区的乡村,一边通往一个高速路口。高速路往上,通往云南的昆明方向;往下,通往四川的成都方向。柏油路上跑着的大车不少,就是那些跑来跑去的大车,特别是那些挂车,让五爷在他这门前装了一个地磅。地磅装在从他房前通往安置区里面的路上。地磅,也就成了路的一个部分。焦点平台
小河虽然已经不在,但五爷跟随着张小芊的身影,就还能从河的这头,理到河的那头。有时,他从地磅这儿理起,理到远处,再远处。有时,他又不知是从哪儿理起的,理着理着,就理到了地磅这儿。那条小河,他太熟悉了。它在哪儿转了个弯,拐了个拐,哪一段河埂宽些,哪一段河埂窄些,五爷都熟稔于心,仿佛他昨天还在上面游走。那些白天,五爷和汪四一起,在里面捞起过多少鱼啊。那些有月亮的夜晚,他和张小芊手牵着手,在那河埂上走过了多少个来回啊。
汪四家媳妇拖着一个功放和喇叭连为一体的音响哗哩哗啦来到地磅上的时候,五爷还不知道她们是要在上面跳舞。她身后跟着五爷一个都不认识的三个女人。汪四媳妇将音响放下后,在地磅上绕了一圈,边绕边放重脚步,跺出砰砰砰的响声,说真安逸,咋就没早点想到这儿,还一直跑那么远。你们试试,踩上去还有弹性;你们听听,跟没跟上节奏,自己就能听出来。发现地磅上有石块,汪四媳妇踢了一脚,又喊噼噼啪啪跺着脚的三个女人说,看看,看看,上面那儿还有石块,找了弄出去,别一会儿崴了脚。
汪四媳妇转到五爷这边,说五爷,我们在这地磅上跳跳舞玩,你没意见嘛?焦点平台
五爷愣了一下。他的脑海里,还在放映着他和张小芊的电影。他没想到她们要在地磅上跳舞。他装这地磅,是用来讨生活的,不是用来给她们跳舞的。
但五爷能有啥意见呢?即使有,他也不敢说。她是汪四媳妇呢。
汪四不但是他儿时的伙伴,还是他们的村主任。
想起汪四,五爷就想起了他和汪四逃学来河里笼鱼的日子,想起汪四腿上被他爹用竹条子抽出来的血印。那些血印仿佛吸足血的蚂蟥,横一条竖一条爬在汪四腿肚上。那时,他不知道汪四为啥不会被抽怕,为啥被抽过没几天,就又来约自己拿鱼笼去网鱼。对汪四,五爷心存感激。回来修房,是汪四帮五爷去信用社贷的款;就是这地磅,也是在汪四的默许下,他才得以装上。
五爷说,你们跳,你们跳。你们在这儿跳着,我还可以有免费的舞看呢。要是跳热了,要脱衣服了,放这边来我帮你们看着。
几个女人同时停下来望向五爷。
汪四媳妇哟嗬一声,说,看不出来嘛,你是老不正经呢,还是不想在这儿混了?要不要我们几个给你来段脱衣舞?
汪四媳妇又指指一个女的说,她可是你侄儿媳妇呢。
五爷由一脸无奈,变成一脸难堪,说,玩笑,玩笑。
汪四媳妇说,好啊,还能开玩笑,就证明你还没到老不死的地步。
月亮依旧停在旷野上
你的身影被越拉越长焦点平台
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
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
格叽格叽的背景音乐,在五爷听来完全像是一把长锯在锯木料,呼哧一声被拉过来,呼哧一声被扯过去。汪四媳妇带着几个女人在地磅上踩踏出来的噼噼啪啪声,让五爷心烦。仿佛那一只又一只脚,踩踏在他心上。没多时,脚步就不只是踩得他烦,而是踩得他的心一阵一阵地疼、一阵一阵地慌。仿佛他们踩去的每一脚,都会在他的地磅上踩出一个坑。
似乎,那地磅就要在她们的踩踏中訇然塌下。
五爷端起搪瓷杯,起身进了屋。
砰一声脆响,门在五爷身后重重地关上。
坐在沙发上听着外面的音乐声和脚步声,五爷的心还是一阵一阵地疼、一阵一阵地慌。索性,五爷脚也不洗,站起身来走进屋角的卧室,和衣钻进被窝。五爷用被子紧紧地将自己裹了,试图将音乐声和脚步声阻挡在耳外。但他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他越是努力阻挡,音乐声和脚步声就越像是经过反射,然后又聚焦,然后全都不偏不倚、不丢不落地钻进了他的耳里。
五爷试图让自己去想常二嫂,不,是想张小芊,想以此抵御这让他心疼心慌的音乐声和脚步声。但一点用都没有,倒是这音乐声和脚步声,让他与张小芊的过往变得支离破碎起来,甚至连张小芊的影子也变得模糊不清。
音乐声停了。
接着,踩踏声也相继远去,然后消失。终于熬过来了。五爷一直紧绷着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刚才,五爷以为他就快疯了。焦点平台
五爷后悔装地磅了。接下来,一个又一个晚上,天刚擦黑,汪四媳妇就领着那几个女人来到地磅上,在那儿扭腰,在那儿展臂,在那儿踢腿,在那儿蹬脚。一跳,就是两三个小时。在她们踩出一阵一阵挥之不去的噼啪声中,五爷觉得自己装这地磅,完全就是自讨苦吃。白天因为零零散散的过磅车辆,晚上则因为这女人们的跳舞,让他再也不能安安静静地想一想张小芊。
后悔一天胜似一天。没几天,他就已经不只是后悔,他整个脑袋瓜,都恨不得要爆炸了;整个人,都恨不得要疯了。
再咋样,这毕竟是我的呢。五爷想。
这样一想,在汪四媳妇又一次领着女人们走来的时候,五爷便厚着脸皮壮起胆说,你们别处去跳了,不能在这儿跳了。汪四媳妇一脸惊讶,带着一脸不高兴问五爷别处在哪儿?要五爷说出除了这儿,周围团转还有哪可以跳?
这周围团转,五爷确实不知道还有哪可以跳。里面一点,有是还有一段路,但因为一户吴姓人家开着一个洗车场,洗车水流淌出来,弄得一路稀泥烂窖,别说跳舞,就是从上面过路,也得拣边儿走。再往里,也还有几条街道一样的路面,但那些路面都还没硬化,不是这儿那儿到处是坑是洼,就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堆人们修房子用剩的石料。焦点平台
周围团转没有,就不能跑远点?清官亭公园恁大,还不够你们跳?你们以前不就是去那儿跳的吗?
想是这样想,五爷却没这样说。
五爷说那是你们的事,我不管,反正不能在这地磅上跳了。
不能?你说不能就不能了?我就在上面跳了,要咋?说着,汪四媳妇扭起腰身,挑战似的边望着五爷,边喊旁边的人说,跳起,他三婶,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来咬我屁股两口。
五爷丧着脸回到屋里,坐到沙发上提过水烟筒猛吸起来。水烟筒里的水被他吸得轰隆轰隆响,那烟被他吸得像是有一股风在簌簌地吹。
五爷找来洋铲和簸箕,将堆在墙脚的一些乱石和碎砖,铲了,抬去撒在地磅上。天快黑的时候,他一边在屋里做饭,一边听着外面的动静。蹲在火上的锅烧红了,他还没舀油进去。慌忙火急把油舀进去后,又弄得那油被烧得冒烟,他还没往里倒要炒的菜。他双眼看着火上的锅,可心思,全被外面的一响一动给牵住了。是她们来了吗?音响怎么还不响?门外响起一阵呼呼呼的声音,接着是砰砰砰的声音,然后又是唰唰唰的声音。五爷端起洗菜的水准备倒门外去。刚到门边,他又缩回了身来。他看到她们正在扫地磅。
五爷突然地怕见到她们了。
五爷刚缩回屋里坐下,一个女人歪在门边探进头来喊,五爷,把你的路灯开一下嘛。女人又问,今天是不是有拉石头的车来过磅,撒落这么多石头在上面?女人说,开灯来照着我们清理一下。五爷哦哦着,没有说出一句顺溜话,急急起身,啪地摁亮路灯。焦点平台
喊开灯的女人离开后,五爷呼地将火上的锅扯下来砸在地上,然后一仰身歪靠在了沙发上。眼睛闭着,五爷却没睡。地磅被踩踏出来的噼啪声,一阵一阵地让五爷恨不得冲出门去胡乱咒骂上一顿。
五爷终究没有起身冲出去。他克制着自己,坐在沙发上,拿沙发垫子一会儿抓上一把,一会儿又抓上一把。直到门外的音响停了,他也没离开沙发站起过身来。一阵散乱的脚步声响着消失后,五爷才腾地站起,呼地端起先没倒出去的洗菜水,冲出门哗地往地磅上泼了过去。那水泼水去的地方,仿佛正一溜儿地站着汪四媳妇和另外那几个女人。
装水的盆哐啷一声掉落在地,五爷有气无力拖拉着脚步往地磅走去。迈上地磅的时候,他是那么小心,那么谨慎,仿佛担心踩踏出一点点声响来影响到别人,仿佛担心自己会踩痛那地磅。
在湿漉漉的地磅上站了一阵,五爷突然弹起身来,跳着跃着,砰砰砰把地磅跺得震天响。五爷成了一个顽童,地磅,成了一张蹦床。
像是跺累了,五爷一摊软泥似的往地磅上蹲了下去。这一蹲,他的某个部位仿佛碰触到了电流,让他接着又呼的一下弹跳起来。随着他的一个弯腰一个甩手,一块石块向他屋檐下的那个灯泡飞了出去,哐的一声后,那灯泡发出一声炸响,昏暗的夜色便像一袭幕布呼啦一下盖住了地磅,也裹住了五爷。焦点平台
二
入冬了,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只水烟筒,一个搪瓷茶杯,一把小木靠椅,伴着五爷过着在门前守候地磅的生活。来过磅的车辆依旧不多,但还是一天三辆五辆地有了。那些车辆,有拉钢筋的,有拉机制砂和公分石的,还有拉煤的。过磅的收入,差不多够五爷的生活开支了。五爷的房子除了一楼他自己住,其余都租了出去。一个月两千多块的房租,他凑两个月,就跑信用社去还一次贷款。
五爷享受着这样的阳光,也享受着这样的悠闲,更享受在这样的日子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他和张小芊的过往。只是汪四媳妇领着那几个女人来地磅上跳舞,依然让他烦躁。她们跳舞的人,已增加到九个。尽管她们踩踏出的声音不再像最初那样让他心疼让他心慌,但听着那音乐声和脚步声,他的心还是感到烦。只要那音乐声和脚步声一响起来,五爷脑海里那张小芊的身影,就会被震得支离破碎摇摇曳曳起来。所以只要看到汪四媳妇拖着音响引着那几个女人走来,五爷就会从小木椅上起身进到屋里。屋里,他已经燃起了煤炭火。煤炭不用他买,装着煤炭来过磅的车,刹车和起步的时候都会弄落一些煤炭下来。他先是用一只胶桶拾了装起来烧。慢慢地,他那煤炉就烧不完拾起来的落煤。他把它们拾了,一桶一桶地倒在屋外一堵墙下堆了起来。就是这免费的煤,让五爷取消了拆除地磅的念头。坐到火炉边,烤着火吸着水烟筒喝着茶,在一阵一阵的烟雾和热气中,五爷慢慢又能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回想他与张小芊的过往了。焦点平台
五爷已经知道张小芊家的房子就在安置区靠里的那个拐角上,从他这儿去虽然要转过一道拐,但总路程也就那么千把米远。五爷还知道,张小芊家的房子虽然在这儿,但张小芊并没有住在这儿。她和她的女儿住在一个叫钻石苑的小区里。这是郭老三来和五爷聊天时说起的。有事没事的,郭老三就会端着一个茶杯来到五爷的门前,边晒太阳边和五爷聊天。郭老三说,她啊,常二还没出事的时候,就帮她姑娘家带孩子去了,住在她姑娘家。张小芊的姑娘家住在钻石苑,也是郭老三说的,他说常二嫂有一次回家来,他遇上了,就问她姑娘家住哪儿,她说的,还说钻石苑,就是地区医院的家属区。从某一天起,郭老三连晚上也开始来到五爷的屋里和五爷聊天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郭老三喝着五爷给他续上的茶水,抽着五爷递给他的纸烟,在五爷像给他们续水一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询问中,就将五爷走后村里三十多年来的这样那样事儿,以及这家的长那家的短,对着五爷,对着五爷这显得空空荡荡的屋子,摆了说了。焦点平台
郭老三说,最不值的,就是常二这狗日的了,算足算尽,最终把自己的命也算没了。那年给我拉一车肥料,差他五十块钱,我说先欠着,他硬不干,硬是逼着我去借来给掉。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就这狗日的做得出来。
五爷不想听郭老三说这些。人都不在了,还说这些干啥呢。五爷给郭老三递过烟去,说抽烟、抽烟。
五爷虽然问过钻石苑的具体位置,但他从没想过要去那儿找张小芊。
她毕竟是常二嫂,而不是曾经的张小芊了。
外面的音乐声和脚步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五爷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一阵汽车的喇叭声,将五爷从那些不知想了多少遍的过往中扯了回来。
过磅车开走了。五爷进屋坐回到煤炉旁的沙发上。有人在外面敲门,五爷以为又是郭老三来了。现在,他已经有些讨厌郭老三。他觉得有如听郭老三说那些东家长西家短的事,还不如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五爷想装作没听见敲门,关灯睡了,但心里又觉得过意不去。五爷转身走向门边,将手伸向了门锁。门打开一半,五爷便像被谁施了定身术,嘴半张着,一只手固定在门方上,一只手向下垂落着,愣愣地站在那儿动弹不得。焦点平台
她的长发已经不在,剪短了,还烫成了一头卷发;三十多年时光,在她脸上留下了一道一道皱纹,那张瓜子脸的双颊已开始下垂。
他看着她,仿佛就是昨天,或是刚才,他还见着她一样。
是常二嫂先动了起来。她往身后看了一下,转回身来望着五爷说,咋啦,认不出来了?就这样堵着门,不欢迎我进屋坐坐?
五爷的手依然扶在门沿上,他扭动上身,缓缓转向里屋看去。一时,五爷感觉屋里的光线是那么暗,整个屋里,完全是一幅灰扑扑昏沉沉的色调;五爷又觉得那光线照在屋里,让屋里的那些物什都那么清晰,那么显眼地摆在这儿那儿。沙发上皱皱巴巴的垫子,火炉上被炒菜时溅出的油、煨水时溢出的水裹搅了混合了敷在上面看去油腻腻的炉面,朝天的锅朝地的瓢,还有或摆于桌上或丢于盆里的碗筷,或卧于沙发前的鞋子或躺于沙发扶手上的袜子,屋里的这样那样,所有的所有,让五爷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五爷转回身来,不敢看常二嫂。他弯了一下腰,低着头,缓缓将门彻彻底底打开,然后站在门边,一副要躲到门背后,任由常二嫂走进去的样子。常二嫂双手反剪身后,也不看五爷,像是专门来检查五爷这屋里似的,径直走了进去。只是她也没细看那屋,只随意往屋里瞟了几眼,就走到火炉旁坐到了沙发上。焦点平台
常二嫂将一个装了什么的黑色食品袋放在身旁,双手举在火炉上空手心手背一上一下地翻了两次,说,有笼炭火燃着真安逸,烤着浑身都热乎,不像电烤火炉,前面烤了热得不行,背后还发冷。五爷已经走过来,站在离火炉一米来远的地方。他一句话说不出来,还像是连地方都找不到坐似的。常二嫂说,坐啊,这是在你家,还要我叫你坐你才坐?五爷将火炉旁的一个胶凳轻轻挪了挪,然后轻轻坐了上去。
五爷的头依然低着,双手十指交叉着夹在双膝间,时而往上抽一下,时而往下塞一下。常二嫂举在火炉上空的双手仿佛经不了火炉的烤,一下将这只翻上来,一下将那只翻上来。她的目光,也不再看向五爷,而是看向五爷那房子的一堵墙。看了很久,她也没有移动一下。
有风,在窗外吹得呜呜呜的。公路上,响着车辆驶过的唰唰声。是谁从地磅上走过,搓出了嚓嚓嚓的脚步声。
常二嫂用一只手捏了捏另一只手,看向火炉中间最小的火炉盖,说,在上面又是丢石块又是倒水,你这何必呢?你这不是得罪人吗?
五爷一时没反应过来常二嫂说的是啥,等他反应过来,便很惊讶,又很羞愧,他将双手从双膝间抽出来,一只放在膝盖上,一只放在炉面上,看向常二嫂问,谁跟你说的?焦点平台
常二嫂哼了一声,说的人多了。
五爷变得很委屈的样子,再次将双手十指交叉着插进双膝间,说那是我的地磅,我就是不想让她们在上面跳。在我的地磅上跳,她们还有理了?
跳跳咋了?还能把它踩破踏通?
这责备的语气,让五爷感到既亲切又遥远。
五爷愣了愣,说要是踩破踏通了呢?咋办?
咋办?凉拌!怕踩破踏通,你就拆了,这地儿——
五爷突然鼓眼看向常二嫂。
被他这一看,常二嫂没接着说那地儿是大家的路,不是他五爷的,转而说:
破了通了,我给你补起。
你又没跟着去跳,关你啥事?
我还正打算去跟着跳呢。她们都叫过我好多次了。三三家孩子送幼儿园了,我正闲下来没事。这不,为跟她们一起跳舞,我都搬到这儿来住了。
五爷慌乱而又惊喜地望着二嫂,真的?
我有必要骗你?明晚上我就参加了,这不,你看,鞋子都已经准备好了,是三三刚才送来的,她专门买来给我穿着跳舞的呢。
常二嫂拿过沙发上的袋子,边解袋子的结边接着说,我就是出来拿这鞋,望着你的灯还亮着,才顺便来看看你的。
解开的袋子里装了一双红色布鞋,还有那么一点点高跟。常二嫂说,这娃娃也是,买这红色的,还高跟,刚才我怪她,她又说跳舞穿这种才好。
五爷定定地看着那鞋子。他不知道,张小芊穿着它们,在地磅上会踩踏出怎样的一种声音来。焦点平台
三
一辆运载钢筋的卡车倒了出去。望着它远去的背影,五爷转回身子看向地磅。还好,没再掉啥在地磅上。也是,难道还能掉下一圈钢筋来?五爷是打扫怕了。先前来过磅的车,有一辆载的是机制砂,装得满满当当的,停车和起步的时候,机制砂簌簌簌地淌下一些来,落得地磅上这儿一摊、那儿一摊。车子一开走,五爷就拾起那把竹扫帚来哗啦哗啦地扫。对那些扫不动的,他还拿洋铲去铲,铲了,又扫。弄了好半天。要是再来上一辆那样的车,五爷怕一时打扫不出来。
天就要黑了。望着依然干净的地磅刚要转身进屋,一辆卡车打着转弯灯开了进来。你狗日些是约好不让老子做饭吃啊?看出是辆装载煤炭的车,五爷更是像看见了黑煞神,一时慌乱不已。这装载煤炭的车,一个个车主都把车厢装得鼓鼓胀胀的,轻轻一个刹车,轻轻一个起步,炭块煤灰就啪啪掉落。以前,五爷最希望装载煤炭的车来过磅,一辆车来过后,他总能扫上一桶半桶的煤。那从车上掉落下来的煤,他已经拾了在墙脚堆起不小的一堆。可是现在,他又最怕这样的车来了。那煤掉落下来不但要扫,要将地磅弄干净,就还得用水去洗。那是黑漆漆的炭呢。二嫂那红红的布鞋在布满炭灰炭泥的地磅上踩踏一阵后会是什么样子?五爷想想都不忍心。五爷想告诉驾驶员地磅坏了,但“促”一声刹车声响,驾驶员已将车稳稳停在地磅上,车上的炭,已窸窸窣窣掉落了一些下来。焦点平台
来不及再将掉落在地的炭撮进桶里,五爷用洋铲三下五除二地铲进旁边的侧沟,接着又是用扫帚扫,又是提水来冲。
五爷准备做饭吃,又突然想起那颗被他砸了却一直没有换上的灯泡。
五爷终于换灯泡啦?站在炽白如注的灯光里想象着二嫂在这光线里舞蹈该是一种啥样情景的五爷,被郭老三媳妇的话吓了一跳。
换了。换了。五爷说。
五爷脸上浮出一片愧色。
这灯泡多大的,咋这亮?
大点好嘛。大点,你们就看得见跳了,就不会踩着石头崴着脚了。
汪四媳妇拖着旅行箱一样在脚下安装有轮子的音响来了。在她的周围,跟着一群女人。以往,这些女人大多是三三两两零零散散地来,今天,却是一起来了。五爷才那么睃一眼,就睃到了二嫂。她真来了呢。她竟然还穿了一条短裙。短裙黄块白条,条块相间。看着这短裙,二嫂,不,张小芊,曾经在南天门歌舞厅里舞蹈的身影,就又瞬间浮现在了五爷的眼前。
我说嘛,二嫂早就该来了。看看,看看,这灯亮的。二嫂一直不来,害得我们摸黑跳了那么长时间。五爷正想往下看看二嫂脚上是不是穿了那双红色的鞋,汪四媳妇这么一说,也就不好再去看,倒是举着手,抓起了头上已然不多的头发,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个女的转过身去,说就是,都怪二嫂没来,前次我的脚被崴伤,二嫂得负责,买云南白药花的钱,二嫂得赔我。焦点平台
放你的猪屁。二嫂指指那女人说,别说才被崴伤,崴断了才好,关我屁事。
咋不关你事?要不是你来了,这儿会不是铺满石块,就是汪满水,还黑灯瞎火的?没汪有那水,我会踩滑崴着?
焦点:www.sdptzc.com
就是。就是。看看,这上面干净得,哈哈,恐怕在上面打滚,也脏不了衣服了。这哪像地磅,就像张床嘛。一个女人说。
你今晚上就在这儿睡嘛,如果怕,叫五爷陪陪你,冷了,他还可以给你焐焐脚。二嫂也不甘示弱,笑着向那女人说去。
还说,我们谁能享受这个,这明明就是五爷为你准备的嘛。
汪四媳妇将音响往地磅一角放了,未开音响先走向地磅,像有蚂蚁在上面爬行她怕踩到一般,欲前未前地说,五爷,你这个真是打整来给我们跳舞的?
五爷搓着双手说,这是我自己的地磅呢,我把它打扫干净点不行?
汪四媳妇说,这就好,你要是故意打整来给我们跳舞的,我还觉得过意不去呢。不过,看在上面这么干净和灯这么亮的份上,下来我给你弄点生意。
汪四媳妇开了音响,放的不是广场舞歌曲,倒像什么大型活动欢迎领导入场时的背景音乐。真是,接下来,汪四媳妇竟然特意弄了一个欢迎二嫂加入这舞团的仪式。说二嫂就是面子大,刘备请诸葛亮,也才三顾茅屋,要她来跳舞,可是见一次说一次,不下十次了。汪四媳妇说不管说了多少次,现在二嫂终于来了,还一来就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干净的地方,还有这么亮的灯。大家一呢,要热烈欢迎二嫂,二呢,要好好感谢二嫂。焦点平台
汪四媳妇还要把领舞的位置让给二嫂。
我哪行?我是才来学的呢。
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跳舞我们哪个有你跳得早?以前听村里的人说,你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经常跑南天门呢。我们这帮土包子,哪个去过南天门?你不领,哪个领?你来了,我们这帮人未来的飞舞人生,可就得靠你了。
五爷饭也没去做了吃。一个女人问他吃饭了没有时,他说吃了。他将茶杯端出来,带了水烟筒,坐在靠背椅上看她们在那儿推让。
推辞不下,二嫂还是答应了,只是说现在她还啥都不会,要汪四媳妇继续带一段时间,等她熟悉了,再由她来带。二嫂说,你们先跳,我在这儿看,先学学。
二嫂来到五爷身边,说借个凳子坐嘛,一个人坐着好意思?
五爷进屋去搬凳子,二嫂也不等他搬出来,坐了五爷先坐的小木椅。等五爷一团一拐搬着一把竹椅出来,她也没有换的意思,只稳稳坐在那儿,看着汪四媳妇站在一群女人前面,领着她们甩胳膊扭臀。五爷也没叫她让,将竹椅置于门的另一边,然后挪过水烟筒和搪瓷杯,坐了下来。他望了二嫂一眼,想说啥,见二嫂目不斜视看着前面跳舞的人,也就没说了。焦点平台
汪四媳妇双手一下曲着举到胸前,一下伸直了甩到裤缝处,随着双脚一踮一弹,身子这边移过来一下,那边抖过去一下,胸前那对下垂的乳房,也跟着这边颠过来,那边簸过去。汪四媳妇踮着弹着,说,二嫂,听说你和五爷以前好过,你们这是要破镜重圆的样子啊。
二嫂弯了一下腰,伸手往地上像是抓了一把什么,然后甩向汪四媳妇说,瞎说,你才要和他破镜重圆呢。
汪四媳妇说,老娘年轻的时候,他是哪个王二麻子都认不得,我跟他圆哪门子的破镜?倒是你,你敢当着我们这帮婆娘的面,说你没有和五爷好过?
二嫂气急败坏的样子,站起身来扑向汪四媳妇,一手推着汪四媳妇身子,一手伸向汪四媳妇脸,说,再说,再说我撕烂你这乌鸦嘴。汪四媳妇不再跳了,偏着身子,边躲着二嫂伸来抓她的手,边咯咯咯笑着往后退。退上一阵,她从二嫂身下探出头,咯咯咯笑着往五爷这边喊,五爷,五爷,你还不管管?
五爷把脸埋在水烟筒里扑通扑通吸着,仿佛没有听见汪四媳妇喊,也没有看见还在不依不饶往汪四媳妇身上扑的二嫂。焦点平台
汪四媳妇用双手举在头顶护着喊那几个女人,死婆娘些还不来救救老娘,要看着老娘被抓死啊?
一帮女人有的弯腰扑在地磅上笑,有的侧身靠在墙上笑,有的捧腹蹲在地磅上笑。一些过路人站下来看,不明所以,就问咋了,有人笑着说,吃饱撑了。
一个蹲在地上的女人撑了又撑,终于站起身来,看去虽然一副瘫软无力的样子,但还是歪着倒着扑到了二嫂的身边,然后举着无力的双手去挡二嫂伸向汪四媳妇身上的手,边挡边说,二嫂这是拿人家的好心当驴肝肺啊,还好意思这样抓四嫂?汪四媳妇脱出身,一溜烟往五爷这边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笑着坐在了二嫂先前坐的小木椅上。汪四媳妇跑了,二嫂不去抓挡她那女人的脸,弯下身去把手伸向女人胸前胡乱捞起来,说你这心好得很,我看看有多好?女人突地一声惊叫,随着一个转身转到二嫂背后一抱把二嫂抱了,喊说,姐妹们快过来,她还兴乱抓乱捏,今天不给她点颜色看看,恐怕她就不知道锅儿是铁铸的。
看着一群女人围上来,二嫂狠命一甩,脱了身飞哒哒一趟跑过来钻进了五爷屋里。一帮女人追过来砰砰砰往门上拍的拍踢的踢,喊着要二嫂滚出来。
拍上一阵踢上一阵喊上一阵,声势渐渐变得雷声大雨点无。一个女人靠在墙边搂着肚子喘着粗气说,别说你才躲进五爷屋里,今天,你就是钻到五爷被窝里去,我们也要把你揪出来。一个女人助阵似的,又去拍了一阵门。汪四媳妇说不要拍了不要踢了,还叫她出来做啥?接着她望向五爷说,五爷,这下,我们可是把她送到你屋里了,以后,别说我们没帮你啊。汪四媳妇离开人群走到音响边,弯腰俯身噗一声将音响电源关了,直起身来说,走了,回家了。焦点平台
一个女人说,还早嘛,不跳了?
汪四媳妇说,跳?跳啥跳?一点音乐都不懂,你还跳啥舞?
外面安静下来,只剩下五爷吸烟筒的扑通扑通声。二嫂将门打开一条缝,虾着身子伸出头来往两边看了看,问五爷说她们走了?五爷说走了。二嫂这才将门大打开,像是不完全打开,那门就不够她走出来。门大大地打开了,她又就着屋里的灯光,摸着抹着看了看衣服,理了理头发。衣服都是伸展的,那头发,却是怎么理也理不顺,倒像是越理越乱的样子。二嫂一点儿身也不侧,正正直直地走了出来。站在门外,二嫂说这帮死婆娘真是,真是扛着张乌鸦嘴乱说。
五爷说你没事吧?
二嫂说没有。
顿了一下,二嫂又说,我走了。
五爷放下水烟筒站起身来,说,我送送你吧?
二嫂又顿了一下,说,你就不怕她们说?
五爷望向二嫂,说,我怕啥怕?要是你怕,我就不送了。
二嫂抬头望向头顶的路灯,脸上突地弥漫上一阵凄楚。她咬了咬嘴唇,说,我又有啥怕的?说着,迈开步子就往安置区里面走了去。五爷返身将门拉上,紧跟几步便跟到了二嫂的身边。焦点平台
安置区的房子虽然是各家修各家的,却经过了政府的统一规划。一条路进去,路两边就是一栋一栋的房子。五爷知道,这些房子后面,就又是路;路后面,又是房子。两排房子中间设一条路。这样的路有四条。往里走上一段,五爷那路灯的灯光就被他们甩在了后面。拐过一道弯,五爷那路灯的灯光,就一丝丝儿也没能跟上来了。里面人家的路灯,这时一盏也没亮。二嫂掏出手机来打开手电,她边照着自个儿往路沿的墙边走,边说,走这边,那边有水。说着,还站下来等五爷。五爷跟随二嫂移动着的手电光,一步一步走到了二嫂身边。在二嫂要转身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五爷蹭上去,用往前甩去的右手抓住了二嫂的左手。二嫂似乎愣了一下,但接着,她继续用右手打着手电,将左手拖在后面丢在了五爷的手里。
过了有水路段,他们也没有往路中间去走。二嫂将手机的手电关了,仿佛担心那光会引来什么。二嫂也没有抽出手去的意思,她抓起了五爷的手。五爷感觉自己是被她拉着走似的。
五爷希望这路没有尽头,希望能这样一直走下去。
但哪能呢。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安置区。焦点平台
二嫂在一栋房子门前停了下来。二嫂往外抽手的时候,五爷觉得那像是他和她就要永别了一样。二嫂掏出钥匙打开门独自走了进去。一里一外,二嫂转过身来定定望着五爷,像是望了很长时间,说,你真是为了我回来的?面对二嫂的目光,五爷不敢迎上去。五爷心跳加快,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真想说是,然后扑过去把二嫂揽进怀里。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想起郭老三说过的二嫂那成器的两个孩子。郭老三说,常二两口子,人家硬是把两个娃盘成了大学生,端上了铁饭碗。他倒不是怕他们,他只是觉得,如果,如果他真和二嫂在一起了,别人一定会说他是冲着那两个孩子,想享那两个孩子的福去的。
五爷将目光投向夜空。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在那儿无声地眨巴着。五爷说,哪呢,这是我自个儿的家,我回来就是了,哪还要为哪个?
二嫂的脚突然地迈了出来,但她又突然地收了回去,那你为啥去了几十年一次都没有回来过?这次回来,我以为你修了房子就会走,你却又在那儿装了那么一个地磅,还就你一个人在这儿,你媳妇呢?你没有娃娃吗?还是你跟她,离了?
谁家的窗子拉出了一声脆响。五爷向那发出声响的地方望了一眼,待他回过头来,心里倒不那么虚了。他说,没有,我啥都没有,现在,就那点儿房子,还有那地磅。五爷又说,不过,也已经够了。焦点平台
二嫂扭头看了一眼房子里面一梯一梯高上去的楼梯,回过头来时,眼里已蓄起了泪花,自语似的说,好,这就好,我还就担心你是为了我才回来的呢。说着,二嫂也不再顾忌啥,举起手来抹了一把眼泪。一把眼泪抹过后,二嫂的脸仿佛变了一张,尽管笑得不那么好看,但她还是笑了,她笑着说,你要不要上去坐一坐,只是我那屋里,没,没燃炭火,没你那儿热乎。
五爷的脚已经提了起来,但他又把它放回到了原地。五爷咬了咬嘴唇,说,时间晚了,改天吧。五爷又说,改天,我给你燃笼炭火。
四
门前的音响一响,五爷就像多年前听到出工的哨声,呼地站起了身来。只是五爷没急着出门。他把煨水壶老高提起来,缓缓往搪瓷茶杯里续水。
杯里的水没浅下多少,但他续水的过程,恒久而漫长。那线悬挂于空的水,扭着柔软腰身,大珠小珠落玉盘一般在杯里的水面上扑打出零零散散的水花。茶水续满,五爷又撑了撑已经有些佝偻的腰,抻了抻厚实的黑棉衣,这才转身摁亮路灯,端了茶杯,从沙发旁提上水烟筒缓慢走出门来。
音响的声音,可谓洪亮。沉闷的混响,一波一波震得五爷的心颤颤巍巍地晃。“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听这曲子,五爷的耳朵都听起了茧。但他没有听厌,倒像越听越喜欢的样子。举目望去,常二嫂正在吆喝着那帮女人站队。女人们大都五十来岁,也有小点的,四十多五十不到的样子。人虽不多,就那么十个,但她们移来移去的散乱脚步,还是在那硬实但因为下面虚空的地磅上,踩踏出了噼噼啪啪的声响。听着这声响,五爷已不再心疼。也是,几十吨上百吨的车开上去都没事,她们还能把它踩破踏烂?焦点平台
不但不心疼,他反而喜欢上了这声音。
五爷吃饭啦?五爷刚在靠背椅上坐下,就听到汪四媳妇问。五爷把茶杯往旁边的石板上放了,边将烟筒往胯前挪,边说吃了嘛。
二嫂叫你起来跳舞。
你们跳,我跳不来。
起来我教你跳。
你们跳,我学不来。
要二嫂教你才能学?
女人们一阵嘻哈笑。
五爷将脸从烟筒里拔出来,说,我笨手笨脚的,神仙来教都学不会。
神仙来教恐怕你还真学不会,但二嫂教,你肯定学得风快。
又是一阵嘻哈笑。汪四媳妇说,要得会,先跟师傅睡。我知道你跟二嫂跑了那么多的南天门为啥连个舞都没学会了。
二嫂说是了嘛,这下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四嫂了。
汪四媳妇说好啊,只怕五爷没这个胆。
再一阵嘻哈笑。
汪四媳妇也笑。笑一阵,汪四媳妇又说,实在不跳,就回去烤你的火了,别在那儿冷出个三病两痛来,我们负不了责。焦点平台
天气确实冷,已经是冬月了。北风虽然不疾,却硬,拂在脸上,像快刀在割,细条在抽。五爷不答话,抬头往屋檐下挂着的那颗灯泡看。一群没被冷死的蚊蝇还飞在灯泡周围,时不时撞击出噗噗的声响。五爷往烟筒栽烟的小嘴上塞了一小撮烟丝,烟丝在他扑通扑通的吸声中红了起来亮了起来。抱着这烟筒,五爷仿佛抱了一团火,一阵又一阵扑通声响起,北风拂出的痛,隐了,冬月天气浸出的冷,也消了。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
又一阵重音袭来,歌曲已响成《套马杆》。抬头看去,几个女人已站成两排,甩着臂扭着腰,还时不时地弯一下身,跳了起来。
见队伍排得差不多,二嫂走到音响旁,将音响上原来的U盘拔了下来,换插了一个上去。二嫂说,从今天起,我们来学一套新的。
二嫂这是要开始点她的三把火了啊?有人说。
教大家跳之前,二嫂自个儿将新舞完整地跳了一遍,说给大家先有个整体的感觉。二嫂一个人在地磅上跳的时候,仿佛不是为了教女人们跳舞,而是在进行一个舞蹈节目的表演。汪四媳妇看完后说二嫂就是二嫂,这舞好看,这舞好看,从哪学的,我以前咋没见过?汪四媳妇又说,这么久我也没去清官亭,是不是那儿有人又跳出这新花样来了?二嫂说我才懒得去跟他们学,老远八远的,我又没吃饱了撑着。我这是从网上学的。焦点平台
网上?二嫂还会从网上学舞?看看,看看,不愧是高中生,有文化就是好,跳个舞玩,都能从网上去学。一个女人说。
所以说,我这让贤,让得是多明智。汪四媳妇说,以后你们学着的多了,有二嫂的功劳,也有我的功劳啊。
二嫂说,这样说来,你的“母”劳最多。
五爷将烟筒挪靠在身后的墙上,袖起双手,将身子匍匐在了双膝上。看了一阵后,他就没再去看女人们的舞,而是微闭双眼,在嘣嚓嘣嚓的重音中,寻起了她们踩踏出的不那么整齐的噼噼啪啪声。没多时,他就找到了二嫂踩踏出来的声音。对,常二嫂踩踏出来的声音。嚓,嚓,嚓,嚓嚓,嚓嚓嚓。节奏分明,清晰有力。在或嘣或嚓的音乐声里,五爷尽管微闭双眼,但常二嫂的一步一挪、一点一踢、一个转身、一个弯腰,依然是那么清晰地在他的眼前晃动。似乎,他还感觉到了常二嫂在转身时甩动的衣摆带起的风,那风拂在他的脸上,不但温柔,还带上了温暖。
渐渐,在或嘣或嚓的声音里,五爷就当起了指挥,他在脑海中要常二嫂转身的时候,常二嫂就转身了;要常二嫂踏脚的时候,常二嫂就踏脚了。
简直就是夫唱妇随啊。
五爷的脸上,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嘟——嘟——嘟——一串破空而来的喇叭声吓了五爷一跳。循声望去,一辆卡车已停于路旁,猩红的转弯灯,鬼火般在那儿一闪一灭。焦点平台
鬼追着了?吓老娘一跳!
开别处称去要不得,没看老娘们在跳舞?
女人们说归说,舞步却是停了,鸟散状往边上让。
五爷看着往边上让的女人们,很勉强地站起身来,懒懒地往路边走去时,五爷还转身望向她们。明亮的灯光下,能看见他笑着的脸上,像是每一条皱纹里都含满了歉意。
五爷还没指挥尽兴,二嫂她们一天的舞就跳结束了。
二嫂她们刚走,五爷就开始盼望起了下一个夜晚。
这以后,五爷在天还老早八早的时候就开始打扫并清洗起地磅来。在打扫和清洗地磅的时候,他先是偶尔感觉到腰酸和背痛,酸了痛了,他就撑起身来,伸伸懒腰舒展舒展筋骨。这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一副幸福的表情。想着二嫂舞蹈时裙摆带起来的风,他的这点酸痛,就会烟消云散。但渐渐地,他腰酸和背痛的频率越来越频繁。时不时地,他还感到了胃痛。他以为真是自己老了,这腰这身不耐事了。不觉中,他发现开来过磅的车,装载煤炭的越来越多了。是这越来越多的载煤车掉落在上面的煤炭煤灰,让他一开始扫起来,就不能停下。这辆掉落的还没打扫完,那辆就又开来了。
五爷想起汪四媳妇说过要给他弄点生意的话。
五爷不知道是她,还是汪四,跟炭山上的人打了招呼?焦点平台
五爷不想这样。在汪四媳妇来跳舞的时候,他甚至走去给汪四媳妇说,麻烦主任打打招呼,让这些车少开来点。汪四媳妇愣在那儿,一起来跳舞的女人们也惊讶不已。汪四媳妇说,五爷你说啥,我咋听不懂?二嫂说,你要麻烦咱们的汪大主任自个儿找他麻烦去,别又在这儿打咱主任夫人的主意。
五爷搓着双手,说,我已经够麻烦主任的了,我哪敢再去麻烦他。这不,拉煤的车多了,我扫不过来洗不过来,怕影响你们跳舞。
汪四媳妇咯咯笑起来,说,扫不过来也要扫,你不扫干净,咱们的二嫂可就不来了。为考验你对二嫂的诚心,我还得让他们再多来。
对。对。就让他们多来。看看五爷这心诚到啥地步。
一个个女人,嘻嘻哈哈嚷了起来。
诚你们的头。二嫂指着女人们在的方向说,他对我诚啥,他扫这个,可是大家都在跳的,他为你们哪个扫的,恐怕只有天才认得。
一个女人哈哈笑着说,不是为你扫的,为我扫的得了。
又一个女人嘻嘻笑着说,五爷,你不会是为我才扫这么干净的吧?
歌声响了起来,是一首新歌。“我时常一个人独自彷徨,也时常一个人独自流浪。”二嫂不但从网上学了新舞来教女人们跳,还下载了以前没有听过的曲子来放。“我希望你能回心转意,再像从前那样的爱我。”五爷觉得这歌,像是二嫂专为他下载来的。焦点平台
……
本文为节选,详情请参阅《四川文学》2022年第12期

杨恩智:1978年生,云南昭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散文百家》《长城》《大家》《啄木鸟》《边疆文学》《山东文学》《四川文学》《西湖》《特区文学》《滇池》《小说林》等刊物发表过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出版有散文集《被风吹净的村路》、短篇小说集《如画似书》、长篇小说《普家河边》。
焦点平台: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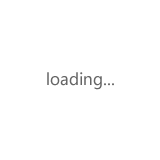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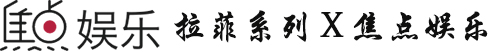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