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网快讯:

赵大河,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作品见于 《人民文学》《十月》《花城》《山花》《中国作家》《美文》 等刊。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 《隐蔽手记》《北风呼啸的下午》《六月来临》,长篇小说 《黄雀》《我的野兽我的国》《侏儒与国王》 等。话剧作品有“开心麻花”系列 《想吃麻花现给你拧》 等多部暨 《大魔术师霍迪尼的最后遁逃》 等。电影有 《四妹子》 等。电视剧有 《湖光山色》《乐活家庭》 等。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杜甫文学奖、曹禺杯戏剧奖、《中国作家》 短篇小说奖、蔡文姬文学奖、河南省优秀文艺成果奖、金盾文学奖等。
六大夫是在一个大雾天回来的。白色的雾像牛奶一样浓稠,睁大眼,看到的只是一片深深的白。房屋和树木都消失了,只有路在脚下隐隐约约地延伸。马和马上的人都很疑惑。他们竟然没有迷路,径直来到了贾赵村。
六匹马停在一个半开放的院子前,院子里面是一个草房子,马上五男一女。
一只黑狗朝他们叫几声,跑开了。
六大夫跳下马,去扶一个女人下马。其他四个男人端坐马上。其中一个朝六大夫“嘿”一声,朝他扔一袋银圆。六大夫伸手在空中接住。银圆发出清脆的声音。他掂了掂,大约有五十块。四个男人没有久留,牵上另外两匹马又上路了。焦点娱乐
很快,六匹马和四个男人被大雾淹没了,马蹄声渐渐远去。
六大夫看着被搅乱的雾又恢复原样,这才回头。他惊讶地看到许多影影绰绰的身影,像幽灵一般从雾中浮现。黑狗又出现了,躲在歪脖的腿后,歪脖拍拍它的脑袋。人们认出了六大夫。六大夫穿着长衫,因为骑马的缘故,前后摆撩起掖在腰里。他和乡亲们打招呼,大伙笑着回应。六大夫离家多年,如今归来,穿上了长衫。在他们眼里,穿长衫的六大夫显得古怪而陌生。但毕竟是乡里乡亲,大多有血缘关系,一会儿工夫生疏感就一扫而空。他们开起了玩笑。大家更关心的是六大夫领回来的女人。
“哎哟,这女子俊的,像画一样。”
说话的,六大夫叫她三嫂,城里人,和木匠三哥好上,就嫁到了贾赵村。她说话好听。
说话不好听的是贾二嫂,她背后嘀咕:
“在哪儿弄了个妖精回来?”
很多人附和:“是,妖精。”
农村哪有这样的女子,衣服小得紧紧箍在身上,两个奶子简直要把衣服撑破,腰细得一把能攥住,她也不羞。虽然好大雾,人们仍然注意到这个女人穿金戴银,红口白牙,目如流星。
六大夫向女子一一介绍乡邻,这个是二嫂,这个是三嫂,这个是九婶,等等。介绍到二流子歪脖,他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大名,卡壳了。焦点娱乐
贾二嫂说:“歪脖啊,你不认识了吗?”
六大夫说认识认识。
歪脖挑衅似的对六大夫说:“那你说我叫什么?”
六大夫讪笑着说:“兄弟,你瞧……”他仍没想起歪脖大名。
贾二嫂说:“歪脖,你还有大名?我怎么没听说过?”
“那是你耳背,”歪脖说,“听不见。”
“你说你叫啥?”贾二嫂说,“恐怕你自己都不记得。”
三嫂添油加醋地说:“我也不知道歪脖还有大名。”
歪脖大声说:“我叫贾够梁,贾够梁,你们记好了!”
大家都笑,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歪脖的大名。人们说:“还是歪脖好听。”
说说笑笑,气氛轻松下来,雾也渐渐散去一些。
最后,六大夫介绍这个漂亮女人,说是他老婆,叫小梅。
歪脖毫不掩饰地歪着脖子看这个漂亮女子,恼恨眼前的雾,让他看不真切。歪脖这样看人是很失态的,但他不管。
贾二嫂说:“歪脖,你看地上是什么?”
歪脖说:“什么?”
贾二嫂说:“你眼珠子掉了。”
歪脖翻个白眼,说:“管你甚事。”
六大夫的草房久不住人。钥匙也找不到了。只好把锁撬开。歪脖帮忙撬锁,六大夫一再交代要小心,别把房屋弄倒。这房子看上去弱不禁风,一根手指头就能戳倒。房门打开,屋里丝丝络络全是蛛网和灰须溜,遍地老鼠屎。房顶有几个窟窿。
“能住吗?”贾二嫂说。
“拾掇拾掇,咋不能住。”六大夫看一眼小梅,充满信心地说,“能住。”焦点娱乐
六大夫脱掉大褂,动手拾掇屋子。人们没想到的是,小梅也绾起袖子干活了。这么漂亮的女子竟然不怕脏不怕累,身手还很麻利。乡邻们一边夸赞她,一边加入其中,帮忙收拾。到雾散时,草房子已焕然一新,而每个人都变得灰头土脸。大家相视一笑。六大夫要去打水,歪脖把桶夺过去,说他来。水井就在六大夫屋后。歪脖前头走,黑狗跟在后面。
歪脖打来两桶水,大家都洗干净。
泼水时,六大夫发现墙角的连翘开了,几朵鲜嫩的小黄花。
乡邻走了之后,六大夫叫小梅来看小黄花。小梅蹲下,仔细看每个花瓣,看着看着眼泪落下来了。
六大夫对小梅说:“委屈你了。”
小梅擦干眼泪说:“委屈啥,不委屈,不用担心我,我没事。”
六大夫看天色不早,急匆匆出门,天擦黑时回来,背着一大包东西,手里拎着锅碗瓢盆。他像是有八只手,拿那么多东西。那一大包是置办的新被褥。
夜里,二人躺在床上,看着房顶的窟窿入睡了。半夜,小梅突然大叫一声跳起来,惊得房子都颤抖了。六大夫也跳起来,大叫一声。原来是老鼠钻进了被窝。他们再也无法入睡。静夜中,他们听到成群的老鼠跑来跑去,唧唧唧叫着。他们呵斥一声,老鼠消停一会儿,复又如故。六大夫打着火,眼前的景象吓他们一跳。遍地发光的小点点。定睛一看,全是老鼠的眼睛。焦点娱乐
六大夫想找根棍子驱赶老鼠,拉开门,他撞到一个黑影身上,受到更大惊吓。
“谁?”
“我。”
“我是谁?”
“我是歪脖。”
那黑影也吓一跳,这时稳定下来,想好了说辞。他说他听到叫声,过来看看出什么事了。歪脖带着他的黑狗。六大夫能听到黑狗喉咙里发出的声音。他没戳穿歪脖的谎言。歪脖和他并非邻居,能听到他们的叫声,他可真是顺风耳。
“有事吗?”歪脖问。
“没事。”六大夫说。
“没事就好。”歪脖拍拍黑狗的头,和黑狗一起走了。
歪脖三十多了,没娶来媳妇,整天东游西荡,小偷小摸。他怎么会在院子里?听墙根还是偷东西?不管哪样,都叫六大夫恶心。他朝黑暗中啐一口。
第二天,六大夫到我们家借大狸猫。我们家的狸猫是猫中之王,逮老鼠可厉害了。它有很多传说,不但能捉老鼠,还能爬到树上捉鸟。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下故事发生的时间,那是1947年。那时候,我奶奶还年轻,我父亲只有十来岁。
六大夫早年的故事都是前些年我父亲讲给我的。父亲记性特别好,讲起故事绘声绘色,但他以前对六大夫没有什么印象,可讲的并不多,因为六大夫总是在外游荡,很少回村,回来也是蜻蜓点水,点个卯就又走了。这次六大夫回来,看样子是要长住。焦点娱乐
表面上看,六大夫很低调,大雾天悄然回家,不事张扬。但他带一个美丽女人回来的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瞬间把村庄掀翻了。
村里人找各种借口来看六大夫带回来的女人。小梅一点也不害羞,看就看,你看我,我也看你,不吃亏。
六大夫到我们家借猫,找的是我奶奶。狸猫是我奶奶养的。我奶奶二话没说就把狸猫借给六大夫。
第三天,六大夫到我们家还猫,说狸猫和群鼠大战三百回合,终于把群鼠降服。猫身上血迹斑斑,六大夫说那都是老鼠的血,猫没受伤。据说猫咬死了一堆老鼠,六大夫装了半筐子。六大夫送一斤盐给我奶奶,我奶奶说什么也不要。六大夫给我父亲几根甘草,我奶奶说拿着吧。父亲接过去,放一根在嘴里嚼。
没了老鼠,六大夫和小梅就躲在小院里卿卿我我过起了小日子。六大夫从不下地干活。客观原因是没有地,他的地让他哥种着。他靠什么生活,没有人晓得。他是大夫,可是没有什么人找他看病。村里人有病都找八大夫,不找他。八大夫为人和蔼,有钱没钱都给看。有时候,八大夫给病人说一个偏方,就把病治了。比如有人得了蛇胆疮,八大夫说,去,到坟园里,找那下垂的油柏,折几枝,拿回去烤干,研磨成粉末,用香油调和,抹上几次就好了。如此这般,怎么收钱?我这样一说,你就晓得人们为什么看病要找八大夫了。六大夫完全不看病吗?也不是。偶尔有外面来的人找六大夫看病。六大夫好用虎狼药,他给病人说到明处,这吃下去,要么好,要么死,你可要想好。病人思虑再三,最后一咬牙,说就这样吧,开药!结果是,有的好了,有的一命呜呼了。有一段时间,全是后一个结果。六大夫感慨,我手上带炮子儿,看一个死一个。这是后话。我小时候对六大夫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其他小孩也一样,谁身体不舒服,我们就起哄说:“快,快去找六大夫给你看看,他手上带炮子儿,看一个好一个。”焦点娱乐
六大夫长得丑,也没什么钱,却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乡里很是轰动。接连几天,来看新媳妇的人络绎不绝。借口各种各样。
六大夫脾气古怪,脸色阴晴不定。小梅却总是一脸笑,对谁都很热情。人们感觉和小梅更亲近,什么都对小梅说,恨不得把村里一草一木的来历都告诉她。事后,他们私下里聊天时,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是透明的,可是对于小梅的身世,他们一无所知。他们不是没问过,但每次都被小梅巧妙地岔开了。他们唯一知道的是,小梅是洛阳人。
小梅很会来事,善于和邻里搞好关系。她的主要手段是借东西。有借就有还,还的时候,她总是加上利息。比如借一平碗面,她必定还冒高一碗。借一小勺盐,她必定还一大勺。借半个皂角,甚至会还半块洋碱。邻居们都说小梅大气。焦点娱乐
小梅的好形象树立起来了。六大夫变成了小梅背后的男人,成了一个隐形的存在。六大夫深居简出,整天在屋里翻看古医书,《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千金方》等等。
不久,小梅的腰身变粗了,这时已是夏天,什么也藏不住,女人们猜测她有喜了。一问,果然是。过来人毫无保留地向她传授保胎秘诀。
六大夫和小梅的幸福生活让人嫉妒,不久就招来了流言。流言是关于小梅身世的,说小梅不是良家妇女,是窑姐儿,她怕人们知道她的底细,才故意隐瞒身世。谁说的?我们村的女人不轻易相信流言,一定要弄清出处。问来问去,最后全都指向歪脖。是歪脖说的。问歪脖可有证据,歪脖说他也是听别人说的。别人是谁?歪脖说是一个曾找六大夫看过病的商人说的。商人说他见过这个自称小梅的女人,在一家妓院里。人们对歪脖的说法嗤之以鼻。
小梅听到风声,就不出小院了。
更可怕的是,没多久小梅竟死了。六大夫说她得的是急性瘟病,吃了虎狼药没救过来。停尸在草房子中间。
有人嚼舌头,说是六大夫把小梅折磨死的。八大夫听到后,说:“积点口德吧,小心舌头生疮。”
还有人说,是老鼠精报复。这又要说到我们家的狸猫。前面说过,六大夫说狸猫与群鼠大战三百回合,才打败群鼠。我奶奶听了撇撇嘴,不信,但是没反驳他。通常情况下,狸猫“喵”一声,老鼠都吓得屁滚尿流,哪还有胆量与狸猫战斗。六大夫信誓旦旦,说是他亲眼所见。据说,指挥群鼠与狸猫战斗的正是老鼠精。老鼠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想方设法让小梅得了瘟病。焦点娱乐
瘟病是传染的,所以当天夜里就匆匆下葬了。
与其说这是个普通的葬礼,不如说是个草率的葬礼。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个葬礼不会再被人们提起。
葬礼之后,六大夫就消失了。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用“消失”这个词的,因为,六大夫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出门,更不用说去哪里了。就这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起初,人们以为他到外村出诊了,多日不见回来,才意识到他又“消失”了。
六大夫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突然出走,在外游荡几个月或几年,在大家将要把他忘却的时候又突然归来——所以大家不以为意。人们猜测,他妻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导致他离家出走。他这人虽然古怪,但对小梅却是疼爱有加。我奶奶说她有一次去六大夫家,看到六大夫正在给小梅吹眼睛,可能小梅眼里进灰尘了。吹眼睛不算什么,六大夫那种疼爱关切的表情给我奶奶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奶奶说,没见过男人那样。贾二嫂说,小梅是六大夫的心尖肉。再说了,小梅死的时候,大着肚子,这是一尸两命,哪个男人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焦点娱乐
几个月过去了。六大夫没有回来,回来的是那四个骑马的男人。也就是春上大雾天送六大夫和小梅回家的那四个人。当初那么大雾,谁也没看清那四人长什么样。他们完全是揣测。
这是个冬日,还有大雾。人们正是从这一点判断这四个人与当初那四个是同一拨儿人。云从龙,风从虎,雾从这四个男人。雾因他们而起。他们身穿黑衣,腰里别着盒子炮,一个戴着礼帽,两个光头,还有一个留着长发。这日虽然还是大雾,但比春上那场雾差远了。
他们在六大夫院门前勒住缰绳。四匹高头大马喷着鼻息,踢腾着腿。
六大夫的院子没有门,是一个半敞开的空间。四匹马如果都进到院子里,会将院子挤爆。
戴礼帽的男子打马进去,在院子里转一圈。草房子的门上挂着锁。他挥舞马鞭朝屋檐抽一鞭,腐朽的屋檐掉下一大块,尘灰飞扬。
他跳下马,一脚踹开门。门连同门框向里倒去,砸起一股呛人的烟尘。草房子摇晃几下,差点倒掉。等烟尘散去,他进到屋里看了看,空空如也,也没有近期生活的痕迹。他从屋子里出来,翻身上马。
看热闹的村民呈弧形散开,与他们保持五步距离。焦点娱乐
戴礼帽的男子问村民:“六大夫去哪里了?”没有人回答他。他又问:“他带回的女人呢?”还是没人回答。他腿一夹,马往前两步,马头快顶住贾二嫂,贾二嫂往后退一步。他用马鞭指着贾二嫂:“你说!”
“死了。”贾二嫂说。
“谁死了?”
“你说的那个女人死了。”
戴礼帽的男人嘟囔一句:“怎么会死
呢?”他不相信,又用马鞭指着歪脖。
歪脖后退一步,手放在黑狗的头上,不让它叫。歪脖也说那个女人死了。“真的,”他说,“坟园里那个新坟就是她的。”
戴礼帽的男人盯着歪脖,歪脖又后退一步。
“你的脖子怎么啦?”戴礼帽的男人问道。
“生来就这样。”歪脖说。
“真的吗?”
“真的。”
“没骗我?”
“没骗你。”
那男人突然一马鞭抽过来,歪脖猝不及防,马鞭正抽在脖子上,抽出一条红印。歪脖跳起来,哎哟一声,脖子仍是歪的。黑狗朝戴礼帽的男人吠叫起来。那男人说:“果然没骗我。带我去看坟!”
坟园就在村边。新坟也不新了,但能看出那一抔土与别的坟不同。歪脖指着这个土堆说:“这个就是!”
戴礼帽的男人问:“那个女人是怎么死的?”
歪脖说是瘟病。
那男人又问:“死时什么样子?”歪脖不明白他的话,说就那样。
那男人进一步问:“她肚子大吗?”
歪脖说:“大。”他比画一下,“肚子上像扣个锅。”焦点娱乐
戴礼帽的男人跳下马。其他三个男人也跳下马。他们围着坟看来看去。一个土堆,有什么好看的。村民们脸上满是疑惑的表情。
戴礼帽的男人用马鞭顶了顶礼帽,吩咐另外三个男人:“去,找几个镢头或铁锨。”
焦点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这是要干什么?人们纷纷猜测,心头有不祥预感。有人悄悄离开,去叫族长。
族长是我们本家的,辈分很高,我父亲管他叫大爷。
三个男人拿来镢头和铁锨,就要动手刨坟。族长带着一群人及时赶到,阻止他们。
长发男人掏出枪说:“谁拦打死谁。”他抬手一枪,树上一只麻雀应声而落。
族长没退缩。
戴礼帽的男人说:“这女人是我老婆,托付给六大夫,她,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谁拦,别怪我不客气。”他眼中杀气腾腾。
族长还要说什么,被族中几个中年人拉走了。他们劝族长,为一个死人,搭上活人的命,不值当。族长骂他们没种儿,叫几杆破枪吓住了。
几个人开始挖坟,因是新土,挖起来不费力,一会儿工夫,棺材就露出来了。戴礼帽的男人一努嘴,两个光头男子跳进墓穴,用镢头撬棺材盖。镢头很难卡入棺材盖与棺材板的缝隙,二人便用蛮力狠砸棺材板,发出嘭嘭嘭的沉闷声响,仿佛死人在诅咒。人们纷纷掩鼻,后退,别过脸去。大人将小孩赶走,不让看。赖着不走的小孩,被大人捂住眼睛。终于镢头嵌入棺材缝隙,用力一撬,棺材盖打开了。焦点娱乐
围观的村民们都愕然,四个男人也目瞪口呆:棺材里并无女人的尸体,只有三块土坯。怎么回事,谁也搞不清楚。死人不翼而飞,土遁了。有人说:“也许那个女人根本没死。”帮助六大夫料理后事的三奶奶说:“死
了,死了,我帮着入殓的,怎么会没死呢。”
那四个男人看着空棺材。戴礼帽的男子铁青着脸踹一脚棺材盖,放狠话说:“你们告诉六大夫,他死定了。”
说罢,四个男人翻身上马,徐徐而去,走出百步之后,身影在雾中渐渐模糊,以至消失。
这一幕是父亲讲给我的。父亲那时十一岁,他属于被赶开的对象。他太小,大人们不让他往前去,说那不是小孩该看的。可他管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被赶开后又悄悄从大人们的腿缝里钻到前面。棺材打开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看到棺材里没有尸体,只有三块土坯。父亲说他看到三块土坯时笑了。他的笑很不合时宜。但他忍不住。这些人大费周章得到了什么?三块土坯!这不是很好笑么。可是其他人都不笑,他们不但不笑,表情还像铁一样冰冷。戴礼帽的人狠狠瞪他一眼,他就不敢笑了。父亲说那种感觉太怪了,笑声在肚子里蹿来蹿去。父亲说:“你不知道那有多难受,肚子里仿佛有一群鹅在打架。”父亲看清了那个戴礼帽的人,他很帅气,五官清秀,如果不是拿着盒子炮,你会把他当成秀才。看得出来,那个长发的和两个光头的都怕他。“长得帅气的人也会很厉害,”父亲说,“人不可貌相。”焦点娱乐
四个人走后,村里人都晓得六大夫惹祸了。那女人究竟是死是活,没有人知道。有人说是尸遁,说得神乎其神。什么叫尸遁?就是死尸会自己遁逃,从棺材里消失。有人相信,有人半信半疑,更多的人不信。
歪脖爱刨根问底,非弄清楚不可。他先问三奶奶:“你帮着入殓的,你说实话,那个女人死了没有?”
三奶奶说:“千真万确,死得透透的。”她又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我还能分不清死人活人。”
歪脖又问抬棺人:“抬棺有什么异样吗?”
抬棺人说:“棺材轻,当时就觉得奇怪,心想这个女人肯定瘦得像芦苇。”
歪脖又问当天夜里谁守灵。这明摆着,六大夫守灵,没有其他人。于是,他得出结论:六大夫根本没把女人埋进坟墓里。
有人问歪脖:“那你说六大夫把她埋哪儿了?”
歪脖歪着脖子,带着嘲讽的表情看着问话人,反问道:“我说他埋他女人了吗?”
那人不服,嘁了一声:“死了不埋,尸体呢?”
歪脖继续嘲弄道:“我说过她死了吗?”
那人说:“咦,三奶奶亲自入殓的,还能没死?”焦点娱乐
歪脖说:“我也没说她没死。”
那人说:“你这不是抬杠吗,依你说,她到底死了还是没死?”
歪脖说:“我哪知道。”
说罢,他吹着呼哨,晃着膀子走了。瞧他那样子,仿佛他知晓秘密似的。
那人在背后骂他:“球样儿!”
歪脖又找八大夫探讨真相。二人都是大夫,也许八大夫能知道点什么。可是从八大夫那里,他一无所获。他问八大夫那个女人得的什么病,八大夫说他不知道,他没给那个女人看过病,六大夫就是大夫,不需要他去给他女人看病。
对于空棺,八大夫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相信尸遁吗?”歪脖问道。
“听说过,”八大夫说,“但是没见过。”
挖出空棺之后不久,村里诞生了一个传说,说六大夫的女人没死,变成了一只火红的狐狸。
见过这只狐狸的人很多。因为它掉到了天坑里。天坑在寨外,是自然塌陷的一个坑,有四五米深,像一口巨大的锅。刚下过雪。可能因为雪的缘故,狐狸才掉进去的吧。天坑四壁湿滑,狐狸没有着力点,上不来,狼狈的爪子在四壁留下许多划痕。最先发现这只狐狸的人是歪脖。他知道狐狸皮值钱,想把狐狸打死,剥皮卖钱。他用石头砸狐狸,狐狸跳跃着躲闪,他一次也没砸中。一会儿工夫,围上来许多人,都用石头和土块砸狐狸。有几次险些砸中。狐狸腾挪闪避,狼狈不堪。焦点娱乐
八大夫路过,看到人们在闹哄哄地往天坑里扔石头和土块,伸头一看,看到那只红狐狸。他喊停,让人们别砸了。
八大夫和六大夫是亲兄弟,六大夫是老六,他是老八,管六大夫叫六哥。他和六大夫反差巨大,八大夫高大帅气,六大夫矮小丑陋;八大夫亲切随和,六大夫古怪严厉;八大夫按部就班,六大夫来去如风……总之,看到其中一个,往他的反面想,就是另一个人。八大夫是我们村很有威望的人,他的话没人敢不听。
八大夫喊停,人们停下来,他们以为八大夫能有好办法抓住狐狸。
八大夫说:“你们看看它。”
狐狸已经跳累了,站立在天坑中间,打量着天坑上面的人。
大家都盯着狐狸,八大夫让他们看什么?
“看它的表情。”八大夫说。
狐狸几乎绝望了,这么多人要置它于死地,它躲无可躲,避无可避。
接下来,奇怪的一幕发生了,狐狸前爪合十,朝人们作揖。
人们说,成精了成精了,这狐狸成精了。
他们搞不清成精的狐狸会不会带来灾祸,要不要把它打死。
八大夫说:“你们还要打吗?”
人们不说话。
八大夫又说:“谁要打狐狸,以后别找我看病。”
人们悄悄将手里的石头和土块扔掉。
歪脖说:“是我先看到的。”
他的意思是,这个狐狸属于他。
八大夫严厉地看他一眼。
八大夫一贯很和善,人们从没见过他有这么严厉的眼神。焦点娱乐
歪脖也扔掉手里的石头。
八大夫让人们散去。他那么严肃,人们只好听他的,陆陆续续离开。但都没走太远,而是躲在墙角、树后,偷看八大夫干什么。
八大夫找来一根长木杆,斜着放入天坑,狐狸明白八大夫在搭救它,顺着木杆爬上天坑,如一道红色的闪电,瞬间消失了。
后来,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传说,说这个红狐狸是六大夫的女人变的。六大夫的女人爱穿红衣服。还有人说,那表情也是六大夫女人的表情。这就太玄虚了。还说八大夫每天早上打开门,都发现门口放一枚鸡蛋,那是狐狸在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父亲说他问过八大夫有没有狐狸报恩的事,八大夫笑了笑,没说有,也没说没有。
六大夫一走,泥牛入海,再无消息,是死是活,没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那一伙人还在找他,而且还没找到。那些人时不时来村里打听六大夫,每次都失望而归。有一次,长头发要烧草房子,戴礼帽的男人制止,烧了房子他就更不会回来了。几个月后,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村。这次,还有雾。雾不大,如轻纱缭绕。有心人回顾之前他们出现的情景,得出结论,他们出现的时候全有雾。莫非他们只挑选雾天出没。
四个男人心事重重,蹲在草房子前吸烟,打发时间。他们在等六大夫吗?当然不是。六大夫哪会这时候出现。马拴在树上。四匹马瞪着空洞的大眼睛。村民们躲得远远的。歪脖曾被抽过一马鞭,鞭痕还在,他更不敢上前。他抱着黑狗,不让它叫。焦点娱乐
三个男人在说着什么,戴礼帽的男人一言不发,只是抽烟。最后,他站起来,把烟头在脚下跐灭,又打量一眼六大夫的草房子,朝长发男人点点头。长发男人打着火,先点燃一把干麦秸,再用麦秸去点草房子。草房子并不像想象的那么易燃,好一会儿才点着。房子已经腐朽,只是焖燃,冒出很大的烟,像蒸笼一样,过了多时,终于腾起一股火苗,然后一发而不可收,熊熊燃烧起来。
四个男人看到火焰冲天而起,这才打马离去。
村民们冲出来救火,已经迟了,草房子一会儿工夫就化为灰烬。
六大夫院里有棵皂角树,皂角成熟时,人们就把皂角打下来,用来洗衣服。皂角树被烧了半边,人们惋惜不已。
不久,宛西解放了。
这年冬天,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新成立的县政府在竹林寺村召开宣判大会。十二个男人被五花大绑,押上临时搭建的台子。县长亲自宣读了对他们的死刑判决,罪名是反革命和抢劫杀人。我们村歪脖在现场。他指着其中三个人说:“那三个家伙来过我们村。”旁边的人问他:“他们到你们村干吗?”“找六大夫的麻烦。”“他们为什么要找六大夫麻烦?”“你问他们。”旁边的人“嘁……”一下,翻个白眼。焦点娱乐
歪脖指的那三个犯人,就是戴礼帽挎盒子炮来村里找六大夫的那个头儿,以及他手下那两个光头。这天头儿没戴礼帽,露着打油的偏分头;两个光头还是光头。他们背上都插着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用红笔打个叉。罪犯都低着头,只有头儿仰头望着人群,从他的眼中看不出恐惧。宣判后,要把他们押到七里河滩,执行枪决。士兵推头儿一把,头儿身子一拧,对押他的人说:“别推,我自己能走。”押解士兵仍然抓着他的胳膊。两个光头互相看一眼,梗着脖子,大踏步往前走。早死早托生。走在最后的大个子罪犯,胆量与他的块头很不相符,吓得尿了裤子,押解士兵推他,他瘫软下来,两个士兵竟然架不住。押解士兵征得县长同意,对他就地执行了枪决。人们哗啦啦跟着看杀人。大块头被枪毙后,他们绕着大块头走。大块头的死法让他们感到失望,他哪像个杀人越货的强盗,这么。有人朝大块头的尸体吐唾沫。
歪脖回到村里神神秘秘地说:“你们猜我在竹林寺看到谁了?”
他说话无头无脑,大家怎么猜。
贾二嫂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歪脖说:“和六大夫有关,你们猜猜。”
贾二嫂说:“那个红狐狸女人。”
歪脖说:“猜对了一半。”
贾二嫂猜不出。其他人也猜不出。歪脖不再卖关子,讲了三个男人被枪毙的事:“他们被押到河滩。枪毙人,都是让跪下,枪对着后脑勺打。不跪?就在腿窝踹一脚,自然就跪了。戴礼帽那个,就是头儿,他不跪,士兵踹他腿窝,他有防备,竟没踹倒。他死到临头,昂首挺胸,丝毫不怕,嘴角挂着笑……枪毙他的时候,他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焦点娱乐
歪脖说那个头儿叫庞一坤,牌上写的是这个名字。他被枪毙后,六大夫就领着女人回来了。这次他没穿长衫,小梅也没穿红袄。他们更没骑高头大马。他们背着两个大包袱——全部的行李,从东边走过来,黄昏时悄然进村。
我父亲那年十四岁,在村边拾柴,远远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觉得奇怪。谁会背着大包袱呢?本村人不会,走亲戚的也不会。他们走到跟前,父亲还没认出他们。六大夫和小梅都变化很大,满脸沧桑。父亲问他们找谁,他们说回家。回家?父亲很疑惑。六大夫也没认出眼前这个后生,他问:“你是谁家的孩子?”父亲回答后,他说:“我是六大夫,你六叔。”
父亲这才认出他们,赶快帮他们拿行李。
多年之后,父亲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个黄昏。天很冷,刮着小北风,外面没什么人。六大夫和小梅走得满头大汗,身上热气腾腾。父亲接过小梅的行李。她道声谢,开始活动肩膀。父亲刚走几步,有些犹豫了。焦点娱乐
“你们家……”父亲说。
六大夫说:“我知道,烧了。”
父亲说:“去我们家吧。”
六大夫说:“你当家吗?”
父亲说:“我爹我妈肯定同意。”
父亲将六大夫和小梅带到我们家,我爷我奶很热情,又是做饭,又是收拾床铺。我们家住房很紧张,但有一个磨坊。我爷奶准备搬到磨坊去住,把他们的房间让给六大夫和小梅。
正吃饭时,八大夫来到我们家,要让六大夫住他那里。他说他有一间空房。我爷我奶说已经收拾好房间了。八大夫说他看到了,磨坊。我爷说磨坊他和我奶住,六大夫和小梅住屋里。八大夫说:“他会忍心把你们赶到磨坊?”六大夫接话说:“是,哪能让你们住磨坊。”我爷还要坚持,八大夫说:“别争了,就这么定。”于是,六大夫和小梅住进了八大夫家。
六大夫回来,人们自然要问他与庞一坤的恩怨过节。六大夫说他不认识庞一坤。这明显是瞎话,你不认识,人家会来找你,会扒你老婆的坟?你把我们都当傻子吗?六大夫咬定他不认识庞一坤。他说他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大家明白六大夫不愿提这桩事,既然如此,也就不问了。可有一个人偏不,你越是不想说,他越要刨根问底。这个人就是歪脖。他刚加入农会,是积极分子,走路头仰得很高,像打鸣的公鸡。焦点娱乐
歪脖问六大夫,六大夫回答仍是那句:
“我不认识庞一坤。”
歪脖提醒六大夫,说庞一坤送他和小梅回来的那天他在场,他都看见了。就是那个大雾天,六匹马,庞一坤走的时候把你们骑的两匹马也牵走了。“那马本来就是庞一坤的吧?”
六大夫不言。
歪脖循循善诱:“你是受压迫者,你应该站出来控诉庞一坤一伙的罪行。那一伙中还有一个长头发的在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的。”
六大夫不言。
歪脖说:“庞一坤已经死了,你还怕啥,有啥不能说的。”
六大夫沉默一会儿,回了一句:“我不认识他。”
歪脖又问六大夫的女人小梅,小梅也说不认识庞一坤。“真的不认识吗?”歪脖直勾勾地看着小梅。小梅被看得心里发毛,但她坚定地摇摇头说不认识。
歪脖去找八大夫打听。毕竟六大夫住在他家,说不定他知道一些六大夫的秘密。八大夫一句话就把他怼回去了:“你管人家的闲事干啥。”
歪脖说:“要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为啥不愿说?”
八大夫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歪脖哼一声,说他会弄清楚的,没什么能瞒得过他。现在,他说话的语气比以前自信一万倍。
……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莽原》2023年第1期。
焦点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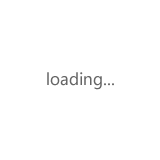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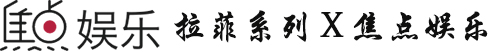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