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快讯:
编 者 按
2013年,《草原》策划推出“草原骑手·九人联展”栏目,优选内蒙古九位青年作家,全年12期进行重点推介,以凝聚和呈现新一代写作者的新气象和新表达。时间的长河奔入2023年,我们欣然看到这九位作家创作质量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并已日渐成为内蒙古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时隔十年,“草原骑手·九人联展”栏目正式回归,一批文学新锐正如骑手般在文学的草原上策马扬鞭,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以作品传递新一代写作者的精神力量。
文学期刊是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重要阵地,积极为青年作家提供崭露头角的机会,是一个杂志的职责所在。这一年,请记住他们的名字:阿尼苏、邓文静、胡斐、景绍德、李亚强、刘惠春、苏热、晓角、谢春卉。
马与人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历史上马与人类的故事俯拾即是。堂吉诃德骑马周游世界,尼采抱马痛哭,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这些历史上的经典故事,让我们更加确信,马与人类的关系之密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马象征着爱、耐力和自由。本期推出的阿尼苏的《绿草白马》以马为题,但不是现实意义上的马,而是作品中主人公情感的外化物。马作为自然界永恒的象征,为作者笔下的人物提供了一种扎根于生活的解药,它如梦境般在现实逼仄的空间里游走,给人以心灵的慰藉。作者在一段独家记忆力里,倾诉着隐隐的哀痛。那宁静的温暖的部分触及主人公内心柔软的角落,它关乎青春、友谊和成长。焦点娱乐注册
1
二十岁那年夏天,我听到了白马的歌声。这匹马在极远的西北,一座飘忽不定的雪山脚下。那里有一片绝美的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白马纯白无杂色,它没有同类,孤单地奔驰。准确地说,它在飞。
我偶然听到了它的歌声。
那个闷热的夏夜,六个舍友一致认为夜里会下暴雨,可事实上,连一滴雨都没有掉下来。到了深夜,舍友们睡去后,我虚弱地躺在上铺,脑子里空空的。这时我隐约听到宿舍门被轻轻推开又被轻轻关上的声音。走廊里的灯光一闪即逝。似乎有人默不作声地走了进来,接着“吱”的一声坐在了我的下铺。我的下铺是个空位,只有一张木床板。
哎——
不一会儿,黑暗中悄然传来轻微的呻吟声。
第二天早上,我问六个舍友,昨夜是不是有人进来了?他们都说没见有人进来。他们趁我还没下床,结伴去食堂吃饭去了。午饭和晚饭时间,他们好像也合起伙来避开我。这种情况持续快一个月了。有一次,我在楼道里揪住舍友巴图的脖领子问,“你们到底啥意思啊?”巴图不停地哆嗦,断断续续地说,“没……没什么……”
我放开巴图,孤单地走在长长的走廊里。我们的教室在顶层。那个月,每天上完最后一节课,我就会站在窗口俯瞰校园。我总有种错觉,不知是我远离了人群,还是人群远离了我。当走廊里的人都走光了,我会沿着消防梯偷偷爬上楼顶。焦点娱乐注册
楼顶空空荡荡的,风很大。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看到夕阳。城市西郊有连绵的群山,夕阳就在那里下沉。我面朝西北坐下,看夕阳缓缓下沉。大片大片阴沉沉的云叠加在无尽的天空上,夕阳在它们的边缘映照出温柔的紫色。这时白色的月亮也悄悄在浮动着的云层后面若隐若现。晚霞绚烂至极,毫无保留地释放着天真的异彩。我的心飞上了天,变成了天空的一部分。我有种在宇宙间行走着的感觉。我身体里某种郁结的情绪仿佛跟着释放出来了。我感到一阵轻松。
我只坐一小会儿,趁顶层还没来人前原路返回。接着,我去食堂或校门口的摊位上胡乱吃点东西。
晚上我泡在图书馆内专门摆放世界名著的阅览室。大家都在复习功课,没几个人去翻阅名著。我以前也不喜欢读这些名著,觉得只有极其无聊的人才读这些笨重、呆板、无趣的书。可那段时间,于我而言,除了看夕阳以外,没有比读名著更有意思的事了。我反复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弗朗茨·卡夫卡的《城堡》和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有时,我把这三本书同时摊开在眼前,一段一段地对比着读。这三本书给我带来了特别的阅读体验。即便我还无法进行更深层地解读,却也沉浸其中,仿佛走进了另一片晚霞。焦点娱乐注册
夜里,舍友们又开始谈论下不下雨的事。这个话题,他们已经延续好几天了。我难以融入他们,索性保持沉默。我在漆黑的空间里,望着触手可及的天花板,想象着约克郡荒野上的艾米丽·勃朗特。想着想着,我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那个人又进来了,依旧“吱”的一声坐在我下铺。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喉咙却发不出声音,身体也无法动弹。可是我在意识里,走在了一条蜿蜒的河边,我看见了那匹白马。它在不远处的山脚吃草。世上任何一个形容词都不能准确地形容它的美。我向它走去,可怎么走也走不过去。突然,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在黑暗中惊醒。宿舍里异常安静。我用手机灯往下铺一照,只看到一张浅黄色的床板。床板在沉闷的空气中散发着潮气,上面回荡着一声幽幽的叹息。当我再次闭眼睡觉的时候,耳边传来一声清脆的马鸣。那匹白马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它飞奔在极远的西北。它跟它身后的雪山融为一体,展现出不可侵犯的威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它。
天渐渐暗下来了。当两个黑夜撞在一起的时候,实与虚并不重要了。我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自然地接受白天和黑夜的交替。恍惚间,灯光一闪,那个人又走了进来。他坐在我下铺开始低吟。不一会儿,低吟变成了欢快的调子,继而变为白马的歌声。一匹白马在我下铺歌唱。很近,又很远。焦点娱乐注册
我不再追问舍友到底有没有人半夜进来。他们依旧躲着我,不敢看我的眼睛,仿佛我的眼睛里有锥子,随时要刺向他们似的。我渐渐地习惯了他们的冷漠。
2
我成了人群中最孤独的那个。每次上课,我独自坐在最后排。老师和同学们的声音忽远忽近。我脑子里时常出现那年春天的情景——
那是一个黄昏,晚霞的光辉洒在校园后面空旷的草地上。我醉醺醺地踩着柔软的草向学校方向走去。我的脑袋嗡嗡作响,眼前的景象微微倾斜。恍惚间,我看到草地中央的凉亭里,三个男生正在围着一个男生拉扯。我以为产生了幻觉,便停下脚步定定神,再看过去,发现这不是幻觉。
伴随着三个男生的笑声和骂声,被围住的男生左脸挨了几个耳光。我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因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就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我用力推开三个男生喊,“你们想干啥呀?欺负谁呢?”三个男生迅速将我围住。他们在我眼前摇晃了数秒钟,其中有个身高一米九左右,满脸横肉的家伙,转头问被打的男生,“这人是谁啊?”他没有得到回应,便狞笑着把手搭在我肩头,说,“这没你啥事,给我滚开!”焦点娱乐注册
读中学的时候,我在校内外打过无数次架,差点被学校开除。最严重的一次,我把一个“校园大哥”的鼻梁骨打断了。阿爸领着我走进校长办公室,当着我的面求校长不要开除我。阿爸的嘴很笨,他生硬地说,“打架肯定不对,但是我儿子本性不坏,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那是我第一次见阿爸流泪。校长叹了口气,说,“写个保证书吧。”从我手臂上渗出的血染红了保证书。阿爸领着我走出校长办公室后,一直没有说话,就那样不紧不慢地走在我前面。长长的走廊里只有我们两人,阿爸沉闷的脚步声让我感到压抑。到了校门口,阿爸说,“回去好好上课吧。”从那以后,我没再打过架,高三那年更是拼命学习,最终考上了师范大学。
说起我中学打架的往事,无非是看不惯欺负人的人。我从心里无法做到冷眼旁观,只要看到了,不上去就不舒服。这扯不上什么正义感,我更没为自己的行为解释过什么。我本就不屑于表达想法,加上我那些“出手”都带着一股狠劲,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觉得我是个难以沟通、难以接近的人。
因为有打架经验,我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出杀气或胆怯。如凉亭里这个高个子,别看他人高马大,眼神里却隐藏着不坚定的恐慌。我摘下眼镜,轻轻推开他的手,上前一步贴近他的身体,盯住他的眼睛,向他脸上呼出一口酒气,平静地说,“别欺负人。”他后退了一步。他显然有些害怕了。焦点娱乐注册
三个男生悻悻离去。
我依旧头晕目眩。走出凉亭后,我躺在草地上大声唱歌,被打的那个男生轻吐一声谢谢,然后一直木讷地站在原地。天上的云越来越少了,温柔的蓝色逐渐被昏黄取代。我不再唱歌,定定地看着天空发呆。酒精在我体内乱窜。过了一会儿,我起身走进了凉亭。男生低着头,用手捂着肿胀的左脸,而右脸下的腮帮子微微凸起。很显然,他正在持续用力地咬着牙。我坐在长凳上问男生,“你也是师大的吗?”他点点头。我故作轻松地说,“以后遇到这种事就直接硬刚,别怕,欺负人的人心里都很虚,很胆怯。”见他不说话,我没再继续追问他的情况。也许,他是陌生人的缘故,我心里没有产生任何芥蒂,开始自顾自地讲起自己的遭遇——
我的烦恼来自开学时的一次被骗。前年秋天,叔叔借走了我家所有的积蓄,又让我阿爸做担保人借贷,后来叔叔跑去外地不见踪影。我的学费拖欠了一个学期,等到新学期开学时,阿爸和额吉四处借钱总算凑齐了学费。可我在交学费前,就看到了叔叔的身影。我情绪激动,差点跟叔叔动手。叔叔却拉着我走进一家正在装修的酒吧。工人们正卖力地干着活。叔叔又把我拉出来,站在街边的一棵树下说,孩子,这是叔叔即将开业的酒吧,等开业就能赚大钱,你家里的那点钱马上就能还上。我的气顿时消了大半。叔叔接着说,不过,叔叔眼下手头还是有些紧。他边说边向里面的工人挥手,工人也向我们挥手。焦点娱乐注册
就这样,叔叔三言两语就把我的学费骗走了。这回,他真的不见踪影了。我不敢跟阿爸和额吉说这件事,但班主任找我谈话,反复强调,再不交学费,不仅找家长,还面临着退学。我心里苦闷,不知该怎么办好,便一个人悄悄买了一瓶烈酒,翻过北郊一家废弃工厂的墙,坐在空旷的水泥地上喝闷酒。
凉亭里的男生一直沉默。直到我们一起快走到学校东门时,他才小声说,“阿吉,我想请你喝酒。”我说,“改天吧。”他轻咬着嘴唇,表现出失落的样子。我们虽然才刚认识,没法像朋友一样直白地交流。但是我不想给他的心意泼冷水,便有些刻板地伸出手臂,搭在他肩头说,“走,我请你。”我们在东门旁边的小酒吧喝了几瓶啤酒。我们聊了很多,他闭口不谈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没有问。他叫巴根那,跟我同级不同系,他在外语系,我在历史系。我们随意地聊了些学校、家乡、爱好啥的。他还给我推荐了几个我从未听过的外国作家。他说,“我希望将来能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时他眼里闪过一丝亮光。我说,“你这么厉害,肯定没问题。”出门时,我发现他已经提前结账。焦点娱乐注册
大概过了一周时间,巴根那再次约我出去吃饭,给我送来了一沓钱。他说,“阿吉,你先把学费交了吧。”他这个突然的行为,弄得我不知所措。我们彼此不知根知底,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朋友,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我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某种负担,他是在讨好我,还是用钱买朋友,抑或在赌友情的价值?甚至,他会不会觉得上次被我看到了他不堪的一面,因而恨我,再用这种方式给予还击,看我在金钱面前软下来的样子,以此证明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内心警惕,却尽量用轻松的口吻问,“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再说,我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他说,“平时家里给的生活费多一些,剩的钱也没地方用,就攒下来了。”我半信半疑,但是看到他衣服的牌子以后,打消了顾虑。我眼下确实需要钱。我心想,也许我错怪他了,他可能就是想单纯地帮我一把。我还钱就是了。我收好钱,写了欠条,他却当着我的面撕了。他说,“阿吉,我信你。”
我很快交了学费,焦虑的心情也缓和了很多。无论巴根那有怎样的动机,也挡不住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感动。在同学们都跟我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下,巴根那像一阵微风似的出现在我眼前,使我心情愉悦。我脾气急躁,容易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加上我各个方面平平无奇,不值得同学们在我身上做感情投资。这也怪我,经常在宿舍里乱说——你们这帮虚伪的家伙。大家都躲着我,谁愿意跟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交朋友呢?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却控制不好自己。焦点娱乐注册
3
从此,我和巴根那的交集多了起来。他不善言辞,但是说起那些名著,会说个没完没了。有时我听烦了,岔开话题聊一些别的事,他只会点头摇头,或笑笑,表现出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他看起来很喜欢待在头脑中虚构的那个世界里。起初我没怎么受他影响,可是时间久了,他有意无意间把我带进了他的空间。他的孤独和我的独行不一样。我更多是现实产生的焦虑,我希望能快点解决问题,也希望能多交到一些真诚的朋友。
但我直来直去的性格,经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他似乎是在躲避着现实,不愿意融入身边的环境当中。他的语言和行为都能说明这一点。
从学校东门那条街一直往南走,走到一栋大厦,再沿着大厦侧面的胡同继续走,就能看见一座并不起眼的桥。桥的另一边是一大片待改造的棚户区。巴根那把我领到桥上,望着长长的铁轨说,“阿吉,沿着这条铁轨一直往西北方向走上一千里,就能到达我的家乡,那里有一片美丽的草原。铁轨到底有没有尽头呢?”我在心里沉思片刻,然后说,“我在镇上长大,没有见过真正的草原,真羡慕你。”他说,“阿吉,我更羡慕你,你想干啥就干啥,真有种。”我苦笑一声,接着问他,“你家乡啥样子呢?”他沉思一会儿说,“有绿草,有白马。”焦点娱乐注册
巴根那的故乡有纯白色的马。巴根那说,当白马驰骋在草原上时,远远望去,就像一片浮动的白云。他的眼里燃起火焰。他讲述的场景令我神往。我说,“暑假去看你家乡的白马。”他说,“好。”可他的声音很低沉。
为了早点还巴根那的钱,我夜里去校外做家教,给初中生辅导作业。这样一来,我跟六个舍友相处的时间就更少了。我每晚回到宿舍,匆匆洗漱完就躺下睡觉。阿爸在镇上开出租车,额吉经营一家民族服饰店。他们为了还叔叔欠下的债,正在努力赚钱。我真想快点结束学业,早日工作。我几乎每晚都在这种焦灼的想法中入睡。
有个周末,巴根那来宿舍找我,见我一个人在,不无羡慕地说,“阿吉,阳面的宿舍真是亮堂啊,又干爽!”他说他目前住的宿舍是阴面,而且紧挨水房,很潮湿,他有腰疾,晚上睡觉时疼得难受。我听出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就说,“我们屋里正好有个空位,你搬过来就是了。”他坐在空位上,用羡慕的眼光盯着木板说,“不好吧。”我说,“这有啥不好的,我跟管理老师说一声。”他说,“这个我可以说,就是怕其他舍友多想。”我说,“放心吧,又没抢他们的床位。”焦点娱乐注册
焦点:www.sdptzc.com
当天晚上我就跟六个舍友说了巴根那的情况。他们脸上的表情都很僵硬。巴图指着空床位说,“我那个床位不好,很早就想换到这了。”我说,“那你现在就换过来吧,然后把你现在的床位给巴根那。”他说,“那倒不用。”我说,“那你啥意思啊?”这时,另一个舍友毕力格图说,“我们本来就人多,再多一个人多挤啊!我说,其他宿舍都是八个人,我们本来就缺一个,这回正好补上了。再说了,你们六个天天在一起行动,从来也不带我,我就不能有个朋友了?”我的话戳在了他们的心上,他们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巴根那抱着行李来到了宿舍。但是六个舍友表现得阴阳怪气,显然不想接纳他。巴根那很不自在,想离开,犹豫半天,却没有走。其实,我心里知道自己的行为很莽撞,没有为舍友们着想,只考虑了自己的哥们儿义气,而没有细想,这究竟会给巴根那带来什么。总之,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
直到有天夜里,宿舍已经熄灯。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凉亭里的那三个男生竟然带着另一个人闯进了宿舍。他们想把巴根那单独叫出去。我跳下床,挡在巴根那面前说,“我跟你们出去。”新来的那个人傲慢地说,“好啊。”焦点娱乐注册
我刚跟他们出去,他们就关了宿舍门,在走廊里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耳边不停地传来高个子男生的声音,叫你多管闲事,叫你多管闲事……
直到从楼下传来舍管老师的呵斥声和脚步声,他们才跑出了楼道。
原来,新来的那个人是所谓的“社会人”,那三个男生是外语系大四的学生。他们得知巴根那家条件不错,便借钱不还,巴根那找他们理论,却被他们打了一顿,而且他们隔三岔五就去巴根那的宿舍进行恐吓。但是经过走廊打架一事,再加上三个男生本就有留校察看的处分,这次直接被开除了。
当我再次把手搭在巴根那肩上的时候,他却表现得异常冷漠。他站在桥上,望着黑夜里的铁轨说,“阿吉,我真的是因为有腰疾才搬进你们宿舍的。”我说,“我知道啊,我又没说是假的。”他轻轻推开了我的手。当我想跟他一起回宿舍的时候,他说,“我想自己回去。”可那天夜里,他没回宿舍。
4
第二天早上,巴根那回来取了几本书便上课去了。我们班没有课,我去超市买了点日用品,回宿舍时,看到毕力格图和巴图两人坐在巴根那的床上。毕力格图手里拿着一个绿皮笔记本,饶有兴致地读着什么。他们见我进来,赶忙把笔记本塞入巴根那枕头下面,尴尬地说笑着起身走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个人,走廊里也空空荡荡的。夏季花草的香气从窗口飘进来,校园内透着一股寂寞。焦点娱乐注册
中午,我换好衣服去户外打篮球。我第一次与巴根那相识的草地后面,有一家废弃的工厂,就是我独自喝过酒的那地方,那里有个破败的篮球场,经过我跟巴根那的简单修理后,勉强可以打半场。那里几乎没有路过的车辆和行人,附近的路也都坑洼不平。工厂门锁着,得翻墙进去。我和巴根那偶尔去练球。
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独自一人在烈日下投篮。天越来越热,四周寂静,篮球撞击篮板发出的声音格外清脆。
阿吉——
突然传来巴根那的声音。他穿着那套大两号的篮球服,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我没问他是怎么知道我在打球的,而是直接把球传给了他。我们相视一笑,然后一起打球。我们一对一对抗。他像打了鸡血似的一直跑个不停。他进了好些球。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出来,我在放水。不过那天,他确实有手感,总是随手一抛,球就进了。他不停地跑,我也配合着跑,直到跑不动。
我们汗流浃背地躺在篮球场上,仰望高远的天空。巴根那指着一朵白云说,“如果天空是草原,那朵云就是白马。”他沉默了好一阵,坐起来,咬着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继续说,“阿吉,我很小的时候没了额吉,现在的是后来的……小时候,我们家有一匹漂亮的白马,我总是幻想着骑上白马,驰骋在无边的绿草上,甚至骑上天空,远离那个家。”焦点娱乐注册
巴根那每次说个人情况时,都像是在心里经过了无数次排练。我没回应他的话,更没表现出同情的样子。看得出,我既在乎又轻描淡写的状态,似乎让他感到轻松。这可能就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最后,我故作轻松地问,“那匹白马,现在怎样了?”他说,“已经很老了,好在他还有一个健壮的儿子。”我说,“真羡慕你会骑马。”他说,“这没什么。”
我跟巴根那的关系刚缓和一些,又突然发生了变化。
晚上关灯不久,舍友们开始聊各种话题。也不知是谁把话题引到了一个与同学格格不入、爱打架的学生身上。毕力格图借题发挥,他说,“听说那家伙在单亲家庭长大,很早就没了额吉、他阿爸曾经捅伤过人。”巴图说,“上次他打架差点被开除,过来处理的就是他后来的额吉。”他们两人的话题引发了其他四人的兴趣。其他四人表现出对这个爱打架的学生一无所知的样子,询问各种问题。巴图和毕力格图一会儿说这个学生在经管系,一会儿又说在哲学系,令人一头雾水。后来巴图断定,这个学生在另一所大学。其实他们心里清楚在表达什么。我强压心中怒火,没有搭话。焦点娱乐注册
巴根那在下铺翻来覆去。我故意大声说,“好了,睡了睡了, 别吵了。”宿舍里顿时安静下来,但是我清楚地听到了毕力格图奇怪的笑声。我敢肯定,这个极其轻微的笑声,是他故意发出来的。他很得意。我翻身下床,走到毕力格图床边,揪住他的被子问,“你什么意思啊?”他说,“咋啦?还不允许人笑了?”巴图语气平和地说,“行了,大家睡觉吧。”
那天晚上,我一夜无眠,巴根那时不时在下铺发出微弱的叹气声。第二天,他没有跟我一起吃早饭和午饭。到了晚上,我在去食堂的路上遇到了他。我故作轻松地说,“走,一起吃去。”他说,“吃过了。”我说,“那你陪我吃吧。”他说,“不了。”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阿吉,我佩服你,你想干啥就干啥,你很有勇气,性格也直爽,但你不要拿我取笑,我也有自尊。”我问,“你啥意思啊?我什么时候取笑过你?”他怪笑着离开了。他看起来很沮丧,我也有些不痛快。我一直在照顾他的感受,他还要误解我。我差点骂他,但忍住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巴根那虽然一直住在我下铺,却很少跟我说话,更不会跟其他舍友说话。他越来越瘦,精神状态也很不好。他总是独来独往,在宿舍时, 除了睡觉以外,要么洗衣服,要么看书。他的枕边逐渐地垒起一摞名著。我一面怕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一面为了跟他缓和关系,便提出想借一本书。他问,“借哪一本?”我看到最上面的那本书封面上写着“复活”两个字。我说,“就那一本。”借过这本书后,我假模假样地翻了翻,随后扔在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我跟他说,“你说得对,外国名著还得看原著,这翻译的读着不舒服。”他只说是,然后没再说话。他可能也知道我这是在故意没话找话。不过这样总算打破了点僵局。焦点娱乐注册
我以为往下一切将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我想错了。就在那天晚上,天空阴沉沉的,却迟迟不下雨。潮湿、闷热、无风的天气让我感到烦躁。巴图说,“最近又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有个学生用菜刀砍伤了同学的半张脸。”毕力格图又开始分析人性,他说,“要我说,家庭不健全的话,孩子内心肯定会扭曲,容易变成怪物。”巴图认同地说,“就是。”他们的声音比往常更大。
我躺在床上看书,没有像先前那样阻止他们的谈话。毕力格图可能觉得无趣,突然转移话题,问巴图,你说,“一个在草原上长大的人不会骑马,会不会是个笑话?”巴图说,“何止是笑话,简直是耻辱。”两人哈哈大笑。
其实,我一直误认为自己表现出来的样子,让舍友及同学们对我有所忌惮。加上早在大一开学时,我曾经的劣迹莫名被添油加醋地传开,这让同学们都选择避开我。我索性选择了独来独往。我领略到了深沉的孤独感。焦点娱乐注册
我用阅读名著的方式过滤着巴图和毕力格图的谈话声,而巴根那不再翻来覆去,他只用一个姿势睡觉,无声无息,就像床位上多了一张床板。他的样子,以及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再次令我隐隐不安。他彻底不说话了。虽然我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我心里有某种对不起他的感觉。我说不上来这是什么。第二天,巴根那没有出现,晚上我在校园里碰到他同学问,知道巴根那在哪吗?他说,好像是请假回家了。我心想,等他回来,想办法让他住进大四宿舍,那里人少。不然,我的六个舍友总这么欺负他,我心里也不好受。
有一天,我手里拿着《复活》悄悄爬上了楼顶。那天下午,天猛然间晴了,晚霞发出橙红的光,驱走了连日来的阴霾,那热烈的光亮在天边好像奏响了一曲生命的交响。孤独背后,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一种绚烂的美。我开始迷恋这样的感觉,每天下午一下课,偷偷爬上楼顶看书。我渐渐地沉迷于阅读的快感,但我没有跟巴根那说起这事。
5
过了几天,天空再次变得阴沉沉的。巴根那请假后,好几天没再出现。一天傍晚,我来到了看铁轨的那座桥,无聊地四处张望。接着,我下桥往前走。即将改造的棚户区里布满蛛网般的胡同。一些人鬼鬼祟祟地走在胡同里。焦点娱乐注册
当我走过一扇铁门时,铁门“吱嘎”一声打开,从里面低头走出一个男人,男人后面是个打扮妖艳的女人。女人边关门边小声说,“帅哥,再来啊!”男人抬头的一瞬间,脸色一下刷白。他僵住了。是巴根那,他迈开双腿,机械性地跑了,很快消失在胡同尽头。
当天晚上巴根那没回宿舍。舍友们乐此不疲地谈论着那片棚户区。毕力格图拉长声音说,据说,“那里是打工人的天堂。”巴图说,“据说,那个地方让警察头疼,整顿了一次又一次。”我突然喊,“你们能闭嘴吗?哪来的那么多据说?”他们两人不再说话,其他四人也没再说话。
第二天,学校传来一则爆炸新闻,我们学校的一个男生,在桥下卧轨自杀了。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我只是没想到巴根那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假设我没在棚户区撞见他,看到他的不堪,他会不会就没事。或者说,从一开始,我是不是就不应该替他出头呢?我非常自责。我当着舍友们的面,从巴根那的黑色皮箱里找出了那个绿色笔记本,然后走出学校,来到了那座桥上。我没有去读笔记本,我知道上面写着什么。我把笔记本一页页地撕碎,扔在黑夜里的铁轨上。一列火车缓缓驶来,我听到了巴根那无望的低吟。焦点娱乐注册
巴根那的阿爸收拾完儿子遗物后,望着空荡荡的木床板发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眼里布满血丝,眼神充满绝望。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常常梦到巴根那夜里悄悄来到宿舍,用微弱的声音叹息。只有我能感应到他的到来。而他每次的到来,不会带来他灰暗的心事。梦里的他,并没有以人的形态出现,他变成了一种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的气息。他的气息萦绕在我梦里。也就是在这样的梦里,我看到了绿草、白马、河流、雪山。忽远忽近的梦境让我逐渐轻松。
我一时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六个舍友从教室和宿舍进出的脚步声既清脆又模糊。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学校的管理员老师终于发现我爬楼顶,找我谈话,警告我以后不许再爬上去,而且锁上了通往楼梯间的小铁门。我把更多时间花在图书馆,巴根那床头的那三本名著,成了我的陪伴。
有天夜里,突然下了一场暴雨。舍友们还没睡,却谁也没有谈论雨。暴雨过后,世界安静了,仿佛这场雨从来没有来过,舍友们也从来不曾谈论过雨似的。他们也不再谈论关于那个爱打架的学生的事,那个被他们造出来的、拥有两种性格特征的人。仿佛他们没有谈论过这个人似的。
我一夜无眠,白天也无心上课,只是呆呆地坐着,或走着。下午上完一天的课后,我走出了校园。焦点娱乐注册
我慢慢走到那座小桥上远望。桥下偶尔驶过长长的火车。棚户区已开始被改造,机器的嘈杂声里伴着砖墙倒塌的声音,一团团的白尘向上腾起。我的沉默里,酝酿着无可名状的悲伤。这时,从一片乌云后面,猛然间跳出夕阳来,灰暗的天空瞬间被阳光普照。天边出现了五彩的晚霞,晚霞照在冰冷的铁轨上,一列火车缓缓向着天边驶去。
在极远的晚霞里出现了绿草和白马,我听到了白马的歌声,很近,又很远。
阿尼苏,本名赵文,80后,蒙古族。现居内蒙古通辽市。作品见于《民族文学》《青年文学》《长江文艺》《福建文学》《莽原》《草原》《作品》等。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出版散文集《寻根草》,短篇小说集《西日嘎》。
焦点娱乐平台: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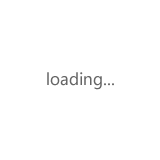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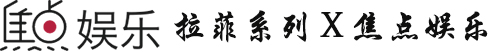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