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注册报道:
这张照片对我冲击极大:一个身穿白色氆氇藏装,脖子上套着木枷,头发凌乱,目光呆滞的中年人倒骑在牛背上。木枷里伸出的两只手,紧紧攥着拳头,下巴上依稀看到几根长长的胡须。旁边一名穿着黑色氆氇藏装的男人,背上驮着一个布袋,牵着牛绳踏步往前走。他俩周围没有任何的景物可以作为参照物,仿佛他们正行进在一片荒无人迹的旷野里一般。
这张照片是何时照的,里面的人又是谁,他因犯了何事被流放的,后来他又怎样了,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萦绕。
“这张照片里的人是谁?”我轻声问讲解员。
小姑娘脸上现出赧羞色来,嘴里吐出舌头,不再言语。我明了她并不知道这人是谁,但我对这名囚徒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我们从布达拉宫西侧的雪巴列空监狱出来,望着碧蓝的天空,长长地舒了口气。巍峨的布达拉宫在我背后矗立,仿佛它就是一本厚厚的历史书籍,深沉得令人呼吸困难。
从那天开始,我在打听这些流放囚徒的故事,在历史资料书籍中寻找关于他们的记录,过了半年多收获甚少。只知道,噶厦地方政府会把这些政治犯、重罪犯流放到遥远而闭塞的阿里、山南、塔工等地的边远地方,如果遇不到大赦,那他们在那个地方终其一生,很难有人活着逃回到拉萨来。也有一些人凭着坚韧的毅力和勇气,穿山越岭逃到印度,再到内地,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焦点登录
当我把那张流放囚徒的照片渐渐淡忘之时,突然接到在西藏社科院里工作的同学旺扎打来的电话,让我立马到小昭寺附近的一个小巷酒馆里,说是给我一个惊喜。
我很快赶到了那一带,没有费多少周折,便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找到那家很不起眼的青稞酒馆。我看到一张不规则的小木板上,躺着黑色油漆写就的歪歪扭扭的藏文“酒馆”两字。
油腻的门帘把里面的一切遮蔽住,不远处一个男人撅着屁股,在墙角边哗哗地撒尿,尿水沿着墙根像一条蛇一样蜿蜒匍匐。行人和自行车不以为然地从他身旁走过。他把裤子一提,拧紧皮带,拉上拉链,若无其事地走过来。他有一张衰老的脸庞,黑而无光,嘴唇塌陷,脑门上顶着一缕稀疏的灰白头发。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瘦。他伸手抢先把门帘撩开,一股酒精的酸味和香烟的气味混合着扑鼻而来,还能听到几声粗俗的话。
门帘再次落下,把我与里面的酒馆给割裂开。
我这才不太情愿地伸手把门帘的一角掀开,眼睛往里面搜寻,终于看到坐在柱子旁边的旺扎。他背对着我,穿了那身棕红色的皮夹克,那头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支在桌上的右手里夹着一根烟,烟头上漂浮淡白色的烟子。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才撒尿的那个老头。
我把右脚迈过门槛,酒气和烟子、汗臭味在我鼻孔里芬芳。临桌的几个人抬头瞅了瞅我,接着又开始他们的谈话。我坐在旺扎的旁边,屁股底下的木板凳硬邦邦的。焦点登录
“喏,这糟老头,这骚鬼名叫多吉次仁,他肚子里装了很多的故事。”旺扎脸都不侧一下,双眼直视着老头说。
多吉次仁咧嘴笑,牙龈上依然健在的那三四颗牙,孤零零地霸占着一方牙龈,他为刚才旺扎说的话显出兴奋来。一道道褶皱铺撒在他的脸颊上,如同久旱干裂的土地。
“年轻时我睡过的女人比天上的星星还多!”他把干瘦的右手伸过来握住酒杯说。由于门牙掉落的原因,他说话的声音不是很清晰。
“跟你睡过的跳蚤和虱子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更准确一些。”旺扎马上反驳他。
“臭屁孩子,你的灵魂还在游荡时,我已经在女人的肚皮上翻滚着。”多吉次仁一脸笑眯眯地进行反击。
“让我过来就是为了喝酒吗?”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喏,我给你找到了这个糟老头,他知道囚徒、流放、鞭打。”旺扎有些得意洋洋地说。
“闭嘴!我刚润了润舌头,喉咙里还干燥着呢,肚子里的火焰燃烧得旺旺的。”多吉次仁的脸一下垮下来说。
我看到他把一杯啤酒饮干,用手抹了一下那干瘪的嘴唇。我在酒馆里寻找老板,喝酒的几桌人外,并没有找到卖酒的。酒馆里烟雾弥漫,夸张的笑声在低矮的屋子里飞来飞去。焦点登录
我问旺扎酒馆的老板,他往身后的一张桌子努了努嘴。我冲那里喊:“老板——”
一个胖女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们这边走过来。
“要二十瓶啤酒!”我没等她凑近就说。
酒馆老板的右鼻翼上沾着一点灰色的鼻烟粉,厚厚的嘴唇,笔挺的双乳,很是炫目。她走向屋子的一角去取酒,硕大的臀部塞满了我的眼睛。
“你真是个好人!”多吉次仁隔着桌上剩下的五瓶啤酒对我说。
“先把肚子里的火浇灭,让话语的烟子从你舌头上冒出来吧。”旺扎求情似的跟他说。
多吉次仁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蠕虫般的沟壑游动了起来,孤独的牙齿阴森森地暴露在我眼前。
“好人,你打听那些事情干吗?”多吉次仁不解地问我。
老板娘把一箱百威啤酒和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说:“不能给这老头喝酒,他的孽根会缩进去的。呀呀——一句玩笑啊,这老头很可爱!200元。哈哈哈——”一阵咯咯的笑声从我们头顶滚过去,撞在了对面的墙上。
我掏出两张毛主席头像递过去,她接过钱后给了我一个很暧昧的眼神。
“这娘们风韵犹在!”多吉次仁试图伸手摸一下,但他没有够着。
“您讲讲那些流放的囚徒!”我有些迫不及待。
“哼,这有什么好听的,男女之间的事才是最有趣的。既然喝了你买的酒,不妨给你说一说。”焦点登录
我们共同端起酒杯碰一下,一口喝完。
“我们家是给雪巴列空支差的,之前我父亲押送噶雪巴到山南过。”多吉次仁说。
“就是雪监狱里的那张照片吧!”我不禁惊叫了起来。
“我有三十多年没有去过雪监狱,照片上的人有可能就是贵族噶雪巴和我父亲。”
没有门牙的原因,他说话依然吐字不清,我只能支棱起耳朵,仔细听他讲。
“西藏革命党{1},知道不?就是根顿群佩那伙人。绕嘎、江洛金、土登贡佩、根顿群佩,这些人你都听说过的。”他端起酒杯浇灭肚子里的火焰,放下杯子继续说:“孟勒家族的老爷也参与到了这个革命党里,听说他在印度为革命党做了很多的事。为了给革命党筹措经费,他回到拉萨准备变卖自己的领地和庄园。没想到这个节骨眼上,在印度的那些革命党人有的被抓,有的逃到了上海。孟勒老爷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终止了自己的行动。可是消息像风一样从印度传到了噶厦地方政府官员的耳朵里,他们惊得脸都成了猪肝色,盘腿坐在柔软的垫子上,喝着浓颜的酥油茶,吸着带劲的鼻烟,连连哈欠声中,决定迅疾逮捕孟勒老爷。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那天的天空蓝得让人只想躺着不动,我坐在雪巴列空监狱大门前的石阶上,闭眼进入到睡眠的状态中。阳光成了我的被子,墙壁成了我的枕头,石阶成了我的床铺,我的呼噜声把周围的麻雀都吓走了。有人重重地踢了我一脚,这一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看到两手剪在背后的托门老爷,他用极端厌恶的口气训斥道,‘看你这个穷光蛋,白天黑夜都分辨不清,像畜生一样只知道倒头睡觉。’我赶紧从石阶上爬起,站在一旁弯下腰,嘴里吐出舌头。被踢的部位还在隐隐作痛,谩骂的声音不断灌进我的耳朵里。这时从墙角钻出几个人来,他们押着一个穿黑色氆氇藏装的男人。托门老爷止住了骂,转身领着那三名跟班上了石阶,钻进雪巴列空的大门。被押解的这个人头发剪得比较短,嘴唇上有两撇胡须,双手被铁链铐着,在押解人员的推搡下进入大门。焦点登录
“下午,我才知道被押解过来的那个人就是孟勒老爷,他被关进最黑暗的牢房里,双手双脚被夹在了木枷子里。嘿,一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老爷,片刻间被投进了暗无天日的黑牢里。”多吉次仁有些洋洋自得地说。他握住杯子,把一杯酒饮干净。
其他几个桌子上的人也围了过来,他们肯定也特别想听后面的故事。
“没有过几天,托门老爷他们站在雪巴列空的院子中央,几个差役从牢房里押着孟勒老爷过来,将他的手脚捆绑在木桩上。达瓦叔叔手里攥着鞭子,嘴里吹着口哨,悠闲地走到他的身后。达瓦叔叔把孟勒老爷黑色氆氇藏装的下摆撩起来,塞进腰带里,再扯下那条脏兮兮的长裤,一个白白的圆润的屁股露在了朝阳下。达瓦叔叔逞能般地把皮鞭举在头顶摇动几圈,突然斜劈下来,发出一声脆亮的哒声。他讨好似的仰头望一眼托门老爷。托门老爷他们已经坐在了台阶上,面前的小矮桌上摆上了瓷器茶碗,一缕热气飘摇升腾。托门老爷用左手捋了一下光滑的下巴,右手捻动佛珠,耳朵上的玉坠在阳光下反射光。托门老爷拿腔拿调地说,‘给罪犯抽一百鞭。’达瓦叔叔手中的皮鞭像柔软的蛇一样,在半空中旋舞,又猛地击落在孟勒老爷的屁股上。我听到孟勒老爷凄厉的惨叫声和达瓦叔叔兴奋地唱歌般的数数声。抽到三十多鞭时,孟勒老爷已经昏厥了过去。那白花花的屁股和大腿,已是皮开肉绽,皮鞭上的血珠绽放在石板地上。最后昏迷中的孟勒老爷被差役抬进了牢房里。孟勒老爷被关了一个多月,这当中他的家人和亲戚试图打通上层的各种关节,想把他从监狱里捞出去。只因他牵涉的事件太大,谁都不想蹚这趟浑水,最后噶厦地方政府决定将孟勒老爷流放到山南隆子的迥巴堡寨。雪巴列空的几个管事老爷,通过在神像前的祈祷抽签,最终从十几个糌粑团里,抽出了写有我名字的那个糌粑团。这可能就是命吧!我成为了押送孟勒老爷到山南去的那名差役,那时我正好二十一岁。焦点登录
“现在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那时孟勒老爷被关在黑牢里,隔个十天八天就提审一次,每次用牛皮鞭再抽打屁股几十下,结痂的肉又绽裂开,传来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托门老爷他们端坐在垫子上,这才懒洋洋地开口提问。这样三番五次受刑后,孟勒老爷终于低头认罪,并在罪状纸上摁下了手印。托门老爷等不及把孟勒老爷投入到牢房里,急忙将认罪的纸折叠起来,装进袖口里,像只偷食的老鼠迅捷地顺着墙根往布达拉宫石阶跑去,他这是向噶厦地方官员邀功去。孟勒老爷定罪后,我们每天早晨都要架着他走出雪巴列空,再出雪城门,把他关进一个木笼子里示众。很多转经的人会围着木笼子絮叨,一些上年纪的老婆婆边祈祷边落眼泪,也有一些好心的人会从怀兜里掏出饼子、奶渣、干果等施舍给孟勒老爷。只是那些贵族,看到囚禁在木笼子里的他,便远远地绕道而行,深怕一旦挨近就会遭受灭顶之灾一样。这孟勒老爷也真有骨气,别人施舍的食物一口都不吃,口渴难忍也不会讨要一滴水,一天都眯着眼,跟谁都不搭腔。太阳落山前,我们又去押解他回雪巴列空。到了木笼子前,我们会跪在地上捡那些施舍的食物,把它们装进自己的怀兜里,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和满足。等我们像只狗一样匍匐木笼子绕一圈后,孟勒老爷这才会睁开眼睛。我们从地上站起来,打开木笼子的锁,把他从里面拖出来。回去的路上我看到他的头发里养满了虱子,领口上有跳蚤。想着这人真不会享福,为什么要去当个革命党,让自己落到这样一个悲惨的境地。可是手摸到兜里的那些食物时,也就不再替他想什么了。”焦点登录
多吉次仁停顿一下,又举起了杯子。酒馆里的所有人响应着端起了杯子,酒顺着我们的喉咙倾泻到肚子里。桌子上有人默不作声地递香烟,烟雾如幽灵般飘浮在我们的头顶。焦点登录
“那时候的生活可真苦!”多吉次仁说完吧嗒了一下嘴,接着看到所有人的目光聚在自己脸上时,挺直腰板,接续上面的故事:“初夏的清晨,布达拉宫雪城前面的那片湿地已经返青,水坑上面的薄冰也已融消,柳树枝丫上长满了新芽,这天我被召到了托门老爷办公的房间。草香的烟雾在屋子里缭绕,吸鼻烟的咝咝声从窗户旁传过来,从烟雾的缝隙我若隐若现地看到托门老爷那张饼子似的圆脸和肉球般的鼻子。不待我靠近,托门老爷说,‘佛下了谕旨,要你明天押解嘎玛维松(孟勒老爷名)到山南乃东去,交接完就赶紧滚回来。’我唯唯诺诺地应承,然后退了下来。我回到家跟父亲一说,他盯着我的脚看了许久,这才无奈地告诉我说,脚上的这双破鞋根本走不到乃东,要我把他的皮箱子给打开,拿出他舍不得穿的那双长靴来。他还给我讲这一路所要经过的地方和注意事项,甚至中午在哪里休息,晚上借宿谁家都讲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我背上父亲的布袋子,里面装有糌粑、木碗、茶叶、盐巴,还有一小块羊腿肉,赶到了雪巴列空大门口。那该死的靴子里我的脚在晃荡,走起路来吧唧吧唧地响。哦,对了,我们该干一杯!”多吉次仁说得口渴了,怂恿我们把杯子里的酒喝完。焦点登录
“他娘的,这时间怎么一晃就过了。可惜了,可惜了!”有人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只要下次你买酒,我重新给你讲。”多吉次仁冲那人的背影喊。
“糟老头,你继续讲故事啊。”旺扎有些微醉,两只眼睛开始泛红。
“阳光从东边的篷布日山上跃出来,黄金般的光镀在布达拉宫的金顶、墙壁上。有两个差役在打扫院子,我去找达瓦叔叔,向他要了一些羊毛,把它们塞进靴子里,要不我的脚继续在靴子里晃荡,不断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来。达瓦叔叔给了我几块奶渣,说路上可以解渴。我跟他借那把长长的腰刀,说路上用来防野生动物。达瓦叔叔给我摊开手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把刀是宝刀,需要留抵押金。’‘呸,什么宝刀啊,我身上只有跳蚤能给你。’达瓦叔叔揪住我的耳朵,把我从房门里推了出去。托门老爷他们开始下马,拾阶去楼上的办公室。带着黄色朵帽的饶杰看到我,要我把那头黄毛的牛牵过来。等我把牛从牛圈牵到院子中央时,其他几个差役也从牢房里把孟勒老爷给架了出来。孟勒老爷身上穿件白氆氇的囚衣,头发上还粘着草屑。焦点登录
“二楼东窗前站着托门老爷他们,几个人的脑袋挤挤地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阳光像贴了金一样让他们的脸变得生动起来。饶杰脱帽弯腰望向那扇窗户,托门老爷把右手一甩,命令我们可以走人了。饶杰伸长脖子喊,‘让罪犯骑到牛背上去。’差役们抬着孟勒老爷放置在牛背上,牛被压得四蹄在石板地上转动,身子也随着摇动。孟勒老爷屁股上的伤口磕得让他嗷嗷直叫。饶杰再一次喊,‘嘎玛维松正式被流放!’我抬头望向东窗,托门老爷他们已经背对着窗户,只能看到黄绸缎的背面。我牵着牛走出雪巴列空的大门,饶杰、达瓦叔叔和几个差役站在门口目送我进入到巷子里。
“我们走在幽深的巷子里,路边玩耍的几个小孩,捡起石块掷到孟勒老爷的身上,发出噗噗的声响,几只流浪狗也向我们狂吠。我可不想制止他们。我们走出了雪城门,湿地的气味一下扑鼻而来。黄牛慢腾腾地绕一圈布达拉宫,行人看到我们后站在原地窃窃私语,也有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来。我们转到去往八廓街的道路上,前面一览无余,在东南方向玉拓桥拱顶上的琉璃瓦熠熠发辉。‘我屁股疼得受不了。’孟勒老爷第一次开口跟我说话。‘还没有到八廓街示众,您得忍一忍。’我这样说。孟勒老爷开始低声哀嚎起来,真是烦死人了。我在脑子里回想昨晚媳妇那绸缎般的身体,禁不住愉快地吹起了口哨,把他的哀嚎声给压制住。阳光快要跃到头顶上之时,我们走过了玉拓桥,大昭寺就在前方。我安慰孟勒老爷说,‘我们马上进入八廓街,离您家很近了,说不准您家人在路边拿着茶和点心等着您呢!’孟勒老爷没有搭理我,但我心里预设他的家人在前方一定等着我们,还给我们送丰盛的食物一路享用。出乎我预料的是,八廓街里的人围着我们俩,仿佛我们是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一样,用手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地交谈着。还有人站在屋顶,两手插在袖子里目送我们走过。一个尼泊尔商人跑出来,挡住我的去路,往我衣兜里塞了一块东西,走到孟勒老爷跟前轻声安慰了几句。我预期的孟勒老爷家人没有出现,倒是无数个陌生人尾随其后,陪我们走出了八廓街。这些人一脸的兴奋,有些还伸手摸孟勒老爷脚上的镣铐,发出啧啧的声响。行进到鲁固时尾随的人员渐渐少了,我们走在坑洼不平的土石路上,颠簸使得孟勒老爷上牙紧紧咬住下唇。这可怪不到我,这条路平日里就这样凹凸不平。焦点登录
“我们顺着拉萨河前行,河水瘦弱得像是个快要干枯的尿迹,河床里的鹅卵石被烤得蜷缩着。四周没有一个人,我这才说,‘孟勒老爷,要不您躺在牛背上。’孟勒老爷带着哭腔说,‘就这样吧,谢谢您!’我平生第一次被这些贵族老爷称为了您,心里自然窃喜。在我的帮助下他匍匐在了牛背上,屁股下的白氆氇被血浸染成暗红色。布达拉宫在我的右侧向后慢慢移动,我们快走到渡口了。这时两个壮硕的男人跑了过来,接着又是几个男女往这边冲过来。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咬牙切齿地恨起了达瓦叔叔,他们要是劫人那我可没有一点还手之力,我的腰间只佩带了一把短刀。好在他们远远喊着孟勒老爷的名字,显得非常地激动又伤心。他们不管不顾地从牛背上抬下孟勒老爷,一直走到了渡口。那里的石头上铺了两张精致的卡垫,旁边有一罐陶壶,稍远处停了四匹马。等孟勒老爷趴在卡垫上后,这些人才注意到牵着黄牛的我。‘差役大人,我们是孟勒老爷府上的,还有夫人和少爷千金。您过去喝杯茶,容我们跟老爷告别一下。’我点头答应了。他们在稍远处给我搭了个小垫子,倒上了浓茶,端来饼子和糌粑油糕,我的眼睛都鼓凸了出来。过会,孟勒夫人过来跟我要尼泊尔商人塞给我的东西。我想说这是给我的,可是听她说这是治疗伤口的药时,我没再坚持自己的想法,有些不舍地递了过去。我们耽误了几炷香的工夫,期间我知道了他们在八廓街里的房子被充公,两处庄园也被没收,甚至下令他的后代永世不能进入噶厦地方政府里任职,孟勒家现在只剩下墨竹工卡的庄园了。孟勒老爷与他们依依惜别,他们送给我们两个牛皮褡裢的食物和几件孟勒老爷换洗的衣服。我们坐上牛皮船渡河到了对岸。河那边的人这才骑上马往拉萨方向走去。焦点登录
“那天我们就支差住在了然马岗的一个农户家里。我看在孟勒家给的丰盛食物的份上,脱下孟勒老爷的裤子,在他那张烂屁股上涂抹尼泊尔人给的药。晚上,我们并排睡在农户的屋檐下,满天的星星绕着一枚上炫月。‘孟勒老爷,西藏革命党是干什么的?’我好奇地问。‘是不满噶厦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反对他们的专制统治,想进行革命的一些人。’趴着睡觉的孟勒老爷说。‘哦!’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听懂,接着我又说,‘这一次您连房子、庄园都没有了,要是不能得到特赦,连老婆和小孩都不是您的了。’孟勒老爷听到这句话后嘤嘤地啜泣。我想革命到头来革到您自家头上了。那夜我睡得很踏实。第二天是被鸡鸣声给吵醒的。一旁的孟勒老爷像一只藏獒脑袋埋在臂弯里睡觉。我们再来一杯吧!”多吉次仁又劝酒。我们马上迎合。焦点登录
“那头牛走得特别慢,到贡嘎宗(县)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黄昏时我们到了宗府,宗本(县长)头发梳得油亮亮,是个人高马大,声音洪亮之人,他看完噶厦的文件后让一个仆人安排我住进一间耳房里,其他几个仆人抬着孟勒老爷去了楼上的房间。我想可能是太晚的缘故吧,抵达的那一百鞭明早会落在孟勒老爷的屁股上。我迷迷糊糊之际,有人敲门说是宗本要开镣铐的钥匙。我问,‘现在要抽那一百鞭?’那人说,‘很有可能。’我从脖子上取下那两串钥匙递了过去。我说,‘能否求个情,打得轻一点。他的屁股上都快要生蛆了。’那人点点头,吱嘎一声带上门走人了。我躺在柔软的草甸上,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等着听他的哀嚎声。外面静悄悄的,偶尔有几声狗吠声和马厩里马的响鼻声。我的眼皮不听使唤地掉落了下来。焦点登录
“太阳从木格子的小窗户里射进来,照在脸上把我给弄醒了。我匆忙起来,还得赶紧出发呢。我出门看到院子里有背水回来的,蹲坐在墙角捻线的,挥动斧头劈柴的。一个管家模样的男人从宗府的门里走出来,告诉我说,‘犯人昨晚挨了一百鞭后昏死过去了,宗本要等他苏醒过来你们再出发。’我心一下抽紧,想着千万别让他给死了,这样对他来说太冤枉了。管家还告诉我说茶和酒会让下人送到我的房子里,让我安心休息一天。确实,像他说的那样,不一会儿,一个女人给我端来了一壶茶和糌粑,我也无聊地跟这个女人说了一些俏皮话,惹得她咯咯地笑,对我并不反感。等她走后,我心一下安静了,也有了一些盼头。吃饱喝足后,我从牛皮褡裢里拿出干肉和发酵糌粑糕装进怀兜里,手上提着茶壶和糌粑袋去了厨房。我再次见到了她,这是个身材高挑,面色苍黄的中年女人,那双眼睛活泛得让我难以自制。我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赖在厨房里跟她闲聊,趁其他人不在的片刻,把干肉和发酵糌粑糕塞到她的手里,然后夺门而逃。我现在没有时间管孟勒老爷了,我只去看了一下那头黄毛牛。大把大把的时间我就在贡嘎宗里瞎溜达。下午她又给我送来了一壶青稞酒,我请她在我的木碗里饮一杯,她欣然接受并喝完了。三宝啊,这可是个尤物!我喝完一壶,又去讨要了一壶。夕阳没有落山前我醉倒在那张草甸上。深夜,有人闯进我的房子里,把我抱进了温暖的怀抱里,我闻到了牛粪的气味和头发上的酥油味,我知道这是那最美妙的时刻。再次醒来时,那缕阳光又射在我的脸上,身边没有人,我慵懒地翻转身子,祈祷孟勒老爷今天也不要醒过来!可是,有人从门外催促我,要我赶紧吃饭后走人。我心里的那个失落啊,没法用语言来表达。趴在牛背上的是孟勒老爷和那两个褡裢,白色氆氇囚服上的血迹不见了,我又得牵着牛绳出发。临走我环顾四周,没有见到她,宗本和管家站在石阶上目送我们。我心凉凉地转身,出了贡嘎宗。”焦点登录
“这骚棍就是不正经。来给老头的年轻时代敬一杯!”旺扎提议。焦点登录
会心的笑容在酒馆里震荡,空气里飘扬着酒精的味道,麦芽的芳香从喉管里跌落下去。
“我后面才知道,贡嘎宗本跟孟勒老爷是沾亲带故的,所以他徇私枉法没有抽抵达的那一百鞭和临走时的一百鞭。这样也好,一路上我就会省心不少。听我父亲说,很多重犯在流放途中每到一个宗(县)就要挨抵达后的一百鞭,离开时又要抽一百鞭,再到下一个宗又得挨抵达和离开鞭,直到到了流放地接受最后那一百鞭才算结束。有些人经过这样的折磨就没能熬过来,有些半年多都在流放地匍匐着干活,最终挺过来,也有的却终生落下了残疾。我们在去扎囊宗的路上,有次中午坐在雅鲁藏布江畔,熬茶吃午饭,孟勒老爷像只狗一样窝在火堆旁,要求我把他的裤子给褪掉,让屁股暴晒在阳光下。我照做了,看到伤口上结的痂,便想起达瓦叔叔抽打鞭子时的情景。‘孟勒老爷,要是我有您的家产和地位,决不会去参加什么革命党。’我说。‘那是我的信仰,我不能容忍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孟勒老爷说。‘那是你们有权有钱人玩的,跟我们这些穷苦人没有关系。’我又说。‘跟你说也是白费,你们只有受苦的命。’孟勒老爷不屑地说。‘老爷,虽然我们半饥半饱地过活,但不至于会走到向您这样家破子散。’我的这句话好像戳到了他的痛处,他半晌没有再吱声。他的头发被洗过,领口处也找不到跳蚤。我把自己的藏装上半截脱下,赤裸着上身在里面找跳蚤和虱子。燃烧的荆棘噼啪着,在铝壶下伸出一个个火舌来。‘帮我在屁股伤口上涂个药。’孟勒老爷说。我把刚抓到的一个圆鼓鼓跳蚤用两个拇指指甲挤爆,这才起身到褡裢边去取药。‘这药快没了。’我说着心里很高兴,没了我就不用往这个屁股上涂药。‘剩下的全涂上吧。’我照他的话要全部涂上去。‘如果我待在印度,那可能逃到内地了,也就不用受到这般酷刑。’孟勒老爷说。‘你们革命党里被抓的就你一个人吗?’我问。‘以西藏革命党罪名被抓的就我一个。’他不甘地说。我的手可能太重了,孟勒老爷突然怒吼道,‘轻一点,你这个可恶的穷鬼。’我的手害怕地缩了回来,双膝跪在地上。片刻的寂静之后,我想到自己是差役,他可是个罪犯,我不可以这样惯着他。我把装药的盒子给扔掉,起身坐在茶壶边,继续往火里添荆棘。不一会,茶烧开了,香气扑鼻而来。我自顾自地喝茶吃糌粑和羊肉。孟勒老爷识趣地自己提上裤子,匍匐着从牛皮褡裢里取食物吃。我看他这副样子先前的怜悯一下就没有了。焦点登录
“到了扎囊宗也是因为孟勒老爷家族的运作,只是象征性地在他囚服上抽了几根鞭子,然后草草地了事。我们补充了一些粮食,继续往乃东宗走去。我已经对这些人失去了好感,他们所做的这些小动作让我这个一字不识的人都感到了恶心。我在牛背上驮着他,一路上都不再跟他说话。到了吃饭的时间,简单地吃个饭,晚上我也会睡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快到乃东宗的那个晚上,我扔下他跑去酒馆喝酒。酒馆老板娘是个标志的美人,我们喝着紫青稞酿造的酒,说着调情的话,喝了一罐又一罐。女人用歌声调节气氛,我用身上不多的藏币换酒,到头来我找不到那家农房,倒在路边熟睡了过去。是一阵麻雀的叫声把我给吵醒了,我昏头昏脑地坐起来,看到脚上的一只靴子丢在一旁。这才回过神来,赶紧穿上靴子,去找借宿的那家房子。那家人熬好了清茶,在等着我的到来。我喝上几杯茶后,把孟勒老爷抱到了牛背上,再把开始干瘪的褡裢放上去。我们从牛粪羊粪落满的巷子里穿过,走到了稍微平整的官路上。我在想到了乃东宗,我的使命就结束了,我可以牵着这头黄毛牛赶到贡嘎宗去,在那里可以多待几日。我们顺着清澈的雅鲁藏布江向东行进,走过了几个庄园和许多个村庄,太阳落山前终于到了乃东宗府。焦点登录
“我把文件和犯人交接完毕后,到他们安排的一间低矮、昏暗的房间里去休息。也许这天赶路太急,空着肚子便倒头睡着了。一觉醒来,我赖在干草铺满的地上,想着第一次的远行竟然这样的顺利,心里的感激之情用祈祷文敬献给了白度母。我想回去以后,雪把列空里的差役们也会对我另眼相看的。我简单地收拾完,就去找宗本告辞。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宗本以手下没有人为借口,要我把孟勒老爷送到迥巴堡寨去。我以不知道路线为借口坚决不去,宗本无奈之下答应派一名老者带我过去。我们又翻山越岭,蠕虫般缓慢地前行,山顶的积雪在阳光下钻石般地闪耀,旷野里的风针尖一样刺得人骨头里面都疼,脚下的草还没有返青,一片金黄色。我们跑到一处草皮垒砌的简陋小房前,向里面的牧人讨要一口热茶喝。牧人看到流放的孟勒老爷,没有显出惊讶来,他还告诉我们曾经有个流放犯人就在这个山上被冻死了。他见过很多从这里经过的流放人员,既有僧人也有普通人和贵族,末了叹口气说,‘人生就是命中注定,只能认了!’我们听完他的唠叨后继续赶路。天空飘起了雪花,风更加地刺骨寒冷,我在前面拉黄毛牛,叫尼玛次仁的老者从后面推,历经一天时间我们才走过了这片绵延的山脊。下到谷地里,一下暖和了起来。山脚下的农田里禾苗露出了头,一片青绿绿的,尼玛次仁在这里有亲戚,我们就去投靠了他们。到隆子宗时也是象征性地抽了几下抵达鞭,然后让我们赶到一个叫加玉(鸟乡)的地方。这么多天不间断地行走,让人又困又累,孟勒老爷的话变得更少了,他趴在牛背上眼神里充满绝望。我也不再理会他,一路上听尼玛次仁讲这里的神话传说。焦点登录
“几天之后,我们把牛寄存在夜宿的那个家里,轮流背着孟勒老爷去加玉。这里根本就没有路,越往里走树木越多起来,只能在巨石岩壁中穿行。咆哮的河水一路陪伴,水分子时时飘落到脸颊上。抵达加玉时,尼玛次仁告诉我说迎面的这些山就是喜马拉雅的山系,它们绵延不绝。山顶全是厚厚的积雪,雪线以下是草甸,山脚各种灌木丛林,丛林边是一片片畦田,牦牛和山羊落满半山腰上。这里可真是个漂亮的地方,但急于要把孟勒老爷送到迥巴,我都没有心情欣赏这片美景。”多吉次仁停顿住。焦点登录
我看到桌上的啤酒差不多快喝完了,又扭头跟老板娘要了一箱。旺扎起身摇晃着去撒尿,我跟多吉次仁干了一杯。我脑袋里翻腾着他讲述的故事里的画面,感觉脑袋有些轻飘飘。焦点登录
“尼玛次仁以年龄太大为由,让加玉村里派一名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帮我去迥巴。出发的早晨来了个矮胖敦实的年轻人,他身上背了个柳筐,要把孟勒老爷装在筐子里。这样确实方便了很多,但道路越发地险峻,人就在峭壁悬崖上行走,下面是乱石岗和湍急的江水。一旦坠下去,也就必死无疑。走到太阳当头时,一座陡峭的山坡挡住了去路,年轻人找来独木梯支在山下,背着孟勒老爷艰难地攀爬上去,我在后面心惊胆战地跟随,全身都不住地发起抖来。接着又走一条狭窄的栈道,下面江水翻腾白浪,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望一眼脚下,万丈深渊,双腿打颤,害怕地把裤子都给尿湿了。走过栈道我瘫倒在地。这下我从内心里感激尼玛次仁给我派了这个年轻人,要不我早已坠落身亡了。很久,我才缓过来,又跟着年轻人走进喜马拉雅腹地的深山老林中。这一路除了碰到动物外,根本看不到一个人。晚上我们躲进一个山洞里。第二天走到一座叫普巴山崖(木橛子山)的面前,年轻人又找来一个长长的独木梯向上爬行,他粗重的喘气声从我头顶传过来,爬一级要休息片刻,耽误好久后我们才爬到了最顶上。又顺着山崖往沟壑里走了许久,最终看到了那两层的碉楼。我们的劲头一下提了上来,轮流背着柳筐。孟勒老爷却泄气了,一脸的茫然与绝望。我们走到那座碉楼前,把柳筐刚放下来,有个脖子上长有肉瘤的男人走出来,让我们把孟勒老爷丢在碉楼前的空旷地上。我们进碉楼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我拽着年轻人头也不回地赶回去,生怕又有什么变故。我好像听到背后传来的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声,但我没有回头看。我们下到山下,就把所有的木梯撤下来,防止这些犯人逃跑。”焦点登录
“给老头敬一杯!”旺扎提议。
我们再次举起杯子,将酒灌进嘴里。
“到了那里逃不出去吗?”有人从一旁的桌子边问。
“我得去撒泡尿!”多吉次仁踉跄着往门口走去。
“到了那里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冰天雪岭,东边又有强悍的珞巴人挡着,迥巴村寨的人又时刻盯防他们,没法逃出去的!”我这样跟人解释。
多吉次仁晃晃悠悠地坐到了凳子上,裤子的拉链没有拉上,红色的秋裤醒目地露出来。
旺扎端着酒杯问:“后来这孟勒老爷怎么样了?”
“臭屁孩,懂个球。西藏解放后人家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他得感谢你这个糟老头!”
“呵呵呵——人家见了面都装作不认识呢。”
我的心情一下滑落到了低谷,这可能是酒精起的作用吧,我再也不想打探这些囚徒的事了。焦点登录

次仁罗布,西藏拉萨市人,1981年考入西藏大学藏文系,获藏文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文学》主编。西藏自治区学术带头人,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曾获西藏第五届珠穆朗玛文学奖金奖、第五届西藏新世纪文学奖、首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年度大奖(2009)排行榜奖、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法语、西班牙等多种文字。
焦点娱乐平台: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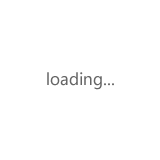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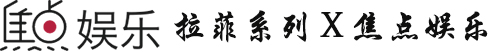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