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注册报道:
冰箱又闹鬼了。
外婆家在顶楼六〇三室。客厅、卧室、卫生间、厨房间,还有一台身坯巨大的双门冰箱,等于第五个房间。起先像个老爷叔自说自话,然后油锅炒菜,油烟机开到最高档。黄酒混了白酒味道。蔬菜在牙齿间咀嚼。红烧牛肉在舌头尖颤抖。老鸭汤在胃囊里翻滚。轧姘头的男女在台面下脚趾头摩擦。所有喧哗与骚动都来自这台冰箱,并与压缩机的重启无关。
清明节的黎明。客厅沙发床上,我同时忍受饥饿与晨勃。我捂了耳朵爬起来。厨房间刷了一层浆白色的光。“海宝”冰箱贴落在了地板上。再等二十几天就是二〇一〇上海世博会。我捡起“海宝”吸上冰箱门,好像按了暂停键。厨房间重新安静得像太平间。我拉开冰箱门。没有老爷叔,没有偷情的男人跟女人,只有昨夜吃剩的两盆菜、七八包蔬菜、几十只鸡蛋、两盒牛奶、两盒酸奶、几瓶调料、一袋切片面包,还有两瓶可乐。冷冻室里有哺乳动物和禽类的碎尸、速冻汤团、水饺、鱼丸、蟹肉棒。外婆活着的唯一乐趣就是塞满这台冰箱,仿佛可以救活整个非洲的难民。前两年汶川地震刚过,外婆在永乐电器买了这台冰箱。妈妈劝外婆一个人不需要这样大的冰箱。外婆说,因为你没挨过饿。别的老太去庙里烧香拜佛,去教堂做弥撒拜耶稣,而我外婆的信仰是这台冰箱,等于她的耶路撒冷,她的大雷音寺。想到耶路撒冷和大雷音寺,我一点点柔软下来。焦点平台
平常这个钟点,外婆已经悄咪咪起来刷牙齿揩面,牵丝攀藤地篦头发,像个唐朝的白头宫女。现在外婆依旧困了眠床,双目微闭,神态安详。我在外婆耳边大声叫唤。六楼到一楼都被我吵醒了。外婆还是困死懵懂。我摸了外婆的鼻孔,尚存栀子花气味的呼吸。我打了120,腔调冷静得像我爸爸。但我一放落电话,眼泪水就滚出来。我怕外婆醒不过来了,就像五年前的外公也在这张床上过世。
我从床头柜寻着一把牛角梳。我把外婆拖出被头筒,稍微帮她篦了篦头发。外婆骨瘦如柴,现在基本没了分量。我时常梦见外婆牵了我走在荒原上,土地龟裂,寸草不生,到处是牲畜尸体,饱食腐尸的鼠类横行,一阵狂风撕碎外婆的皮肉毛发,露出森严的白骨骷髅。
急救医生敲了房门。我送外婆上了救命车。楼下蛮多老头老太看闹忙。救命车顶灯旋转“乌鸦乌鸦”了开走。再爬六层楼回到外婆家里,我只想倒一杯牛奶,加两片面包填充肚皮。我打开冰箱门,两盒牛奶只剩一盒。两盆隔夜菜消失了。还少了一包鸡毛菜,一包蓬蒿菜。我的记忆没有紊乱。刚刚几分钟的空档,有人闯进厨房间,打开冰箱偷了菜?隔壁邻居平均年龄八十岁,应该没人玩开心农场偷菜。冰箱还是闹了鬼。焦点平台
我拆开剩下的一盒牛奶,靠在冰箱门上吞入喉咙。客厅墙上挂了外公遗像。外婆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外公的鬼魂就游荡在这幢房子里。有一趟外婆半夜起来小便,看到冰箱门无声敞开,烟雾腾腾的冷气跟白光一道流出来,外公弯腰驼背坐在冰箱里,全身被厚厚的白霜包裹,眉毛胡子都是白的。我听了笑出来说,这不是圣诞老人吗?外婆伸手进了冰箱,摸了摸外公青紫色的嘴唇皮,外公睁开眼乌珠说,肚皮饿。外婆急忙挖出隔夜冷饭,打开油锅烧好蛋炒饭,冰箱里的外公已经消失。
下半天放学,我去了医院。外婆醒过来了,但是不能讲话,眼泪汪汪看了我,这段辰光都要住医院。舅舅过来照料外婆。我有一台诺基亚手机,妈妈出国前送给我的。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在一万公里外的巴塞罗那。她是西班牙语翻译,陪了中国代表团参观诺坎普球场。妈妈帮我搞到了梅西的签名球衣。她以为我会开心地尖叫。我只说,蛮好。妈妈的回国机票是四月三十日,为了赶上世博会开幕式。今朝是清明,妈妈关照我烧点纸给外公。
回到外婆家门口,我看到爷爷坐在台阶上,拎了一条鲈鱼、一包牛肉、一袋大虾、一盒豆腐干,嘴巴里叼了香烟等我。妈妈给爷爷打了电话,保证我不会饿死。爷爷进了厨房间,慢悠悠汏好手,推开冰箱取出几样绿叶菜、葱姜蒜、各种调味料。爷爷提起剪刀杀鱼。我只负责淘米按下电饭锅开关。我在旁边盯了鱼眼睛,好像它要记牢我的样貌,只等下地狱复仇。我的馋吐水流出来了。爷爷弄清爽鱼,准备好肉,刷了油锅,开了煤气灶,火苗跳得像庙里香火。焦点平台
爷爷是扬州人,退休前是国际饭店中餐厅的大厨,精通淮扬跟本帮菜。爷爷一生引以为豪的有两桩事:一是娶过两房太太,二是给西哈努克亲王跟莫尼克王妃炒过菜。我从小听爷爷的口头禅“今朝让你享受西哈努克亲王待遇”。今夜,我跟爷爷吃光了一条清蒸鲈鱼,八只爆炒大虾吃了四只,大煮干丝跟西湖牛肉羹还留一半。冰箱里塞了四只保鲜盒:吃剩的三道菜,还有一盒白米饭,是我明朝带去学校的中饭。
爷爷立在阳台上吃了一根香烟就走。我问爷爷要了一只打火机。爷爷家在老西门,文庙背后的梦花街。爷爷一家门六口人,还有二奶奶就是我爸爸的后娘,叔叔婶婶跟双胞胎堂妹,挤了石库门的楼上。爷爷出门同时带走了垃圾。我的影子在地板上拖了蛮长,好像长高了十公分。我打开外婆房间,不但有栀子花气味,还有食物腐烂腔调。我在床头柜寻着一袋锡箔。外公埋在宁波老家的山上,本来每年都要去扫墓,今年外婆身体不好没去,但是自己包了锡箔。我寻到一只铅桶,打开厨房间窗门,搁在外面铁格子上。打火机像爷爷的油锅,点了银元宝形状的锡箔,眨眼烧成一团焦黄。我的脑子里烧起两团火。一团火可以填饱你的肚皮,另一团火也可以填饱肚皮,不过是在阴间。焦点平台
清明夜里,终于滴滴答答落雨了。对面六楼照旧弹起琵琶。每到夜里八点,隔了一条窄窄的马路,对面阳台上有个姑娘开始弹琵琶,每趟反反复复《十面埋伏》。她跟我一样也是初中生。我给她起了名字“琵琶小姐”。她坐了阳台的折叠椅上,穿了白毛衣,蓝颜色运动裤,怀抱一张琵琶,十根手指头眼花缭乱,好像给霸王跟虞姬招魂。琵琶小姐倏尔抬头,望见对面六楼窗门,灰黄花朵般的灰烬飞向夜空。燃烧锡箔的火光点亮我的面孔,顺便拖出两道眼泪鼻涕。我的背影在银灰色冰箱门上跳舞,像古代的屏风。
隔天早上,冰箱又闹了鬼。四只保鲜盒还在,但是爷爷烧的三道菜——四只爆炒大虾、半份大煮干丝、半份西湖牛肉羹还有白米饭统统没了,只有四只空盒子,洗得清清爽爽,闻得到洗洁精味道。这是一台饥饿的冰箱。但它不是贼——冷藏室里多了五百块人民币。我的手指头慢慢伸进去,触摸五张冰冷的粉红色钞票,鼻头前闻了闻。钞票稍微有点旧,捻起来有点软,不是刮啦松脆,但没污渍,也没缺角。一张张钞票在台子上摊开来,对准窗口的光照一照。老人头水印是真的。焦点平台
放学路上,我去了肯德基。点好鸡腿堡套餐加上新奥尔良烤翅,我从书包里掏出一百块,心里却是兵荒马乱,万一验钞机嘟嘟乱叫,我被送去派出所哪能办?要是讲冰箱闹鬼吐出人民币,我就要被送去宛平南路六百号。钞票“唰”一声滚过验钞机,稳稳进了收银抽屉,我心里的冰箱门才轻轻关上。
肯德基吃饱等于夜饭。我翻过苏州河的三官堂桥。曹家渡花市像个堡垒立在桥头。咸蛋黄似的夕阳落下来。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这座桥上认得的。那年爸爸刚到美术学院做老师,长头发像两片乌鸦的翅膀,他坐在桥栏杆后头,架好一张画板写生。妈妈陪外婆出门买菜路过,定怏怏立在桥上看他画画。妈妈让外婆先去河浜对面菜市场。等到外婆拎了一篮头菜还有两斤带鱼回到桥上,妈妈已经靠在爸爸身边,两个人一道看落日沉入苏州河的波光。十二个月后,世界上多了一个我。三个月前,爸爸和妈妈领了离婚证。我们住的房子还给了高校。爸爸跟他的女学生去了北京。爸爸让我放暑假去北京过十四岁生日。妈妈丢给我一句话,敢去就打断你的脚骨。
回到外婆家里,天已墨擦乌黑,我打开冰箱一看,又多了五百块人民币,还有一张冻僵了的小纸条:“冰箱君:急需阿司匹林一瓶,购药款已附上,谢谢。冰箱老人。”焦点平台
蓝颜色钢笔字写得毕工毕整,好像印刷上去的,手指头却能摸出一层墨水。摊开五百块钞票,有点旧,有点软,但是如假包换的人民币。我看懂了,冰箱君就是我,冰箱老人是啥人?我只能想象冰箱门无声打开,冰箱老人披了白霜钻出来,四肢修长,背脊笔挺,像一支坚硬的钢笔。他从冰箱里取出四个保鲜盒,依次塞进微波炉加热。冰箱老人坐在我的对面,三道菜摆上台子,低眉顺眼举起筷子,抖豁夹了大虾塞进嘴巴。他又举起瓷调羹,盛起西湖牛肉羹,慢慢吹气吞入喉咙。他的面孔和头发一样雪白,点了老人斑,皱纹像苏州河水波荡漾。我从没见过这张面孔。外公生前是个弯腰驼背的老病鬼,慢性肝硬化导致面色黑紫。外婆常在厨房间熬中药,那种味道一直潜伏在我的噩梦里。
我没能在房间里找到阿司匹林。但我见过外婆吃这种药,阿司匹林几乎是万能的,可以医治各种血栓特别是中风。我连夜去了一趟医院。住院楼的六人病房里,外婆见着我就气色好转,紧紧拉了我的手,讲起刚做过的梦。外婆在梦里回到五十年前,她还是十七八岁小姑娘,住在番瓜弄棚户区,碰着大饥荒,连续四十天,每日一碗粥,几粒咸菜毛豆子,早上饿得昏过去,夜里饿得困不着。外婆带了四个弟弟去苏州河边的粮食码头捡漏在地上的米粒,兜了衣裳里带回家,唯一吃进肚皮的荤菜,是从笼子里捉到的几只老鼠,马上剥皮下了油锅。后来外婆每趟看到老鼠都像看到恩人,看到猫就要拿起扫帚赶了远。虽然一家门拼了老命活下去,饥荒的第三十日,最小的弟弟还是死于营养不良,小小的身躯没了分量,一张草席卷起来送去火葬场。外婆说,我也要去了。我说,外婆瞎讲了。我又问外婆,能让医生开一瓶阿司匹林吗?外婆说,抽屉里有。我说,这是医生给你吃的药。外婆说,我可以问医生再开,我是老年痴呆,就讲原来的药寻不着了。焦点平台
从医院回来蛮晚了。对面阳台亮了灯,琵琶小姐在写作业。清点冰箱里剩下的食物,暂时还没变化,我把阿司匹林放进冷藏室,无声地关上冰箱门。我背靠了“海宝”冰箱贴,想象冰箱深处弹出一只手,青筋暴突,皮肤松弛,每根手指头干枯细长,猫捉老鼠似的抓起阿司匹林,塞进轰鸣的压缩机,传送到外婆的饥荒岁月。房间安静下来,我没上开心网偷菜。关了电脑,熄了灯,我困到沙发床上,尘世的声音撕开墙缝钻进来。
天蒙蒙亮。我被一泡尿憋醒。我打开冰箱。阿司匹林消失了。蔬菜、冻肉、鸡蛋、酸奶也统统消失。冰箱在一夜间彻底清空。冷藏室多了厚厚一叠现金。数钞票的摩擦声比琵琶声好听多了。我点出两千块人民币。冰箱里还有一张钢笔写的小纸条:“冰箱君:谢谢你的阿司匹林。再附一千块现金,请填满这台冰箱。清单详见背面。冰箱老人。”焦点平台
这天傍晚,我像个马戏团杂耍艺人推着家乐福超市购物车,按照小纸条背面的清单——十二种蔬菜、八种冻肉、火腿肠、速冻汤团、卷子面、方便面、面包、大米、牛奶、水果、啤酒和香烟。堆积如山的食物淹没我的头顶,仿佛一座太行山,一座王屋山。收银员耗费半个钟头才能全部录入。我没有信用卡。我掏出十几张粉红色钞票。我回过头才看到琵琶小姐。她跟她妈妈在我背后排队老久了。她妈妈说,快点结账啊。等我把购物车推出闸口,头顶爆发了一场山体滑坡,十几个包装袋砸落到地上。我像操纵泰坦尼克号那样艰难地停稳购物车。琵琶小姐已经蹲在地上帮我捡东西了,当中混了一包卫生巾,这玩意儿也在冰箱老人的购物清单里。琵琶小姐瞪我一眼,卫生巾交到我手里。她的手指甲就像一片贝壳。琵琶小姐的妈妈拖开女儿,关照不要多管闲事。家乐福购物车不能推出卖场。我拖了最大尺寸的拉杆箱走回外婆家。我担心冰箱会被塞到爆炸。暴饮暴食容易猝死。隔天早上,我打开冰箱,冷藏室和冷冻室已经干干净净,骨头渣子都没吐出来——除了一叠粉色的人民币。焦点平台
这台冰箱成了自动售货机。我准备了一份记账本,每天揿了计算器,记录从冰箱得到的收入跟支出。我把攒下来的钞票藏在储钱罐,每夜数一数有助于睡眠。爷爷每隔两日来给我烧菜。除了阳澄湖大闸蟹还没到时令,国际饭店中餐厅的菜单已经做了个遍。但我每趟只吃一道菜,剩下的放进冰箱。爷爷问我不合口味吗?我说同学们都欢喜爷爷烧的菜,明日带到学校里给他们尝尝。如果不算食材费和爷爷的人工,这个利润是百分之百。我还会帮冰箱老人买药,他的心脏不太好,急要了硝酸甘油。
我也给冰箱老人写小纸条。可惜我的字太难看,好像板砖砸在纸上。冰箱老人告诉我,他已经七十四岁,做过四十年中学老师。我把自己的数学卷子塞进冰箱,有两道题实在太难。早上我从冰箱里收到卷子,答案写在另一张纸上。冰箱老人买一送一,数学卷子下面垫了一本书,封面上是个文艺复兴年代的欧洲人。附了一张小纸条:“你必须学会自己解题,送你笛卡尔的《几何学》。”我问还有其他书吗,冰箱老人又送我《第一哲学沉思集》。面对冰箱里的笛卡尔,我觉着沉思才是世上最难的事,要是爸爸妈妈懂得沉思也不会分开,冰箱懂得沉思何必吞下这么多食物?我问有没有好看的小说,我以为会收到《笑傲江湖》或者《哈利·波特》,但我收到了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缪的《鼠疫》,还有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我看完了第三本书——我决定不吃早饭,上午第二节课就头晕了,并且胡言乱语,化学老师说我属于低血糖和电解质紊乱。恢复早饭以后,我决定不吃中饭。下午两点,我饿倒在体育课的操场上,仿佛来了月经的女同学。我告诉自己白天不能饿肚子,但可以晚上不吃饭,据说比较健康。天黑以后,饥饿占据了所有的注意力,我开始彻夜失眠,直到黎明前被冰箱里的鬼魂吵醒。饥饿是世上最恐怖的感觉,仿佛打烊后的游戏机房,只剩下闪闪发光的屏幕,轮番滚动字母和数字,诱惑你掏空钱包投入代币,等于投入陌生的天堂。你会心慌意乱,担心地板开裂,天花板纷纷坠落,洪水淹没你的脖子。你会期望自己被抓进监狱,最好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少有口饭吃。焦点平台
冰箱老人说他并非鬼魂,而是真实存在于地球上。我怀疑他活在外婆记忆中的饥饿岁月。但在五十年前,这幢楼尚不存在,冰箱这种玩意儿也刚发明。更有可能在五十年后——历史并非全部笔直向前,我们时常走上岔路,甚至原地掉头返回,比如第三次世界大战后的核冬天,每个人必须躲在八百米深的地堡里度过余生。或者,冰箱老人跟我活在同一时间,但远在某个深山中的不毛之地,交通与人烟断绝,肉、蔬菜和鸡蛋统统是奢侈品,逢年过节才能宰杀一头羊,看不到医生,也寻不着药。要么在东南亚某个小岛,四面环绕炎热的大海,红树林根须顶破地板,每天午后一场瓢泼大雨,巨龙般的湾鳄潜伏在瘴气弥漫的沼泽中,姑娘们海藻般的长发垂落在丰满的乳房上,但那边是瓜果飘香,下海能捉到鱼虾,应该也不至于饥饿。冰箱老人大概是住在撒哈拉沙漠,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血黄沙,全部家当就是这台冰箱,电源是太阳能或者堂吉诃德的风车。裹着蓝袍的图阿雷格人的骆驼队路过,用写着象形文字的古埃及莎草纸文书,交换冰箱里的香莴笋、鸡毛菜、咸鸭蛋、粢饭糕、速冻小馄饨,或者我爷爷做的扬州炒饭。焦点平台
四月,最后一个礼拜,记账本里收到九千四百块,实际支出五千六百块,净赚三千八百块,等于过去三年压岁钱的总和。我把钞票藏在裤腰带里,去了曹家渡的自行车行,买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这是爸爸答应给我的生日礼物。但直到爸爸妈妈离婚,我也没等到自己的生日礼物。从前每到春天,爸爸就会带我去田野写生,专挑偏僻的腰眼角落,比如窝在青浦乡下的青龙塔。爸爸讲这座塔造了一千年,唐朝跟宋朝辰光,此地是一座繁荣的海港,苏州河还叫吴淞江,水面辽阔直通长江口,青龙塔就是商船出海的航标,可以横渡东海去日本,也能去遥远的马六甲海峡。春日午后,我骑了捷安特自行车出门,穿一件白衬衫,背包里装了画板、画笔、颜料跟调色盘。我像骑了一匹黑色野马,踏过潮潮翻翻的油菜花,终于望见一座孤零零的宝塔。一千年前的灰色砖头砌成八角形,一层层堆叠上天,某年台风吹落塔刹,只剩一根倾斜的塔身。我见到的是青龙塔的尸体,经过七趟改朝换代,年复一年的瘟疫、饥荒、战争,泥沙俱下的海港淤塞,吴淞江倒退成苏州河,城镇夷为寂静的田野。调色盘上挤出好几种颜料。画幅大半留给深蓝色天空与浓云。一只斑鸠停在塔身上横出的一截焦黑木头上。地平线上画出金色与绿色夹杂的油菜花。耳朵绑了白纱布的文森特·梵高骑了我的自行车在田埂上转圈。焦点平台
我把这幅画送给了冰箱老人。我收到冰箱老人的回信:“谢谢你的春天。”我问他,你看不到春天吗?冰箱老人说,心里能看到。我听不懂。我推开厨房间窗户。当我偷看对面阳台上的琵琶小姐,琵琶小姐也在观察对面窗户里的我。她正在踮着脚晾晒内衣,白色胸罩和内裤仿佛两对小白鸽的翅膀,吹了苏州河上的野风,即将扑入春天的浓云。冰箱不仅是我的提款机和私人信箱,也是一口有求必应的树洞。我把自己的秘密写进小纸条。冰箱老人知道了我爸爸抱着女学生在十三陵和公主坟描绘春天,我妈妈带领中国代表团在阿尔罕布拉宫的阳光下晃荡,我外婆正在六人病房里苟延残喘,我爷爷跟西哈努克亲王的往事,我每天守在厨房窗前偷窥对面六楼的琵琶小姐——她家里并没有男人的迹象,这两日她妈妈不在家,琵琶小姐自己煮方便面吃。焦点平台
“为什么不请琵琶小姐来家里吃饭?”这是冰箱老人传给我的最后一张小纸条。
我给爷爷打了电话。爷爷说,今日让你享受西哈努克亲王待遇。挂了电话,我从床底下寻出吸尘器打扫房间。我按照外婆的手势收作厨房,抹布揩了三遍冰箱。银灰色冰箱门照出我的脸,至少不难看。我放了热水洗澡。卫生间的镜子前,我看到皮肤下流淌的青色血管,数出自己的每一根肋骨。我用外婆的牛角梳篦头发,鼻尖不合时宜地爆出一粒痘痘。
风有点冷。我穿过曹家渡的小马路,第一次走进对面楼房,好像隔街相望的双胞胎,水泥台阶一样贴满小广告。走到六楼,我稍微有点喘,防盗门上有只猫眼,贴了两道虎年春联。我敲好门才看到门铃。防盗门打开。琵琶小姐看到我就噗嗤笑出来,因为我穿了世博会主题T恤,胸口有只蓝颜色海宝。琵琶小姐说,你是对面六楼的?我说,是啊。琵琶小姐说,有事吗?我说,我爷爷是国际饭店中餐厅的大厨,今日夜里,我想请你吃我爷爷烧的菜。琵琶小姐安静下来,唯独手指头轻微抖动,好像还在阳台上弹拨琴弦。琵琶小姐说,等我三分钟。防盗门关上。超时两分钟,琵琶小姐出来了。她换了一件翠绿色背带裙,配了白衬衫,头发重新梳过。琵琶小姐说,你能陪我去一趟家乐福吗?我想买些东西再去你家。焦点平台
焦点平台:www.sdptzc.com
外婆家门前的马路沿着苏州河通往中山公园后门,那里有棵一百多岁的悬铃木王,据说上海所有的法国梧桐都是这棵树的子子孙孙。我骑着捷安特自行车碾过十字路口。春风吹得孟浪。树上的毛栗子纷纷炸裂,掀起迷你型的沙尘暴。琵琶小姐在后座晃荡双腿,头发沾满金黄细毛,活像沼泽地里的长脚鸬鹚。到了武宁路家乐福,一整面巴黎风光的壁画墙下,我们同时呛出眼泪鼻涕。琵琶小姐的购物车里有一大瓶可口可乐、薯片、话梅、辣条、果冻,还有八支冰激凌。我的购物车里有青菜、洋葱、大蒜头、卷心菜、西红柿、洋山芋、火龙果、冻鸡翅、龙口粉丝、潮州牛肉丸、新西兰羊排、挪威三文鱼,加上十斤面条、两箱卷筒纸。琵琶小姐说,我们只是吃一顿晚饭,不是搭伙过日子。我说,囤积食物是我的习惯。
我和琵琶小姐一道把自行车推回曹家渡。我们捧了几个家乐福大袋子上楼。经过三二门口,九十六岁老太太坐了轮椅上,铁灰色眼角溢出浑浊的液体,好像看了两个贼骨头。六楼到了,我打开门。琵琶小姐先看厨房间。她最好奇我的冰箱。她很多次看到我往冰箱里填满食物。琵琶小姐打开冰箱门,冷藏室和冷冻室都是空的。琵琶小姐说,你一个人吃了那么多?我说,我食量大。我把家乐福买来的东西重新填满冰箱。琵琶小姐问,你把卷筒纸也塞进冰箱?我说,低温消毒杀菌。琵琶小姐撕开两支冰激凌。她吃香草味,我吃抹茶味。焦点平台
爷爷提了一条鱼来了。他看到琵琶小姐先是一愣,然后眉开眼笑。琵琶小姐嘴巴蛮甜,帮忙清洗料理台。爷爷做了本帮菜,红烧鱼、响油鳝糊、四喜烤麸、马兰头香干,加上一锅子腌笃鲜。但是爷爷一口不吃,他讲有糖尿病,必须回到家里吃医生开的套餐。爷爷出门说,小姑娘,今日让你享受西哈努克亲王待遇。琵琶小姐问,西哈努克亲王是啥人?爷爷看看天花板说,柬埔寨国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老英雄,整整四十年前,西哈努克亲王携莫尼克王妃下榻国际饭店,我给两位殿下做了一条鱼,西哈努克亲王胃口大开,特地寻到厨房间,捏了我的手讲了一串英文,头一句“笨猪”,最后一句“傻驴”。焦点平台
我和琵琶小姐坐在台子两端,像两只安静的兔子吃菜。但我先收走了马兰头香干,装了保鲜盒收进冰箱。我说,这是我明天带去学校的中饭。其实是因为冰箱老人爱吃本帮菜。穿过响油鳝糊的热气,我偷瞄了琵琶小姐。一条红烧鱼几乎都到了她的肚皮里。我的舌头和牙齿只剩下进食的功能。春风从窗门缝隙侵入厨房间。三官堂桥上的汽车轮胎川流不息,每次碾过桥墩生出沉闷的“咯噔”声。苏州河上的轮船马达也响了,荡起一层层浑浊的涛声,水面上无数把剪刀划破防护堤。我回头再看冰箱。琵琶小姐问,你在看啥?我说,没啥。我打开大瓶可乐,倒了两个杯子。琵琶小姐跟我碰杯。可乐泡沫在舌头尖放焰火。吃好最后一口汤,琵琶小姐揩揩嘴唇皮,眼角滚出两滴泪水说,谢谢你,我第一次尝到那么好的味道,我妈妈烧菜实在太难吃了。
琵琶小姐收作台子,打开水龙头洗碗碟。我开了电视机,世博会倒计时,又是哪个遥远国度的元首到达机场。我立了琵琶小姐背后,呼吸重得像一台拖拉机。琵琶小姐回头问,有事吗?我停了停说,还要吃冰激凌吗?琵琶小姐说,不吃,太甜,怕胖。我还是拉开冰箱门。白光夹了冷气覆盖我的面孔。冰箱里没有任何减少,也没有任何增加。我没能等到冰箱老人的小纸条。琵琶小姐洗好碗筷,毛巾揩揩手说,我还不晓得你的名字。我说,我叫海宝。琵琶小姐笑说,瞎三话四。我说,我真的叫海宝,外公给我取的名字。琵琶小姐说,怪不得,你的“海宝”冰箱贴蛮好看的。我摘下冰箱贴说,海宝送给你。琵琶小姐接过“海宝”,塞进裙子口袋说,谢谢你,海宝。我们加了开心网账号。但我并不想她来偷我的菜。我打开厨房间的窗门。琵琶小姐望了马路对面的楼房,每个窗门里都亮着光,好像灯火通明的蜂巢,只有六楼阳台是黑的。几滴雨水落下来。琵琶小姐说,我要回家了。我抓起外婆的长柄伞说,我送你。焦点平台
到了楼下,我为琵琶小姐撑起雨伞过马路。细密的雨点落在伞面上。两个人的影子在金色的路灯下轮番交错。琵琶小姐说,海宝,你该回家了。我说,琵琶小姐,再见。我看了她走上楼梯。琵琶小姐的影子先消失,然后是脚步声。
我回到六楼,收起外婆的长柄伞。冰箱还是塞满的。保鲜盒里的马兰头香干还在。对面六楼阳台拉起窗帘。诺基亚手机响起大华尔兹铃声。爸爸从北京打来电话。我告诉他外婆中风进了医院。爸爸对此一无所知。他在北京寻到了工作,专门为图书画封面。爸爸给我搞到了中国美院附中插班生的名额,我可以在北京继续学画。我说,不去。
关掉最后一盏灯,我困在沙发床上,听到底楼的老头雷鸣般的咳嗽声,夹杂黏滞的吐痰声,好像点了一根火药线,整幢楼都骚动不安起来。二楼产后抑郁的女人与婴儿,三楼九十六岁老太太的轮椅,四楼游走在凶杀案边缘吵架的夫妻,五楼通宵达旦的麻将搭子们,此起彼伏各种唱腔的咳嗽声。雨点凶猛地撞击六楼窗户,沿了外墙流淌汇聚到马路上。苏州河像一口堵上塞子的浴缸。春潮没羞没臊地翻涌溢出了防护堤。黑色的水淹没了曹家渡,倒灌进沪西电影院的午夜场。曹家渡花市几万支玫瑰浸泡腐烂。鸟贩子店铺里上千只画眉、鹩哥和虎皮鹦鹉在笼中溺毙。水变成无孔不入的病毒,从底楼迅速传染到六楼,穿透门缝蔓延到地板上。我从沙发床上漂浮起来。外公的遗像漂到我的脸上。整幢楼最重的冰箱都浮起来了。房子眼看要变成灌满水的棺材。我只能爬上双门冰箱,顺着汹涌的水流漂出窗户。等我回过头一看,整栋楼消失了。我想要看到马路对面的琵琶小姐。黑茫茫的水面上只漂来一张琵琶。天亮了。我躺在冰箱上面对浓云和雨点,胸口印着“海宝”。冰箱是我的救生筏,也是天方夜谭的飞毯,穿梭在长江三峡似的悬崖峭壁间。我看到静安寺的金刚宝座塔尖,爷爷引以为豪的国际饭店。我在南京路的上空随波逐流。全城上百万只木头马桶在水上漂浮。终于到了外滩。眼门前的海关大钟敲响八下,振聋发聩地奏响东方红。黄浦江消失了。浦东和浦西已是连成片的海洋。陆家嘴变成一群海上冰山。我差点被环球金融中心切成两半。浦东成了太平洋的一部分。世界博览会的地盘到了,水上漂来一块广告牌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殷墟般的中国国家馆,搭积木似的红色斗拱,只剩最高一层露出水面。美国馆、日本馆、德国馆、俄罗斯馆、印度馆,地球上一半国家沉入水底。冰箱是一艘诺亚方舟,漂到中国馆屋顶上搁浅了。火山灰似的尘土从天而降。我拉开冰箱门,像个饿死鬼钻进去觅食。没有电的冰箱是一个温暖的子宫,塞满了丰沛新鲜的食物。冰箱里的东西不会腐烂,所以我们才能活下去。现在我才晓得,每个人的归宿都是冰箱,然后才到坟墓。焦点平台
天上打了一只惊雷。我睁开眼睛,衣裳沾满了眼泪水。我从沙发床上爬起来。窗外暴雨倾缸。马路对面的楼房还在。琵琶小姐的阳台拉了窗帘。六层楼下柏油路上,只有一层薄薄的积水。冰箱还站在厨房间里。我拉开冰箱门,没看到任何变化,依然塞得水泄不通。世界回到了外婆中风的前一天。焦点平台
我从未放弃过冰箱老人。我每天放学去家乐福超市,我成为了白金会员。我继续往冰箱里塞满各种食物,还有卷筒纸、处方药,甚至卫生巾。我发现这台冰箱像个海绵,无论多少东西都能塞得下,只要用力往里一推,冰箱又会多出新的空间。我决定每天塞满一次冰箱。但是储钱罐已经空了,这个月赚的每一分钱已如数奉还给了冰箱。我把过年收到的压岁钱都贴进去。我在外婆家里翻箱倒柜,但只寻着两百块现金,还有两罐子硬币。焦点平台
妈妈从马德里的春天打来电话。那是一片干燥而温暖的高原,妈妈领着中国代表团在伯纳乌球场,帮我搞到了C罗的签名球衣。我说我是巴萨球迷,你给我弄个皇马球衣干吗?明日夜里,妈妈就要从马德里起飞,后天早上到家。妈妈问我一个人住得还好吗,我说很好,吃得特别好。妈妈不太相信。妈妈让我去一趟医院,听说外婆的情况又不好了。
我骑上捷安特去了医院。外婆缩在病床里,好像个白头发的木乃伊。外婆把手指头塞进我的左手掌心里。外婆会看手相,她讲我的生命线相当长远,不像外公六十几岁就走了。我贴了外婆的耳朵问,家里还有钞票吧?外婆的嘴唇皮嗫嚅,喉咙里含一口浓痰,发出混沌的声音,在你外公的背后。我攥了外婆的手指头不放开。我叫护士过来给外婆吸痰。
我从外公的遗像背后寻到一只牛皮纸信封,装了五千块现金。隔日,我去家乐福装满五台购物车,再叫一部厢式货车拉回来。我爬了八趟楼梯,等于登高四十八层,要是加上八趟下楼,等于九十六层的摩天楼,接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各种食物堆满了房间,从厨房间排队到了卫生间,体积至少有冰箱的十倍。我忙了整整一夜才填满冰箱。如果对面是一间相同面积的房间,不但塞得水泄不通,还要从窗门缝里漏出来。我坐倒在冰箱门上,眼皮一搭困着了。焦点平台
早上,冰箱已经空了。这几天塞进去的东西都不见了。这台冰箱空得清清爽爽,好像刚从永乐电器搬回来的状态。我整个人钻进冰箱,就像闯入《纳尼亚传奇》的衣柜。但我撞了墙。我用拳头撞击冰冷的白霜。我没有力量穿透白色的冰箱内壁。我从冰箱里钻出来。我拔出电源线。压缩机安静了。我用尽力道把冰箱挪出来。我从外公的工具箱里寻出螺丝刀,卸下冰箱背后的铁壳。我想找到某个世界的入口。但我只看到压缩机和密密麻麻的电线。
钥匙转开门锁的声音。女人皮鞋踢踢踏踏。拉杆箱轮盘滚动。妈妈从西班牙回来了。她叫了好几声“海宝”。我没有回答。妈妈走进厨房间,问我出了啥事?我说,没事体。妈妈说,你做啥拆冰箱?我说,进了老鼠。妈妈把冰箱恢复原样,推回老位置插上电源。妈妈打开冰箱说,小鬼,本事大了,统统吃光。妈妈变漂亮了,化妆跟发型蛮有讲究。妈妈带了飞机上的点心给我吃,调好衣裳就去医院看外婆。焦点平台
这一夜,刚好是二一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妈妈准时打开电视,开了一瓶西班牙红酒,我开了一瓶可口可乐。对面阳台的琵琶小姐还在弹《十面埋伏》。谷村新司唱了《星》。安德烈·波切利唱了《今夜无人入眠》。妈妈认出了法国总统萨科齐跟他的意大利超模老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韩国总统李明博、越南总理阮晋勇、柬埔寨首相洪森。我突然问,为啥没西哈努克亲王?妈妈笑了说,你还想吃爷爷烧的菜啊?
春天转眼死去。我在烈日酷暑下去过三趟世博会。我在沙特馆排过三个钟头长队,在阿根廷馆落了皮夹子,在印度尼西亚馆学会了画皮影戏。我去西班牙馆不需要排队,因为妈妈是工作人员。但是红色斗拱的中国馆,每趟我都是远远眺望,好像屋顶上躺了一口冰箱。这个夏天我长高了十公分,嘴唇上冒出一圈柔软的绒毛。我把家乐福的白金会员卡给了妈妈。冰箱重新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但我强迫自己读完了冰箱老人送给我的书,虽然没能读懂加缪的《鼠疫》。琵琶小姐照旧在夜里八点弹奏《十面埋伏》,直到霸王跟虞姬抹了脖子,我再也没有去敲过她的房门。
过了中秋节,阳澄湖大闸蟹来了,我和妈妈抱了外婆的骨灰盒,租一台车跨过杭州湾大桥,埋入宁波山上外公的墓穴。外婆没有留下遗嘱,为了曹家渡这套房子,妈妈跟舅舅半夜里吵架,最后签了一份协议,决定房子挂牌出售,钞票各分一半。我还不敢让妈妈晓得,藏在外公遗像背后的五千块钱消失在了冰箱里。焦点平台
漫长的二一上海世博会闭幕了。我穿过家门口的马路,爬上六层楼,敲开琵琶小姐的防盗门。琵琶小姐笑笑说,你终于来了。我说,明天早上,我就走了。琵琶小姐说,你去哪里?我说,西班牙,妈妈要去那边工作,我要去那边读书。琵琶小姐说,我还能见到你吗?我说,可能有点难。琵琶小姐说,你等一等。我只等了半分钟。琵琶小姐出来塞给我一张小纸条,写了一条固定电话号码。琵琶小姐说,以后打我电话。我攥紧小纸条说,现在才给我啊?琵琶小姐说,你没问我要过啊。我说,再见。琵琶小姐说,再见,海宝。
夜里关了灯,我困了沙发床上,听厨房间冰箱的喘息声。在上海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盖了同一条棉被。妈妈讲起一九八年的曹家渡,像只巨型的五芒星迷宫,环绕长寿路与万航渡路口的交警岗亭,瞄了上海的五个方向辐射而去。妈妈生在闸北区番瓜弄,八岁才搬到曹家渡——外公被评为社会主义先进工作者,单位分配了这套六层顶楼的房子,当时几乎是方圆一公里内的制高点。妈妈头一趟用了抽水马桶,铺了马赛克的水泥浴缸。外公跟外婆住了里间,妈妈跟舅舅住了客厅。舅舅比妈妈大五岁,经常偷吃妈妈的早饭,兄妹俩不但吵架还会动手,但妈妈从没吃过亏。妈妈在这幢楼里度过了十六年。等到她搬出去那天,我已在妈妈子宫里发育了六个月。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我想。焦点平台
天亮辰光,妈妈整理好三只大号拉杆箱。我的捷安特也可以托运上飞机。我打开清空的冰箱,拔了电源,只闻得着冰箱本身的气味。下个礼拜,房子的新主人就会搬进来。这台冰箱会送进废品回收站粉身碎骨。出租车等在楼下了。妈妈催我出门,我们要从浦东机场直飞巴塞罗那。我说,等我一分钟。我撕了一张小纸条,匆匆写一行字塞进冰箱——
冰箱老人:
我等你回来。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一日,上海,曹家渡,冰箱君
虎年转了一轮回来。我已经二十六岁。我住在一万公里外的巴塞罗那。梅西终于离开巴萨,我去机场为他送行,举起十二年前的签名球衣。我没能成为画家。我和妈妈在巴塞罗那老城区开了一家中餐馆,名叫加泰罗尼亚上海饭店,雇佣了五个越南厨师。食客们大多是巴塞罗那本地人。我每天坐在餐馆门口的小圆桌上,眺望高迪的圣家族大教堂。我总觉得那是一座巍峨的冰箱,戳着星辰般的褶皱、孔洞和雕塑,依靠无数根巨人的腿骨支撑起来,装满足以供养全人类的食物。我有个女朋友叫费尔明娜。她生了一双绿眼睛,擅长用古典吉他弹奏《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妈妈谈过几个男朋友,有中国人,也有西班牙人,但没有再结过婚。爸爸又离了两次婚,现在跟二十岁的乌克兰女朋友住在香港。爷爷一家还住在上海老西门的石库门房子。西哈努克亲王死于北京的那一年,爷爷戴了七天的黑纱,蛮像古时候的忠臣。焦点平台
三年前的秋天,巴塞罗那不太平,到处是加泰罗尼亚的黄红间条旗。妈妈暂停了中餐馆的生意,我们飞回上海住了一个月。曹家渡的落叶像金色灰烬铺满街道。琵琶小姐住的那幢楼已经拆了,变成一座天主教堂,哥特式尖顶上挂了十字架,彩色玻璃画了圣母玛利亚的故事。我打了琵琶小姐留给我的电话号码。有个山东口音的男人接了电话,他说我打错了。但我相信琵琶小姐依然在上海的某个角落,可能是浦东,或者闵行。曹家渡的老房子基本消失了,唯独外婆家的楼房幸存下来,围困在几幢高楼之间。时间踩上粘鼠胶,除了老人们变得更老,底楼老头子咳嗽得更凶,三〇二门口轮椅上的老太太已经一百零五岁。爬上六楼,我敲响外婆家的房门。开门的是个老头,至少七十岁,顶着雪山似的白发,面孔上有老人斑,身体干枯瘦长,后背挺得笔直,胸前插一支钢笔。我的眼光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外婆的冰箱依然活着,压缩机发出苟延残喘的噪音,仿佛变成一堵坚不可摧的承重墙。老头说,你好,请问寻啥人?我说,对不起,敲错门了。老头说,没关系。我说,我叫海宝,再会。老头说,再会,海宝。焦点平台
隔年春天,回国变得比登天还难。我有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回过上海。过好耶稣复活节,圣家族大教堂重新人山人海。加泰罗尼亚上海饭店每夜翻台两三趟,半夜十二点还有人等位,妈妈数钞票数得开心。我和费尔明娜准备在巴塞罗那结婚。四月最后一个黎明,中餐馆楼下厨房的冰箱开始轰隆巨响。我躺在费尔明娜的胸口,梦见自己回到了曹家渡。我爬上寂静的六楼,用一根铁丝打开门锁。房门被沉重的分量顶死,门缝里滚出腐烂的蔬菜。我寻来几个男人卸下门板,不计其数的冻肉、火腿肠、速冻汤团、卷子面、方便面、面包、大米、牛奶、水果、啤酒和香烟冲出房间,仿佛一场溃坝灾难。我从堆积如山的食物上爬进厨房间。冰箱大门敞开,像一张嘴巴吐出各种东西。人们清空了厨房和冰箱,终于从食物的深渊里打捞出一具尸体。七十四岁的白发老头,双手双脚并拢折叠,像个蜷曲的小毛头,死因是心肌梗塞。老头僵硬的手指捏了一幅水彩画——金色的油菜花田上,衰败了一千年的宝塔冲向春天,仿佛断了头的通天塔。焦点平台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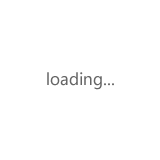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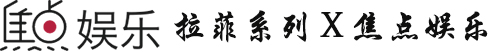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