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报道:
一
我坐在餐厅二层的靠窗位置,面朝大海的餐桌边就我一个人。我的桌上有一盘生煸草头,一盘咸鱼烧茄子,还有一小碗米饭。老板娘头顶一朵金黄色云团,端了一碗赠汤送到我桌上,用一种对待远房亲戚的语气说,吃啊吃啊,勿要客气。
我笑笑说,谢谢老板娘。低头看汤碗,泛白的汤色,几缕裙带菜漂浮在上面,闻起来有股鱼腥味。我怀疑,这家叫“海市蜃楼”的小饭馆里的赠汤,如果不是用鱼骨熬出来的高汤,就是刚烧过鱼的刷锅水。不过我并不介意,我给自己的规划是伙食费每天不超过一百元,我需要省着点花。
金乌嘴渔村靠海的街上有数十家饭馆,之所以选择这一家,是因为它便宜,并且,它二楼的小餐厅有一面巨大的东窗,我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窗外,是一条被叫作沪杭公路的宽阔的海堤,海堤的外侧,是苍茫而又喧嚣的大海。灰色泥浆般的海滩上停泊着两艘渔船,一大一小,像一对有十岁年龄差的兄弟。船体外壳涂着蓝色防腐漆,也许是海水日久侵蚀,油漆已经斑驳脱落。船舷和甲板上拉着横七竖八的绳子,绳子上挂着千疮百孔的渔网,发黄的布帆收拢在桅杆底部,像细腿上堆着褪下的破裤子,这让两艘旧渔船看起来像两个蹲守在街头的无业游民。这很好,让我在独自一人的午饭时间里陡增想象空间。焦点
我是两天前坐着长途汽车来到金乌嘴渔村的,它地处沪浙交界处的杭州湾畔,虽然它属于上海,但我听出来,这里的人说的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介于上海话与浙江话之间的方言。对了,我要说的是,我来金乌嘴渔村是为了闭关,我给自己设定的时间是七天,今天是第三天。
张达明问我为什么要闭关?并且是七天?我说,我的长篇小说快要杀青了,我得完成结尾,七天是预估,最终几天能完成,视情况而定。张达明说,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他没有再追问什么,他总是这么克制,抑或,他只是心不在焉。
在这之前,我已经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地方,盘算了很久可以去哪里。我不敢走得太远,因为我不太有钱。这个城市的很多角落散居着一些像我这样被冠名为自由撰稿人的无业者,名义上我们靠写作生存,但如果我们的书不够畅销,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养不活自己。我已经当了十年自由撰稿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小说的畅销与否,与文学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可能,这需要缘分?好吧,我承认,我的书不畅销,我的稿费只够勉强养活自己,但是不足以改变生活,这让我在张达明面前总是处于弱势,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强势的样子,但我还是为此感到忐忑。
张达明赚的钱大概是我的七到八倍,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三年来,我从未主动问他要过钱。我知道,我的胸腔里藏着一颗过于自尊、脆弱的心脏,它让我总是处于傲慢与卑微的边界。问男人伸手要钱会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虽然我也常常接受他不定期主动给我的钱。但是,当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沓纸币时,我总会很自然地想到,今晚要与他完成一场床笫之事。我知道这么想是有问题的,但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把他递钱给我时的动作和表情想象成一种恩赐。焦点
张达明主动给我钱的频率逐年下降,最近一年,他几乎没怎么给过我钱,他很久没对我说,是不是要交房租了?给你点钱吧。我替他找了个理由,用以自我宽解: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每个月,他的工资都以数字的形式进入他的账户,他正在适应无现金生活,一时还没习惯用转账的方式给我钱。
可以确定的是,我并不是为了钱而负气出走,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自己。为此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发现,我只是想离家出走几天而已,没有理由。是的,我和张达明,我们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没有明面上的矛盾让我们拉下脸皮敲桌子、摔杯子,相互指责、贬斥、谩骂,乃至发生肢体摩擦,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是,倘若我对张达明说,我就是想离家出走几天,那他肯定认为我脑子出毛病了,所以,我只能说我要闭关写稿。事实上,没有人逼我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长篇小说。焦点
就这样,我带着用了很多年的笔记本电脑离开了家。我选择了离市区七十公里远的金乌嘴渔村,据说这是上海陆地上形成最早的渔村,如今也是上海的最后一个渔村,据说它古老的街道和飘逸在街道上空的海腥味来自清朝。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七十公里足以让我确信这是离家出走,并且,这个上海远郊的渔村还处于初期开发阶段,有民宿客栈、饭店酒吧,但没有多少游客,物价还没有飙升起来。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它让我“离家出走”的命题更加完善。
二
到达金乌嘴渔村的第一天,几经对比价格和环境,我订下了这家靠海的民宿。一栋正门朝向大海的二层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海蓝底色,上面翻卷着白色浪花,浪花里夹着“海市蜃楼”四个楷体字,“海”的左边爬着一只张牙舞爪、面红耳赤的大螃蟹,“楼”的右边是一只伸着很多条腿正翩翩起舞的大章鱼,一眼看去,叫人无法分辨这是一家水族馆,还是一家海鲜饭馆。好在招牌上的螃蟹是红色的,这足以证明它被烹饪过,如此,“海市蜃楼”就是一家饭馆。
饭馆的后门通向内院,绕过几株月季,几棵冬青,一个凉棚,就是另一栋二层小楼,那是老板和老板娘的住所,也是为游客提供住宿的客栈。我要了一间一层的单人房,一晚一百三,价格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焦点
两天后,我与老板娘已然成为熟人,她染成稻草色的头发在脑袋上顶起一朵枯燥的金云,金云下是她那张时刻赔着笑的饱满的脸。两天来,她是我在金乌嘴渔村说话最多的人,虽然大多时候她用的是本地话,而我说的是普通话,但我们似乎很信任对方的听力和理解力,因为,我每一次点菜她都没有搞错过,而她每每提问“红烧还是白灼”“清蒸还是爆炒”的时候,我也没有听错。
闭关生活进入第三天,三天来,我没有给张达明打过电话,他只在第一天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到了吗?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是张达明对我表达关怀之意的唯一语言,从提出闭关开始,他已经说过两次。我回复他:到了,很安全。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餐桌,“海市蜃楼”二楼小餐厅靠窗位,我一边欣赏着窗外的大海,一边吃着虽然味道平庸但分量充足的饭菜。就着咸鱼烧茄子和生煸草头,我很快扒掉了半碗饭,我端起碗喝老板娘送给我的免费汤,汤面上的裙带菜旋转着进入我的嘴巴,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踢踢踏踏一阵响。
来了!我想。男人的说话声传来,嗓子里饱含一口浓痰,从低到高,越来越近。我从汤碗里抬起视线,一颗黑色的头颅从楼梯口探出,是他,那个黝黑的老男人。六十岁左右的样子,矮个儿,方块脸,像扑克牌中的老K。老K斜着肩膀,甩着敞开的衣襟往里走,他的身后,照例跟着她——紫红羽绒服,光滑的鹅蛋脸,脸庞上趴着两朵健康的红云。他们终于来了,比昨天晚了半个多小时,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焦点
头顶金色云朵的老板娘紧随着出现,徐老板介晚才来?我只当你们不来了。
被称为“徐老板”的老K回应,来啊,哪能不来?今朝等一个朋友。
老K说的也是本地话,他黝黑的肤色,以及斜着肩膀、敞着衣襟的样子,令我想象他渔民的身份。是的,我在“海市蜃楼”吃了三天饭,每天中午,我都在二楼的小餐厅遇见他们。不过,老K说了,今天还有一个朋友。
我再次看向楼梯口,十秒钟后,上来一个中年瘦男人,高个子,鞋拔子脸,肤色同样黝黑。这是多出来的一个,前天和昨天都没有他,相比老K,他更像扑克牌中的J勾。
两男一女渐次落座在我身侧的另一张餐桌边,老板娘开始给他们点菜。老K捏着一张破旧的A4纸,指着印在上面为数不多的菜名说,清蒸海鲈鱼,勿要放大蒜;白米虾新鲜吗?盐水吧;再搞点素的……我回忆起昨天他们点的菜,是一碟海瓜子,一盘青菜,还有一碗榨菜蛋汤。今天比昨天丰盛,大概是多了一位客人的缘故。焦点
正想着,听见女声插话,尖锐脆亮,带点发育不完善的娃娃音,芥菜糯米饼好吃,要一份吧?是皖北的口音,又像豫东。
老K打开饱含浓痰的嗓子,慢吞吞说,再吃,再吃就太胖了!他忽然改用普通话,显然是要让女人听懂,却因为浓重的本地口音,他的普通话更像是第三国语言。至此,新加入的J勾还没发出过任何声音,坐下后,他一直在看手机。
我侧目看向女人,与昨天一样的衣着,短款羽绒服,紫红色,太过紧小,勾勒出浑圆的躯体;厚重的刘海儿遮盖住上半张脸,露出的下半张脸饱满圆润,这证明她很年轻。正好,领桌的两男一女凑齐了扑克牌中的三张花牌,女人算皮蛋——Q吧。这么想着,我几乎要笑出来,她大概感觉到我在看她,脑袋向我转过来,我迅速把目光移向窗外。
窗外是正在退潮的大海,也许是冬天的缘故,这里的海和影视剧里的海很不一样。这里的海是灰色的,海边没有金色的沙滩,只有泥浆色的滩涂,灰色的大海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巨人,一边节节后退,一边收起声势,丢下大片劫后余生的泥沙,在远处低吼着等待反扑的时机。
我从窗外转回头,继续吃饭,咸鱼烧茄子太咸了,我朝楼梯口喊,老板娘,倒杯水好吗?
穿紫红羽绒服的皮蛋从手机里抬起头,终于,我们的视线对上了,三天来第一次。但她很快垂下眼皮,划着手机屏幕,一边说,为啥不点芥菜糯米饼?要不然,给俺点一碗饺子吧。焦点
她把自己叫“俺”,她还没来得及改掉她方言中最“土”的部分,再加她脸颊上的两朵红云,都证明了她来自农村的特征还未褪去,这让我暗暗断定,她是刚来上海不久的“新人”。可是前两天,我没听见她说“俺”,她甚至都没怎么说话。
第一天,中午十二点,就在这里,我初次遇见他们,她,以及老K。以我的直觉,我不认为他们是熟人,因为,全程只有老K偶尔发出饱含痰气的说话声,像第三国语言的普通话。她好像有点羞涩,在被老K提问“要不要添饭”“吃饱了吗”时,总是回以最简单的词汇,“不要”“饱了”。昨天,同样的钟点,我正在享用我的午餐,他们又来了,老K问,想吃什么?皮蛋探头看了看我的餐桌,指着芥菜糯米饼和八爪鱼红烧肉说,这是什么?看着怪好。
这是她前两天说过的所有话,她让我产生了些微优越感,以及感同身受的期待。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五年的非上海人,我身上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痕迹大概已经消磨殆尽。譬如,我不再习惯于把大葱和生蒜当作与主食配套的必备小菜,再譬如,我已经学会在公共场所用最小的声音提出最严肃的诉求。当然,我也看见了皮蛋的变化,三天来,我眼见她一天比一天主动起来,今天,她好像不再矜持,变得有主意了,还学会了提要求。似乎,她更喜欢面食,比如芥菜糯米饼和饺子,海鲜对她没有太大吸引力。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父女?口音不一样,相貌也不像。同事?朋友?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猜测,但他们对话太少,我无法从只字片言中分析出答案。焦点
餐厅里没有别的客人,除了我,以及另一桌的两男一女。这让我有些不安,吃饭的享受感不再充分,就像一名身陷黑店的侠客,貌似一切都与我无关,事实上,每一张平静的脸背后,都隐藏着某个令人兴奋抑或恐惧到尖叫的阴谋。是的,我用了两天时间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想象力抵达真相,第三天,他们又增加了一个人。我的好奇心呼之欲出,我恨不得坐到他们的餐桌边,与他们攀谈一阵,以了解他们的真实关系。当然,我没有这么做,这不符合我一贯的形象。
老板娘给他们上了最后一道菜,同时给我送来一杯水。紫红色的皮蛋站起来,问厕所在哪里,然后在老板娘的带领下出餐厅,下楼梯。餐桌边剩下两个男人,老K端起酒杯,碰了一下J勾的酒杯,来,陈老板,吃酒。
现在我知道了,老K是徐老板,J勾是陈老板。我怀疑,这里的男人都是“老板”,就像城里的男人都是“先生”一样,熟人之间相互打招呼,只需在老板前面加上姓氏即可。那么,这里的女人,岂不都可以叫作“老板娘”?皮蛋是老板娘吗?焦点
老K和J勾各自干掉了一杯本地黄酒,而后沉默着吃菜,没再说话。十分钟后,皮蛋回来了,老K站起来,你们慢慢吃,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说完转过身,甩着敞开的衣襟,斜着肩膀,顶着黑胖的方脸晃悠悠地下了楼梯。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又往嘴里扒几粒米,再看一眼窗外灰色的大海和破旧的渔船,同时,我把听觉神经调到最高的灵敏度。可是,J勾和皮蛋始终没有说话,我只听见碗筷的碰撞声,以及来自邻桌的咀嚼声和吞咽声,直到他们吃完,结账离开。对,是J勾结的账。
三
晚上七点半,我在客房里对着电脑屏幕打字,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章正进行到一半。老板和老板娘在后院里搬运海鲜,泡沫箱碰撞摩擦,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说话,聒噪声伴随着鱼虾的腥味涌入我的房间。他们的嗓子里带着天然的、来自大海的基因,高亢耿直的是老板,略微沙哑却生猛的是老板娘。一开始,我还能听懂他们对话的大部分内容,比如笋壳鱼和梭子蟹的进价太高,赚不了几个钱,二道贩子坏得很,遇到小饭馆就抬价……他们说着说着,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也越来越响,像是争论起来。最后,两人的说话声搅拌在一起,带着浓重的火药味,令我怀疑一场海啸即将来临。焦点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文档,竖着耳朵分辨门外的说话声。可是,一旦进入吵架模式,他们的乡土语言就变得格外陌生,我听出了老板呵斥的语气和老板娘争辩的语调,我还听懂了几句他们一来一往不分伯仲的骂人的话,带着全国通用的脏字,他们还多次提及一个叫“王老板”还是“汪老板”的人。果然,这里的男人都是老板,这让我既感觉好笑,又觉得实在恰如其分,是的,对于他们,我找不到一个比“老板”更贴切的称谓。
老板和老板娘还在用我陌生的语言进行着激烈的争执,虽然我依旧没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夫妇俩的矛盾昭然若揭,以我有限的理解,我猜测,他们对“王老板”还是“汪老板”产生了看法上的严重分歧。最后,我听见一声肌肤激烈碰撞发出的脆响,果断而又猛烈,紧接着,老板娘的哭声如裂帛般迸出,虽然沙哑,却巨响无比。
我跳起来,准备冲出去劝架,但在打开房门的瞬间,我犹豫了。我突然想到,我是应该先谴责打人的男人,还是先抚慰被打的女人?并且,打人的未必是男人,老板娘完全拥有打男人的体魄,作为女人,她还有号啕大哭的权利。再说,倘若我去劝架,最后的效果却事与愿违,我非但没能有效遏制矛盾升级,甚至还催生了他们更为剧烈的对抗,那该怎么办?焦点
我贴着房门站着,一时不知所措。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来电显示张达明,我脑中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找不到他的内裤了……
张达明就职于一所三流大学,讲师职称。倘若按部就班,张讲师应该在两年前荣升为副教授,但他似乎并不热衷于名利,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教的是大学语文,但平时,他从不把《诗经》和《楚辞》放在嘴上,也不会从《论语》或《庄子》里信手拈几句经典语录来感悟人生,除了完成每周规定的课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下围棋和打桥牌。每天下班回家,他就往沙发里一躺,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进入棋牌游戏网。倘若彼时我正好有问题要问他,他将以缓慢的语速以及温和的态度给予我答案。
张达明,蔬菜沙拉你要千岛酱还是油醋汁?
他捏着鼠标,看着屏幕,一脸放松地重复着我刚说过的那几个词汇,千岛酱、油醋汁,嗯嗯,好……
张达明,你的脏衣服呢?洗澡换下来的,放哪儿了?
脏衣服啊!放哪儿了,是的,是的……
上个周末的傍晚,我在厨房里做饭,我准备切一块五花肉,我的目标是把肉切成薄片,然后与线椒一起做一个小炒肉,这是张达明最喜欢的下饭菜,他点名要吃。为此我特意去五公里外的一家大超市买了菜,除了五花肉和线椒,我还买了烧鸡和豆腐。一回家,我就大刀阔斧地操作起来,我把五花肉放在砧板上,左手按着肉,右手握着菜刀,手起刀落,一股鲜血涌出,不是五花肉,是我的左手中指。焦点
张达明,创可贴,创可贴!我在厨房里大叫,他躺在沙发上岿然不动,眼睛盯着架在膝盖上的笔记本电脑,喃喃道,创可贴,好啊!创可贴……
我扑到电视柜边,打开抽屉,找出创可贴,右手与牙齿配合,包好受伤的左手中指。血止住了,我又去卫生间找出一块抹布,擦干净滴落在地板上的血,然后回到厨房,继续做晚饭。整个过程,张达明都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也许他正处在棋局的关键时刻,他在另一个世界奋不顾身地杀敌,他听不见这个世界的任何声音。
一个小时后,晚餐开始,张达明举起筷子,夹了一片小炒肉送进嘴巴,眉头一皱,肉这么老?做饭开小差了?说完嘴角朝上一弯,露出一个微笑,好像在说,我可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想说我的手指受伤了,为了给你做饭,但我一开口,说的是另一句话,那你吃烧鸡和凉拌豆腐吧。我把烧鸡推到他眼皮底下,又把小炒肉挪到自己面前,与此同时,想了很多天的“离家出走”的念头悠然冒出。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张达明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吞咽动作,喉结滚动了一阵儿,一脸艰难地摇了摇他完好的左手,没必要换,我可以吃。然后又伸手点了点烧鸡,这个,是符离集的吗?焦点
符离集?不是,这是新奥尔良,我说。他立即正色道,那就不是烧鸡,而是烤鸡。
我点了点头,对,新奥尔良烤鸡。
他抿住嘴,笑一笑,没关系,我告诉你了,以后你就知道了,烧鸡和烤鸡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表示宽容的表情,嘴角朝上一弯,抿嘴微微一笑。他总是这么克制,在说烧鸡和烤鸡的区别时,仿佛在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不同。他充当着一名大学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个无聊的食客。他那么有礼有节,懂得给我面子,就好像在刚下课的教学楼走廊里,我跟在他身后问,您能给我推荐几部经典的戏剧作品吗?
他的回答礼貌而又疏离,我可以推荐,但未必是最好的,个人之见,也许是偏见。
他温文尔雅的样子一度让我回味无穷,后来,我终于有些明白,他那么礼貌和克制,其实只是为了掩饰他逃避主义的本性。他不想承担责任,对经典的戏剧作品,对难吃的小炒肉,对我受伤的手……他很少表达他的喜怒与好恶,他缺乏态度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不愿意从自己的世界里抽身而出,就好像,他不愿意把自己的钱过多地转移到我的账户里……这么想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念头愈发强烈。我放下碗筷,对着正扯下一条鸡腿的张达明说,我要出去闭关一段时间,七天,可以吗?焦点
第二天清晨,我在张达明还没醒来时就出了门,我像逃离集中营一样从他的眼皮底下逃了出来。是的,逃离是一种好感觉,我给自己增设了一段挣脱枷锁奔向自由的戏份,这让我有一种把生命与生活的权利夺回自己手中的错觉。走出家门的一瞬间,我完全忘了,我是在征得张达明的同意后才离家出走的。
两个半小时后,长途汽车助我完成了七十公里的横渡,我从市区我们租住的公寓,来到了上海西南远郊最后的渔村。
此刻,是我闭关的第三天晚上,我住在“海市蜃楼”的客房里,一不小心,我见证了老板和老板娘的一场战争,在我犹豫着要不要去劝架的时候,张达明打来了电话。
张达明在电话里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想知道,你这次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个什么故事?
他忽然变得像一个正经语文老师了?这和他一贯的做派很不一样。我们刚认识一个月时,他看过我的一本言情小说,看完后,他忧心忡忡地问我,你好像经验很丰富?
我感觉到了他的疑虑,也许他在书中看到了一个令他恐惧的我。我说,要是写小说都靠经验,那岂不是要累死?写小说的人,最厉害的就是虚构能力……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些怀疑,作为一名大学语文老师,张达明难道不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吗?焦点
他抿嘴笑笑,哦,的确是这样的,对!
他没再对我那本言情小说提出什么异议,从那以后,他也不再看我的任何小说。可是今天,他突然关心起我的小说来,这让我不禁怀疑,他是要做什么重要的决定吗?还是作为语文教师的责任感忽然爆发?
我对电话那头的张达明说,这个长篇小说大概有二十五万字,太长了,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有什么用吗?
张达明没有回答我有什么用,他说,梗概就可以,三五句话,你,总结一下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那所三流大学的课堂,他站在讲台上,指着坐在最后一排的女生问,《诗经》的古称又叫什么?你,回答一下吧。
他的问题太简单了,后来他才告诉我,他只是用以试探,因为女生的面容他并不熟悉,他不能确定,她是不是他班里的学生。
四
张达明很少冲我发火,不不,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冲我发过火,我说过,他是一个很知道克制的人。我们通了大约半个小时电话,我试图告诉他我的长篇小说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就像在课堂上回答他的问题。我说,女主人公是个职场女性,她在处理家庭与工作关系时,遇到一系列麻烦,反映当代城市女性的生活困境吧……我承认我说得十分概念化,没有情节,更没有细节,我甚至没有提及小说是有男主人公的,因为我不想让他听出来这又是一部言情小说。他有些不耐烦,好了不用说了,那么,你写一段文字给我吧,故事梗概。焦点
我说你又不是出版社编辑,要故事梗概做什么?他回答,我是一个语文老师。
可我不是你的学生,我脱口而出。
他沉默了几秒钟,好吧,你在外面注意安全。
挂断电话后,我想起来,自打我说要出门闭关,他自始至终没问过我要去哪里闭关。当然,这是我们一贯的相处模式,我们生活在一起,却保持着距离,张达明认为这是对我的尊重,而我,似乎从没有认真想过,我是否需要这样的尊重。
已是晚上八点,后院里寂静无声,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停止战争,两人大概都离开了。我打开房门,走到一棵冬青树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吵架的人不在,可他们相骂的余音还在我耳边震荡,那才是真正的夫妻间的吵架吧?直接、爽快、名正言顺,因而令人愉悦。我和张达明,我们从来没有吵过这样的架,这让我感到有些遗憾,以及,莫名的庆幸。我和张达明的关系,不允许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吵架,我们保持着最起码的体面,以维护我们脆弱而又并不十分体面的关系。倘若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经受无数场恶语相加的吵架,就像老板和老板娘那样,会不会,那就是另一种灾难?
我抬头看了一眼混浊的夜空,没有星斗,也没有月亮,但能听见远处的海浪声,接踵而至的哗——哗——声。我决定出去走走,去看看冬夜里的海。焦点
海边的夜晚,温度并不低,但是有风,风不断送来凛冽的寒意。我套上连帽羽绒服,出客栈,沿着石阶登上海堤。沪杭公路上,每二十米就有一盏路灯。海堤的内侧,是数十家海鲜餐馆,门口的灯箱以及稀疏的彩灯闪烁,让外侧的大海显得格外阴沉黑暗。我听见海浪轰响着扑来,却看不见海浪究竟从何而来,又飞扑到了哪里。举目眺望大海深处,一片漆黑的底色上,一大一小两艘渔船在弥漫的夜雾中影影绰绰。更远的远处,有一盏航标灯,每隔五六秒闪一下,像一个瞌睡的值夜人。除此以外,就是一片黑。
夜里的大海真没什么好看的,我想调头去老街走走,也许可以找一家生意寥落的酒吧消磨时光。正想转身,忽然看见一道微弱的光柱从大渔船身上扫过,光柱滑动着,又扫向小渔船。两艘渔船上都没有灯光,应该没有人,会不会是赶海人正打着手电捡海货?这勾起了我的兴趣,也许,我可以跟着最后一个渔村的渔民赶一趟夜海?
赶夜海,当然是个好主意。我从来不是个胆小的娇弱女子,我因此也很难成为一个躲在男人背后的女人。也许,在张达明看来,我是不合格的。但此刻没有张达明,没有一个人用他无所不在的沉默监督着我。我紧了紧羽绒服,拉起帽子,兜住脑袋,沿着海堤,追着若隐若现的光柱,向渔船停泊的方向走去。焦点
沿着沪杭公路走了大约一百米,出现一条深入滩涂的岔路,大约一米多宽,岔路的前方,是停泊在黑暗中的渔船。我没有犹豫,一脚跨上岔路,行进了大约五十米,出现一条更小的岔路,仿如田埂,两边都是滩涂泥浆,尽头就是两艘渔船,距离我此刻的位置大约二十米。与庞大到无边无际的黑暗相比,二十米是极短的距离,渔船已经近在眼前,层层叠叠的海浪声涌来,又退去,它们轮番进攻着我的听觉神经。天和海都是黑的,混沌一片,狂妄的风推着海浪轰响着刮来,刮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开始犹豫,要不要走上更小的岔路,完成最后二十米,到达那两艘渔船的位置,哪怕是伸手触碰一下渔船的外壁?正要抬腿迈步,却见手电光柱又出现了,在二十米开外滑动,光柱渐渐变亮,然后,我听见脚步声,咕滋咕滋,像是一个穿套鞋的人正踩着泥浆走来,穿透风浪声,越来越近。
我向着脚步声的方向望去,一个黑魆魆的身影,一摇一晃,手里拎着一个桶状容器,光柱在黑影前面闪跳。我还听见渐响的哼歌声,今天是个好日子……老歌老调的,情绪很欢乐,并且,是我熟悉的声音,嗓子眼儿里饱含着一口浓痰,是老K,没错。黑影渐渐变大,几乎走到我跟前时,忽然大喊一声,啥人?焦点
他那一嗓子,把我吓了一跳,但我知道,是我先把他吓了一跳。我赶紧撸下兜住脑袋的帽子,齐耳短发瞬间被风吹得满头乱飞,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起来,老K的正式称谓是徐老板,海市蜃楼的老板娘这么叫他。我说,是徐老板吗?我来散步,没想到会遇见人。
手电光柱射向我的面门,我眯起眼睛。他应该认出了我,因为他改用了像第三国语言一样的普通话,竟是呵斥,夜里出来做啥?有毛病啊!然后扭身指着身后的两艘渔船说,那里有鬼,信不信?你可以去看看。说完从我身侧擦过,向着沪杭公路方向咕滋咕滋地走去。
我来不及收起张大的惊恐的嘴巴,两艘渔船在喧嚣的海浪声中沉寂着,因为离得近,船体显得特别庞大,外倾的船舷几乎要覆压到我身上。果然,没有灯光和人迹的渔船,很像某部恐怖电影里的场景,船舱里也许装满了冤死的灵魂,殉情的渔家姑娘,永远等不到出海归来的男人的寡妇,渔霸的恶灵……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拔腿追赶前面的人,徐老板,等等,我跟你一起走。
从第二条岔路回到第一条岔路,再回到齐刷刷亮着路灯的海堤,老K始终没说话,他走得很快,呼哧呼哧喘气。我快步跟着他,低头看他提着的红色塑料桶,桶里是一堆海洋生物,几只奄奄一息的小螃蟹,还有一摊摊破抹布似的八爪鱼。我猜得没错,他去赶海了,我指着塑料桶和他搭讪,徐老板,这些都是你捉的吗?焦点
他鼻子里发出一声嗯。我继续问,那,徐老板是金乌嘴渔村的村民吧?
他没有回答我,却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哼!
他如此冷淡,却挡不住我的好奇。徐老板,你说那两艘渔船上有鬼,那你晚上去赶海,就不怕鬼吗?
他突然扭头,看着我,咧开紧闭的嘴,嘿嘿一笑,那些鬼是我养的,我怕什么?
我倒退一步,拉开与他的距离,同时,脖子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为了掩饰恐惧,我主动和他开起了玩笑,你不养鱼,倒养鬼,那你是鬼王了?
他断喝一声,鬼王是阎罗王,懂不懂?不懂就不要瞎讲八讲!
他凶横的样子,倒是全没了适才的鬼里鬼气,只是,他太过变幻莫测的态度,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刚好已经走到“海市蜃楼”的招牌底下,我说我到了,谢谢你陪我走回来。老K忽然提起手里的塑料桶说,刚捞的海货,准备自己吃的,你要不要?
我吃了一惊,慌忙摆手,不不,你辛苦捉来的,我不能要。
老K笑了,这回笑得竟有些憨厚,我要是想吃,哪天吃不着?你拿去,让老板娘给你炒炒,很鲜的。
没想到他竟是个热情的人,这倒让我不好意思推辞了,那,好呀,不过我要付钱的,你收点钱吧。焦点
老K抬起浮肿的厚眼皮看了我一眼,钞票那是要收一点的,不能让我一晚上白干对吧?说完,他把塑料桶放在地上,站定,给自己点了一支烟,猛吸两口,喷出一团烟雾,然后皱着眉头,痛下决心一般说,五百块,全部拿去。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这样小半桶海货在市场上卖多少钱,无论如何,五百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可是,据说在旅游景点,倘若你和摊贩说好了价,那就一定要买下来,不买的话,你就会被骂、被打,甚至被刀子捅……这么一想,我就不敢说不要了,我费神找了个借口,可是我没有东西装啊!算了,你留着自己吃吧。
他再次咧开嘴笑起来,露出两排黄烟牙,桶送给你。说着很熟练地拿出手机,点开支付宝,亮给我一个收款码。
我知道我受骗了,但这是在他的地盘上,我不敢造次,于是掏出手机,瞬间,五百元钱从我的手机跳进了他的手机。他拎起桶递给我,扭过头,向海堤内侧的老街走去。我看着他踩着一双黑套鞋的背影,矮壮的身材,深蓝色外套,右手握着关闭的手电,左手甩啊甩,甩出一路狡黠和得意。那会儿,我很想给张达明打个电话,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半小时前我们刚通过话,但此刻,我忽然有种想对他一吐为快的欲望。可是我担心他正在下围棋、打桥牌,倘若打电话给他,很有可能我会听到一串答非所问、不明所以的呓语。我拿出手机,想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给他发一条微信。我脑中想的是:我刚失去了五百元钱,但我发出的是另一句话:你的内裤在卧室衣橱下面的第二个抽屉里,记得洗澡前拿进浴室。焦点
……
(全文见《清明》2022年第3期)
焦点娱乐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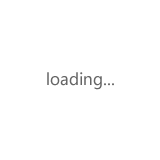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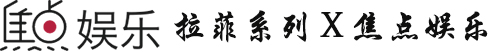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