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平台登录发布:
干了一辈子工作的人,会先后有许多同事,有男同事,也有女同事。随着时间水一样逝去,多数同事早已被淡忘得无影无踪,不可寻觅。却有少数同事,清晰的形象不时在脑子里闪回,让人难以忘怀。既然老也忘不掉,总有其原因,有值得回忆的地方。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写作的人,我难免在自己的记忆里找来找去找人物,讨来讨去讨生活。当有的同事在我的回忆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请自来时,把他们排除在外,忽略不计,是不是有些舍熟求生呢?是不是有些可惜呢?
好吧,我这次就写一写我的同事,一位多年以前的女同事,她的名字叫汪莹丽。
我第一次见到汪莹丽时,她还是一个刚从农场回到矿区的知识青年。那时我从农村到煤矿参加工作不久,正在支架厂里当工人。支架厂是新建的厂子,就地挖坑采石头,用地炉烧水泥,打成钢筋水泥支架,运到井下代替木头支架支护巷道。厂里只有一个茶炉房,干部和工人们喝开水,都是提着水壶或暖水瓶到茶炉房里去接。定时供应生水的一只水龙头,也是安在茶炉房里。厂里有的女工,会端着自己的搪瓷盆去那里接水洗衣服。我就是有一次在排队等着接开水时看到汪莹丽的,当时她正端着多半盆子泡着衣服的清水,从茶炉房里往外走。厂里的女工不多,我知道所有女工的名字。这个女青年是谁呢,我以前怎么从来没见过她呢?焦点平台注册
女青年大概感觉到排队等着打开水的人都在看她,她低着眉,谁都不看,只看着自己盆里的清水,径直向外走去。都处在青春阶段,男青年对女青年是敏感的,我很想知道这个女青年是谁。我很快就从工友口中知道了,她叫汪莹丽,跟她妈一起住在工厂后面的家属区里。矿务局有一些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还有一些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在厂里进行劳动改造。汪莹丽的妈妈是在抗战期间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不知是何原因,也从矿务局机关下放到我们厂,放在劳动改造之列。那两年,矿区职工子女下乡插队或去农场锻炼告一段落,开始被分期分批召回矿区参加工作。汪莹丽参加工作不在我们厂,她被分配到矿务局党校当讲解员。党校里办有阶级教育展览馆,展览模仿四川《收租院》的泥塑形式,塑造的是旧社会的矿工在地狱般的井下受苦受难的形象,以对现在的矿工进行阶级教育。汪莹丽的老家在河北,可能因为她家乡的人说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汪莹丽的普通话说得好一些,就得到了一份只动嘴就可以挣工资的工作。她当讲解员,不算是当干部,但与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工人又有区别,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以工代干,说是有些人是工人身份,做的是干部的工作。汪莹丽等于一参加工作就跨越了体力劳动阶段,在向脑力劳动者靠拢。汪莹丽初中毕业于矿务局中学,有不少男同学和女同学。她的那些同学绝大部分被分配到矿上或厂里的基层单位当工人,只有她和极少数同学,才走上了矿务局的“上层建筑”,从事以工代干的工作。这样她就与绝大多数同学们拉开了距离,体现出她所处地位的优越。焦点平台注册
我对汪莹丽加深了印象,源自她对我的一次拒绝。不是拒绝别的,是她拒绝我看一场电影。我有一位老乡,在矿务局电影队当放映员。有一天下午,那老乡悄悄告诉我,晚上要在矿务局党校的小礼堂放一场用于内部批判的电影,电影的名字叫《早春二月》。当时的文艺生活单调得很,不是看样板戏,就是翻来覆去地看那几部老掉牙的黑白电影。矿务局机关的干部大概也耐不住单调和寂寞,就以“批判”的名义开小灶,看一些普通观众看不到的电影。我曾听人说过,《早春二月》是一部根据柔石的小说改编的表现爱情生活的电影,由著名电影明星孙道临和谢芳主演,那是相当精彩。这样的电影让人无法拒绝,我渴望能看到这部电影。在还没有看到电影以前,我已经开始准备回头向工友们炫耀,心里稍稍有些激动。天刚黑,我见矿务局的机关干部一个接一个分头向党校走去,他们互相之间不打招呼,更没有成群结队,都是单溜。他们接到的是秘密通知,采取的是秘密行动,显得都有些神秘。党校大门口是两扇大铁门,右侧的大铁门上还开了一扇小铁门,大铁门关闭了,只开着一次只容一人进出的那扇小铁门。小铁门外面的门灯下立着一个把门的女青年,女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汪莹丽。看见她,我心中一喜,想到我见过她,她应该会顺利放我进去。可我刚走到小铁门门口,她手一伸把我拦住了,问我:“你是谁?你不能进!”焦点平台注册
我向她解释说:“我在矿务局政工组帮助工作,帮助筹备即将召开的矿务局共青团代表会议。电影队的放映员是我的老乡,是他让我来的。”
“那也不行,我不认识你!”
我知道看这样的内部电影不是凭票,而是凭脸,汪莹丽不认识我这张脸,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电影大概快放映了,这时我看见矿务局办公室的周主任匆匆走了过来,他举手对汪莹丽打了一个无声的招呼,向小铁门里迈去。我认识周主任,周主任也认识我,我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样,赶紧喊了一声“周主任”,意思是让周主任跟汪莹丽说一声,放我进去。让我大为失望的是,周主任只回头看了我一下,连一句话都没说,就自顾自地进去了。周主任的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我就认识了一个人的品性。焦点平台注册
看不到电影,我还是不甘心,站在党校门口不愿离去。我对汪莹丽说:“你不认识我,我可是认识你,我在支架厂里见过你。”
周主任不搭理我,也许更坚定了汪莹丽拒绝我入内的决心,她说:“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你什么都别说了,说什么都没用,我说了不让你进,你就是不能进。”
这个汪莹丽,真够死心眼儿的。我说了一句“真遗憾”,就悻悻地走开了。
团代会开过之后,瘫痪了多年的团委又重新恢复了共青团的活动。因我参加了团代会的筹备工作,原本可以留在团委当一个干事,可因为我当工人还在试用期内,需要回到原单位转正、定级,就回到了支架厂继续当工人。
煤矿上会挖煤的人总是很多,会动动笔写点儿东西的人却很少。因为我喜欢在业余时间写点儿小东小西,在支架厂的石坑里又打了一年多石头之后,我被调到了矿务局政工组下属的宣传组工作。矿务局有一座新建成的煤矿要投产,宣传组决定创办一份《矿工报》,将矿井投产作为喜讯加以宣传。办《矿工报》得有编者,于是宣传组的领导就把我调了过去。此前因恋爱的事,厂里有人说我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把我狠狠整了一通,几乎开除了我的团籍。是宣传组的领导把我从困境中拉了出来,使我的命运从此开始有了转折。知恩感恩,多少年来我一直对那位宣传组的组长心存感激。焦点平台注册
在编《矿工报》期间,有一天我收到了汪莹丽寄给《矿工报》的一篇稿子,是一首短诗。我认识汪莹丽,但我绝不会因为她曾拒绝我看电影,我就拒绝发表她的稿子。相反,我欢迎她给《矿工报》写稿子。加上她的稿子写得还可以,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她,准备采用她的稿子。汪莹丽很高兴,多年以后她告诉我,那是她所写的稿子第一次变成了铅字印刷品。给她打电话时,我顺便告诉了她我的名字。她说“噢噢,知道,知道”。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也许是那次她拒绝我看电影后向别人打听到的。
过了一段时间,政工组所属的组织组和宣传组分开,成为两个部门,分别叫组织部和宣传部。我当然被分在宣传部,一边继续编《矿工报》,一边兼搞对外新闻报道工作。党校办的阶级教育展览馆时兴了一阵子,大概该受阶级教育的都受过了一遍,就不大时兴了。展览馆虽说没有关门,但里面矿工受苦受难的连组塑像已无人参观,变得冷冷清清,有些阴森。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了讲解任务的汪莹丽就被调到了矿务局宣传部,成了我的同事。我毕竟比汪莹丽早到宣传部工作,部长给汪莹丽安排的工作任务,是让她跟着我学习写对外新闻报道。这同时也是部长给我布置的新的工作任务,按当时流行的说法,叫以老带新的“传帮带”。这样一来,我和汪莹丽的同事关系就是一对一的同事关系。我们两个在宣传部见面时,脑子都难免闪现在党校门口关于看电影的那一幕,但谁都不会提起,那一幕像是某个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焦点平台注册
蜜蜂采蜜,必须到有花儿的地方去。在煤矿写稿子,就必须到挖煤的地方去。我和汪莹丽如果老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待着,喝喝茶水看看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轻松倒是轻松了,可拿什么写稿子呢?于是,我就时常带着汪莹丽到下面的煤矿去采访。矿务局管着六座煤矿,有的矿在东边,有的矿在西边。比较近的煤矿离矿务局只有几里路,比较远的煤矿离局机关却有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我和汪莹丽怎么到矿上去呢?比较近的矿,我们就沿着运煤的公路或运煤的铁道专线走着去。比较远的矿呢,我们只能搭运煤的敞篷大卡车过去。那时的司机属于吃香阶层,都牛得很。我们站在尘土飞扬的路边,往往要招好多次手,才能叫停下一辆卡车。司机的驾驶室里只能坐一个人,我都是让汪莹丽坐到驾驶室里去,我翻过车帮,站到后面的车斗子里。只要是运煤的卡车,不管车斗子里装没装煤,车一旦跑起来,车斗子里就煤尘飞扬,飞蚊一样打在我脸上。不记得有多少回了,我们只要搭运煤的卡车去矿上,我都像下了一次矿井一样,脸上、耳朵里、脖子里,都沾了一些煤尘。每回下了车,汪莹丽见我脸上沾了煤,都对我不好意思地笑笑,显得有些抱歉。我们去矿上带的东西很少,我背一只褪了色的黄色军挎包,里面装的是笔记本和稿纸。汪莹丽提一只灰色的人造革敞口手提袋,里面装的无非也是采访和写稿所用的文具,反正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带过洗漱用品和化妆品。矿上那时候没有免费的招待餐,我们在矿上吃饭,都是自己花钱和粮票买饭票,去职工食堂排队打饭。每次采访结束,我都没让汪莹丽写稿子,还是我自己动手写稿子。稿子写完,我顶多让汪莹丽抄写一遍,我想让她通过抄写,知道新闻稿子应该怎样写。稿子在报纸上发表时,都不署作者的名字,不管谁写的,也不管多少人合写的,只署一个“本报通讯员”就完了。那时写稿一律不付稿费,更不存在稿费分配问题。焦点平台注册
说是以老带新,我的岁数并不大,才二十三四岁。我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汪莹丽是1969届的初中毕业生,她比我小两岁,也很年轻。两个青年男女,时常在矿务局机关同出同进,下矿时一路同行,在那个处处充满火药味的斗争年代,别人会不会有什么看法呢?会不会引起别人的议论呢?不会的,我相信不会的。我们二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甚至有些互相戒备。根本的原因在于我那时已结婚,是有了妻子的人。我妻子和汪莹丽是什么关系呢?她们是矿务局中学的同学,我妻子比汪莹丽高一年级。而且她们还一起在矿务局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唱过歌跳过舞,曾经是宣传队里的同事。从资格上说,她们是煤矿职工的“家生女”,至少也是煤矿职工的第二代。作为一个从农村被招工进矿的青年,我只是一个后来者,或者说是一个闯入者,先入为主的她们,有资格对我进行审视和评判。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原因是,我和妻子的恋爱经历了一些磨难,闹得妻子的同学们都知道了,汪莹丽当然也会知道。汪莹丽极少在我面前提到我妻子,我理解这是她对我的尊重。焦点平台注册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汪莹丽也参加了。因她上初中时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知识基础差得太多,没能考上。我没有参加高考,一是我已经有了孩子,二是对高考缺乏自信心。等恢复高考头一年的作文题目出来时,我有点后悔,觉得就那个题目而言,我能写一篇不错的作文,说不定能得高分。还说不定因为作文写得好,我有可能考上某所大学的中文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会一旦错过就永远错过了。汪莹丽考大学不成,开始跟着收音机里的电台广播上电大。我没有上电大,我愿意在实践中学习。有人劝我,说上电大可以拿到大学文凭。我没有动心,对拿文凭不感兴趣。再加上我家没有收音机,没有条件天天跟着收音机听课。焦点平台注册
汪莹丽岁数不算小了,有人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我不知道别人给她介绍了多少个对象,反正她一个都没看上。全矿务局范围内的男青年似乎都不在她找对象的视野范围之内,有人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连跟人家见面都不愿意,说:“呀,不行不行!”某矿团委有一个青年看上了汪莹丽,给汪莹丽写了一封求爱信,趁汪莹丽不在办公室的时候,把信偷偷塞进汪莹丽办公桌的抽屉里。我和汪莹丽在一个办公室,那个青年往抽屉里塞信的时候被我看见了。汪莹丽办公桌下面的抽屉是上了锁的,但抽屉上面有一点缝隙,那个青年是通过缝隙把信塞进去的。对那个青年的情况我知道一些,他求当团委书记不成,受到刺激,出现了精神分裂和不能自控的状况。他的主要表现是以团委书记自居,喜欢参加各种会议,听说哪儿有会议,他早早就到了会场。有些群众性的大会,他参加就参加了,没人管他。有些不该他参加的小范围的会议,他一去会议室,人家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赶了出去。除了参加会议,他就提着一只灰色人造革小提兜四处游荡。他多次游荡到我们宣传部的办公室,圆圆的大脸上带着微笑,一待就是半天。等汪莹丽来到办公室时,我告诉她,那个青年往她抽屉里塞了一样东西。汪莹丽了解那个青年的情况,她曾以开玩笑的口气,把那个青年喊作书记。也许正是因为她把那个青年喊作了书记,那个青年误以为汪莹丽对他印象不错,就向汪莹丽发起了求爱。汪莹丽打开抽屉,只把求爱信瞅了一眼,就像是受到了莫大侮辱一样,气得脸色发白。她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把信撕成两半、四半,扔进脚边用铁丝编成的废纸篓里去了。她犹不解气,拎起废纸篓向门外走去。我估计她是要把撕碎的求爱信倒进厕所的垃圾堆里去。回过头来,汪莹丽对我说,希望我不要对别人说这件事。我让她尽管放心。焦点平台注册
我也曾给汪莹丽介绍过对象。我觉得自己并不擅于为别人介绍对象,似乎天生缺少这方面的才能。可眼看汪莹丽的年龄越来越大,眼看她的同学们纷纷结婚并有了孩子,我觉得我有责任为她介绍一个对象。我给她介绍的对象是省日报社工商编辑处的一位姓苏的编辑。我和汪莹丽时常去报社送稿子,我们认识苏编辑,苏编辑也认识我们。苏编辑很有才华,他不仅通讯报道写得好,报告文学也写得极有文采。他父母都在北京的新闻单位供职,他一个人在河南工作。他岁数也不小了,比汪莹丽还大两三岁,不知是何原因,他一直没有结婚。我想,把他介绍给汪莹丽是合适的,应该能够符合汪莹丽找对象的标准。我没有直接对苏编辑说,而是通过苏编辑的一个同事,先探听一下苏编辑的意思。我也没有先跟汪莹丽说,倘若苏编辑有意跟汪莹丽谈一谈,我再跟汪莹丽说明也不迟。我探听的结果是,苏编辑没对汪莹丽做过任何评价,只说他的父母正准备把他调回北京工作,他就不在河南找对象了。多年之后,调回北京工作的苏编辑因写热点问题报告文学和电视专题片,成了炙手可热的知名作家。这时候,我才对汪莹丽提起,我曾想过给她介绍苏编辑。汪莹丽说:“人家是大地方的人,哪里看得上我们小地方的人呢!”焦点平台注册
出人意料的是,我比苏编辑还先一步调到了北京。我先是一个人在北京帮助工作,一年后就调到了北京。虽说调到北京工作,我却没走出煤炭系统,是在煤炭工业部所属的一家《煤矿工人》杂志社当编辑。同时,我妻子和女儿的户口也迁到了北京,我们全家在建国门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定居。如此一来,我和汪莹丽多年的同事关系就终结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以前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记一笔,请允许我简略补充一下。大约在1976年的春天,我被借调到省里的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写材料。矿务局宣传部和矿务局党校的部分工作人员,临时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要去上海的工厂学习人家组织工人理论小组的经验。学习小组赴上海,需由省里相关部门开具介绍信才行。他们开不到介绍信,就找我帮忙。我在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职责跟办公室的秘书差不多,开介绍信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明白矿务局的那帮人打的是学习的幌子,外出旅游才是真。于是我跟他们讲了一个条件,说让我帮助开介绍信可以,我得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学习。他们不能拒绝我,只好同意让我跟他们一路同行。学习小组包括我一共六个人,五男一女,那唯一的女同志就是汪莹丽。在十多天时间里,我们先后去了南京、上海、杭州,还拐到了九江,登上了庐山,玩得十分尽兴。我们从九江乘江轮去武汉时,坐的是夜行船。我喜欢江风春水,夜里一个人抱了被子到舷窗外的甲板上去睡。没人干涉我的出格行为,仰脸躺在甲板上,我看着天上的星光,听着长江水东流的声响,竟想到了“浪漫”这个词,给我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更让我难忘的是,天将明时,有人从船舱内向外泼洗脸水,一下子泼到了我头上,把我从“浪漫”的睡梦中惊醒过来,顿时变得有些狼狈。这一幕刚好被早起的汪莹丽看到了,此后,每每提及那次旅行,她都会把别人向我泼水的事当笑话说。焦点平台注册
接着前面被自己打断的话说,我调到北京工作不久,汪莹丽也离开了矿务局宣传部,通过应聘调到《郑州日报》报社工作。我想,正是因为她在矿务局宣传部期间写稿子打下了底子,积累了经验,才顺利地走上了新的更高级别的新闻工作岗位。焦点平台注册
那些年一切都在发生变化,而且是快速变化。比如说,以前各个单位都是一潭死水,在死水里,是鱼你伏着,是龙你也得伏着。变成活水之后呢,龙很快腾起来,鱼也变得活跃起来。再比如说,以前各个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一副扑克牌,如今扑克牌在盒子里装着,早就不洗了。形势的变化使牌重新洗过,重新组合,不管大鬼小鬼,还是小三小四,都在发挥作用。拿我原来所在的矿务局宣传部来说,有的人调到市里当某区的区委书记去了,有的下矿当矿长去了,有的给市政府的领导当秘书去了,有的到学校当老师去了,也有的下海做生意去了。只几年时间,我在宣传部共同工作的那帮同事纷纷离开了原单位,各奔东西,各奔前程,走得一个不剩。所谓同事关系就是工作关系,没有了工作关系,同事关系随之不复存在。一般来说,当人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建立起新的同事关系,跟过去的同事就很少联系了,彼此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拿我自己来说,自从1978年春天调到北京工作,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有的同事一次都没有联系过,不要说见面了,连电话都没打过一个。想起往事,我也很想念他们,很想和他们说说话,或见见面。可我的想念只停留在想念的层面上,想想就过去了。我想,我主动跟人家联系,也许会打扰到人家的生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有人说世界很小,远在天边的朋友都可以见到;有人说世界很大,离得并不远的朋友却很难见到。我说不清这个世界是小还是大,反正由于空间的原因、时间的原因,还有心理的原因,我和有的同事也许这一辈子都联系不上了,彼此存在跟不存在差不多。焦点平台注册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几十年来,我一直跟汪莹丽保持着联系。我们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很频繁,都是在过年过节时互相打电话问候一下。我们都还在做新闻工作,虽然不是同事了,但仍然是同行。既然是同行,共同的关注点和共同的语言就会多一些。另外,我在做新闻工作的同时,业余时间还搞点儿文学创作,每出一本新书,我都会寄给汪莹丽看。我们写了东西,总希望有人读。但我常常不知道自己作品的读者是谁,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所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读者。除了我妻子之外,有一个读者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汪莹丽。汪莹丽读了我的小说不但有及时的反馈,有时还能指出某篇小说的生活原型是哪位。这样的读者是难得的,她不仅可以让我清楚地知道读者是谁,了解读者的层次,还可以激发我持续写作的积极性。这样的读者哪个作者不需要呢,哪个作者不愿意和这样的读者保持联系呢!焦点平台注册
我所在的新闻单位面向全国,外出采访的机会很多,每年去的地方也不少。每次路过被称为铁路交通枢纽的郑州,或在郑州停留,我都会与汪莹丽联系一下。是的,我很少与别人联系,只与汪莹丽联系。在我的心目中,汪莹丽和郑州几乎成了一个同义语,汪莹丽代表着郑州,郑州也代表着汪莹丽。我到了郑州一趟,如果不和汪莹丽联系,差不多等于没到郑州。有一次,我到郑州参加一个由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召开的影视创作座谈会,开会的地方正是我原来所在矿务局的驻郑州办事处。一到办事处住下来,我就给汪莹丽打电话,说我到郑州了。我们刚说了几句话,汪莹丽就要我中午饭别吃会议餐了,她请我吃郑州的羊肉烩面。我们在矿务局宣传部一块儿工作时,多次趁往省报送稿时一起在郑州吃羊肉烩面,她知道我爱吃那一口儿。我说那好吧。中午时分,我们在汪莹丽指定的一家羊肉烩面馆里见了面。季节是初夏,路边绿化带里的月季花开得正盛,在阳光的照耀下,每一朵月季花都像是燃烧的火焰。面馆门前撑起了一些大伞盖的太阳伞,太阳伞下面放有餐桌,有的食客嫌面馆里面太热,就在太阳伞下面吃烩面。汪莹丽嫌外面过往车辆太多,声音太嘈杂,影响说话,我们还是在面馆里面找一个人少的角落坐下了。除点了两大碗烩面,汪莹丽还点了两瓶啤酒和两盘下酒的凉菜。在烩面还没端上桌之前,我们先喝一点啤酒。我们喝了两口啤酒,汪莹丽用河南话叫着我名字的后两个字说:“我还欠你一场电影呢,哪天有机会我一定请你看一场电影。”焦点平台注册
我知道,她说的电影指的是《早春二月》。
焦点娱乐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我说:“现在新电影那么多,想看过去的老电影恐怕很难了。”
她说:“是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一旦错过机会,想再找回来就难了。”
汪莹丽从电影说到“许多事情”,我听出了她的话后面的话,我觉得她把话说远了,也说重了。我的敏感和自律要求我不能顺着她的话说,如果顺着她的话说,有可能会落入男女之间的俗套。于是我说:“咱们不说这个了,喝酒喝酒。”
我听说汪莹丽终于找到了对象,终于结婚了。她没有主动对我说起她丈夫,我也没有问她。她要是愿意说起她丈夫,我倒愿意听一听。她不主动说,我不便多问。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问起她的丈夫,倒显得我过于敏感,多心,好像故意岔开话题似的。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仿佛话不由己,一开口还是岔开了话题。我说一到烩面馆,就想起了许多往事。我讲的一件往事是,我在北京帮助工作期间,有一次回矿务局,妻子到郑州接我。妻子接到我,我们就到二七纪念塔旁边的一家烩面馆吃烩面。烩面占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一边吃面,一边说话。等我们吃完了面,妻子才发现她挂在长条板凳一头儿的提兜儿不见了。提兜儿装的东西有钱包,还有一本她没有看完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不用说,一定是小偷见我们两口子说话说得有些忘了身在何处,就把妻子的提兜儿顺走了。汪莹丽没说起她丈夫,我却说起了我妻子,也就是她的同学。我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拿妻子抵挡什么,只是在不知不觉间就说到了妻子。焦点平台注册
汪莹丽也没有顺着我的话说。热气腾腾的羊肉烩面端上来了,太热,我们没有马上吃。汪莹丽问我:“那次我不让你看电影,你临走时说了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我摇头说不记得了。
“我还记着呢,你说的是‘真遗憾’。因为这句话,我一下子记住了你。全矿务局那么多年轻人,只有你才会说出这样的话,当时我就觉得,你和别的人都不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汪莹丽竟然还记得我当年随口所说的一句话。我相信汪莹丽的记忆不会错,就我的性格和习惯而言,我应该会说出那样的话,面对一个女孩子,也只能那样说话。我该说什么呢?我不会再说“遗憾”那样文绉绉的话了,只能夸汪莹丽的记忆力真够好的。焦点平台注册
若搁以往,羊肉烩面上桌后,我的全部注意力会很快集中在烩面上,一口气把一大碗烩面全部吃光,吃得大汗淋漓。可那天我们都有些走神儿,注意力一点儿都不集中,没有吃出羊肉烩面应有的香味。不管是面条,还是粉条,我们都是一根一根挑着吃,一碗面只吃了半碗,就把筷子放下了。
我原来所在的矿务局,属于国家煤炭部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但因行政区划是在郑州市范围内,一些社会性功能也归郑州市管。也就是说,对于矿务局的宣传报道跟我有关系,跟汪莹丽也有关系,我们一块儿去矿务局是顺理成章的事。有一年,某矿举行庆祝建矿五十周年庆典,我和汪莹丽都去参加了。在晚间举行的舞会上,我第一次请汪莹丽跳了舞。汪莹丽说我跳得挺好的。我说刚学的。又有一年,某矿的原煤年产量比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翻了一番,邀我和汪莹丽去给他们写报道。在矿领导招待我们的酒会上,我和汪莹丽都喝了酒。借着酒劲儿,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第一次拥抱了汪莹丽。拥抱汪莹丽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预谋,我把预谋得以实现的功劳推给了酒。我觉得汪莹丽也有预谋,我的预谋是拥抱她,而她的预谋是接受我的拥抱。这样说来,我们迟到的拥抱就不是不谋而合,而是有谋而合。在我们拥抱时,有矿上宣传科的人为我们照了相,之后汪莹丽一再向人家要照片,我知道她是想留一个纪念。尽管当晚喝了不少酒,但我仍不失理性,理性告诉我,拥抱一下我以前的女同事,带有一定的礼节性,同时也是我和汪莹丽交往的一个底线。我绝不会越过这个底线,永远都不会。有人说,连喝了酒都保持清醒状态的男人是可怕的。可怕就可怕吧,反正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得管住我自己。焦点平台注册
我妻子对汪莹丽也很好,她对我与汪莹丽的交往没有任何疑虑。有一次,汪莹丽带着她女儿到北京参加一个外语培训班,妻子热情地安排她们母女住进了我们家。回忆起来,我们到北京几十年,除了我母亲和我妻子的父母,以及我的兄弟姐妹在我们家里吃住过,在我们的同事和朋友里,汪莹丽是在我们家吃住多天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两口子对汪莹丽是多么友好。其实朋友之间的友好是双向的,汪莹丽之所以能在我们家得到特殊的待遇,是她愿意与我们保持友好的关系。听妻子多次说过,她有一个以前和她关系不错的女同学,头天听说她要调到北京工作,妒火中烧,第二天见面把脸一扭,就再不搭理她了。对于这样的人,就算你想跟她保持友好的关系,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焦点平台注册
我和矿务局宣传部的绝大部分老同事都断了联系,不等于汪莹丽和他们也没了联系,汪莹丽和不少老同事都有联系。有些老同事的信息都是汪莹丽告诉我的,谁谁升官了,谁谁发财了,谁谁瘫痪了,谁谁出事了,汪莹丽都会及时告诉我。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宣传部的部长去世了,副部长去世了,新闻科的科长去世了,一位才五十多岁的老同事也去世了。汪莹丽每告诉我一个不幸的信息,都会把逝者妻子的电话告诉我,嘱我打电话向其表示悼念和慰问。同时,每每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和汪莹丽都会不胜唏嘘,感叹生命的短暂,并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
汪莹丽退休后,担负起了照顾她母亲的责任。在汪莹丽年轻的时候,她和她母亲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因一点小事,她母亲曾到我们宣传部大吵大闹,告汪莹丽的状。不承想她母亲到了晚年,她们母女相处得那么好。她母亲九十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能大睡,能吃肉,身体好得惊人。我时常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她晒母亲的照片。在春天的花园里,她母亲在健身器材上锻炼身体。在秋天的阳光下,她母亲坐在室外的椅子上看报纸,竟然连老花镜都不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她母亲作为抗战老战士,得到了一枚国家颁发的纪念章,她把纪念章的照片发在微信上,很为她母亲骄傲。母亲身体好,说明他们家的长寿基因好,汪莹丽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充满自信。我每次看见她,她都身手矫捷,似乎还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说她母亲在向一百岁迈进,她前面的路更长更长。焦点平台注册
说话到了2019年的年底,我的长篇小说《家长》获得了第二届“南丁文学奖”。我去郑州领奖时,因来去匆匆,未及和汪莹丽联系。直到我登上返京的高铁列车,才给汪莹丽发了一条微信,请她谅解。她很快回信,说她看到了我获奖的消息,向我祝贺!因她生病住院了,才没有到颁奖会现场去看我。她在微信的最后说的是后会有期。
汪莹丽生病了,还住院了,这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女同事,我不好意思问她生的是什么病,只是祝愿她早日康复!
没有再收到她的回复。
2020年春节前夕,我禁不住又给她发了微信,说:“都快要过年了,您难道还没出院吗?真让人挂心啊!”
仍未收到她的回复。这让我有了不太好的预感。
整个春节期间,我都没有汪莹丽的任何信息。这不正常。在以往每年的春节,我都会与她互相拜年,互致祝福。在鼠年的春节,我给她打电话,无人接听;给她发微信,不见回复。这太不正常了。焦点平台注册
到了正月初七,也就是2020年的1月31日,春节长假结束,上班的人又开始上班。我实在忍不住,又给汪莹丽的手机上发了微信。这次发微信,我写的是汪莹丽女儿的名字。她女儿很快给我回信:刘叔叔,我妈妈今天上午11点走了。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一下子蒙了,有些头晕。我马上把消息告诉了妻子,说话时我喉头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妻子一听就哭了,她说:“莹丽才六十多岁,她不该走得这么早啊!”
我立即给汪莹丽的女儿回信:“得知你妈远行的消息,我和阿姨心情都很沉痛,阿姨都哭了。深切悼念你妈妈!她那么热爱人生,热爱生活,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好孩子节哀珍重!并安慰你爸爸!”
天还在,地还在,山还在,水还在;矿区还在,郑州还在,汪莹丽却不在了,永远都不在了。汪莹丽是我与老同事们保持间接联系的信息枢纽,汪莹丽一不在,我再也得不到所有老同事的任何信息了。人的存在是相对的,汪莹丽不存在了,在与老同事的联系方面,恍惚之间,我仿佛觉得连自己都不存在了。
好在汪莹丽的手机号和微信号还在手机上保留着,每次路过郑州,我都会想起汪莹丽,都会给她留言:我到郑州了,莹丽您在哪里?又来郑州,莹丽永生……
在天国的汪莹丽也许会看到我给她的微信,可惜她再也不会回复我了。焦点平台注册

刘庆邦,生于河南沈丘农村。一级作家,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女工绘》等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七十余部。《刘庆邦短篇小说编年》十二卷。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南丁文学奖、孙犁散文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等奖项。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韩国、越南等外国文字,出版有七部外文作品集。
焦点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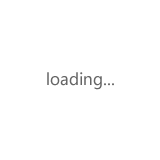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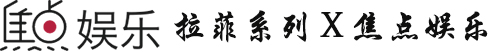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