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平台快讯:
未亡
太太,太太。
双唇紧闭,舌密封于齿内,从脑部神经到声带,轻微颤抖,继而由某处漏出一声。可我不敢大声,仿佛出声只为使自己听到。但她每次都能捕捉到这种声音。
不敢大声是因为太太并不喜欢“太太”这个称呼。她觉得“太太”会让她想起年轻时,那属于小布尔乔亚的称呼。
她有偏见,她厌恶。
我似乎遗传了这种固执与偏见,认为曾祖母这个大词,配不上有趣的她,因此我依然喊她太太。
她倒也惯着我,嘴上说不喜欢太太这个称呼,但在我喊她太太时总会回应。她并不说,哎,怎么了?而是说,发生了什么?接着就用那绵软的手捻我肩头披散的细发。这种时候她总喜欢来一句,男娃娃怎弄个这头型。
太太的手好闻,她浑身散发的那股如露珠般清新的味道,好像全集中于指尖,谁挨到都能沾染一缕。她的手除了有露珠味,还被漂亮的海娜从指间到手腕整个包围,起初是褐色,然后变成红棕色,最后是长久的橙色,好似另外一层皮肤。我生怕被她触碰时那颜色会传染,便顾不得留恋露珠的味道,着急跑开。
太太既不追我,也不喊我,只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有时会因此生气,为什么太太不喊我的名字呢。
阿西娅,你不疼我!我跺着脚叫她的经名。太太斜倚屋门,笑容始终挂在她褶皱丛生的脸上。
天色渐暗,月光悄然自屋檐滑落,清真寺里唤人礼拜的喇叭声悠扬响起。太太说,该礼拜了,礼拜完了该睡了。她拖着影子往屋内去。在大炕上,长袍起起落落,额头上的一颗汗珠沾到拜毡上。月光透过木制的窗棂,打在她身上异常柔和,她从来都如此平淡静美。焦点平台登录
我没见过太太年轻时的样子,哪怕一张照片也没见过。我从出生到开始记事,太太好像一直没有变化。我想知道更多关于太太的事,但我上哪知道去?方圆五里,哪怕整个夏城,都少有人活得像她那么久。
据说有个绰号叫“尕飞机”的祁爷活了九十多,听说他将自己锁在宅院里整整五十年,我们都没见过他。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根溯源,却还是知道了一些事。在太太捻我头发,我逃开,大喊阿西娅的运动中,我从五六岁长到二十五岁,胡须需要每天一剃。太太也一直重复捻我头发,微笑着看我,一日五次祷告后再来寻我的动作。
“几十年前,你的高祖父是个受回儒两重文化熏陶的体面商人。他穿着长衫,向北平城一路进发,到了天津港就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那是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可惜刚过了一年,我父亲拗不过我母亲,催没读完书的我回家成亲。刚出阁的女儿家当教书先生,这在夏城成了千古奇闻,我虽然只是教初小的丫头们学几个字,却就一辈子跟教员这事扯上了关系。”太太拉拉杂杂讲了很多,有时会反复说一段事,有时说到一半又停下。焦点平台登录
回忆混乱且真假难辨,我陷入需要证实却无法证实的困境。甚至有时候觉得太太疯疯癫癫,怕是得了老年痴呆也说不好。明明不知所云,她偏又好似握紧了逻辑,像个坚定的文学家,让我坚信自己是个不合格的读者。
屋外凌乱飞着细碎的雪片,雪沾在我的肩膀和头发上。我看她褪去长袍,卷好拜毡,铺开床,自顾自躺下。她像被谁设定了程序似的,我的想象只能维持她起身到躺下的这段时间,而后我洗净自己,去另一房间晚祷,再躺回她身边。整个过程我加快速度,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但这旅程中,我们如此安静,是两只彼此不闻的冬眠乌龟。
枯河
我醒来时,太太已做完晨祷,坐在窗前翻动泛黄的纸张低声诵念,屋外的雪已重重扑打在窗上。我听到些奇怪的音响。这是冬河的喊声吗?我问。太太说,只有我在念经,赶紧起床洗小净(一种穆斯林礼拜前的仪式,用特定的方法洗手、肘、脸、口、脚等器官),赶紧晨礼,天快亮了。
这些日子我疲惫不堪。本来读的大学就不好,毕业后参加各类考试又一再失利,如今只好在县城里打杂。干的虽只是些端茶送水、整理文档的琐碎事,但比起大学生活,着实累得不轻。这导致我常常忘记祷告时间,其他四次还好,晨祷我实在是起不来。以前睡在太太身边时,我逃不掉,但我想了办法,像几年前离开她上学那样——躲到别处睡觉。太太感到诧异,十几年来已适应睡在她身旁,如今回家了,怎又变了?焦点平台登录
我心肠变硬了。太太说,有信仰的人心肠很软。我质疑她,心硬与信仰没有对等关系。尽管如此,我仍然依恋她的味道。太太是我记得的第一张人脸,在这座小院内,也只有我们两张脸。我曾为此困惑,问号像川流不息的河,却只得到些模棱两可的答案。在答语的尾巴上,太太还要缀上一句,这是真主的安排。
我是固执的人。在太太做着她着迷的事(比如写大字)时,我总能擒住她的几句真话,哪怕它们依旧值得怀疑。我爸呢?我爷呢?怎么就我一个人?我穷追不舍。太太提着毛笔的手略微停顿,墨汁随即浸透白纸,那一团黑墨如鬼似魂。她的笔尖继续滑动,嘴里始终是那句话——殁了,都殁了。她也不是心软的人,用我后来学到的话说就是没有情商。从我小学三年级,老师布置作文“我的爸爸”起,我就开始问她,得到的也是这样的回答。
日常生活中,太太给予我蜂蜜般的爱意,但在这问题上,她冷酷无比。从小到大,从懵懂的“殁了、殁了”,到惊愕、到嘴巴张大,再到重复这问句,我像跟她开玩笑一样。我知道她依旧是“殁了,都殁了”,但我还问,不期待她说别的。有时想起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角力,便哑然失笑。多年来她持续写字的习惯,有时是读书,读那些厚厚的大部头,也读小册子。在我步入中文系大门后,我们也曾就《在酒楼上》是否是鲁迅的好小说而争论。这时的她混乱又坚硬,话很多,但当我岔开话题,重复问她男人们的秘密时,她又继续翻着《呐喊》《彷徨》,赏给我那几个字。焦点平台登录
她的余光已收起,我开始挥动想象的鞭子,有时它抽到爷爷,有时是父亲。爷爷活着的话年纪应该很大了,他是个知识分子,还是革命青年。在抗美援朝热情的感召下,他不顾他母亲的反对,脱下校服穿上军装就去了,上甘岭那几个吃苹果的人里就有他一个。之后他血洒鸭绿江畔,魂归故国;父亲也是遗腹子,他是爷爷早恋的果实,我奶奶怀他时,是个小女娃(这导致她后来可能不是我奶奶了)。他大概也被太太拉扯大,后来成功考取大学,去最大的城市读最好的大学……此时他应该是一个老教授了吧,我这样想着。父亲结婚晚,到四十岁才生了我,而我到现在还找不到对象,原来是遗传。
太太没法进入我的世界,在这虚构的天堂里,我是帝王。当我戴着王冠享乐,抑或遭遇滑铁卢般的艰难时,太太总会攻克我的城堡。她放下手中偏爱的物什,说,我给你讲讲你太爷爷。这并不是我所愿听到的,眼前的人已遥远如历史,又何必再多寻些苦恼,毕竟我丰富的想象力有时会产生负担。可我关不掉她的话筒,她像个会议发言人,一条一条梳理脉络,阐述观点。他要介绍那个高大挺立的人,起初我并不接受,她说。你也知道,我上学上得好好的,非要我结婚,可是只一眼,我就决定了,这是我一生的人,真的,就一眼。太太瞧着天花板,仿佛上面悬着某张脸或记忆的提词器。我说,这有点像电影,哪有那么多一见钟情。不,不是一见钟情,是真主安排好他等我。她说。焦点平台登录
他跟我同岁,照夏城人的看法,我们结婚都晚。第一次见面,他从部队上请了假回来,我虽见过些大场面,但男女之间这种事是头一遭,不免有些紧张,说不出话来。他滔滔不绝地向我热情介绍各种自己的情况,说中学后就不读书参了军,男儿何不带吴钩嘛,说部队里识字的人不多,所以他升得快,现在是团参谋。我吟吟笑着,不敢看他,实际上心里可着急了,要不是害羞,我就瞪大眼盯着他,因为脑子里全是关于他的问题。但我不问,他说得多了,也就乏了,可能意识到气氛有点微妙,他突然说我给你唱首歌。我说好。他说,这歌是听老兵们唱的,前不久他受命接待一个姓范的记者,还给他也唱了。没想到那个范记者听过这歌,早知道就不唱了,蛮不好意思。“骑大马来背钢枪,富户门前要粮饷”“大……姑娘……大姑娘捎在马上,大姑娘捎在马上”。他唱完鬓角全是汗,说自己不会唱歌,但也不知道唱啥,这歌好玩得紧,唱给你当笑话听。看着他的脸红扑扑的,我竟然噗嗤笑了出来。其实我不是笑这歌,笑的是这有趣的人,他比歌有趣。为了缓解尴尬,他竟然唱起兵油子的不正经歌子,没想到我们更尴尬了。但看我笑了,他也笑了,笑得很大声。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冒犯,他至真至纯,想不到这层 ,真是可爱。焦点平台登录
我不知道太太还原那流行于兵痞间的歌谣时,音调是否准确,词对不对。我只是惊叹她的记性,如果这是真的,几十年前的事竟记忆犹新。侧耳聆听,我逐渐被这故事吸引,即便已不知听了多少遍。太太每回讲到这事,总是准确又流畅,既不重复也不停止,从头讲到尾,连贯得让我无法怀疑。大多数情况下,她目光呆滞,但偶尔也射出些五光十色。
再往后,我们成了亲,他就跟着队伍出发了,说是先去陕西,再可能去河南,那里来日本人了,该打。我不像别人,我理解,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我懂。但我心里难受,从我们见面、成亲到他出发,太短了,有时候想想,那光阴短得就像这几十年的光阴。我再没见过他。焦点平台登录
故事结尾显然稍显仓促,我并不满足。当我沉浸于此,想听太太讲之后的事时,她就停了。她说,没了。但这毕竟是我们家唯一能听到的男人故事。从六岁开始,我就知道结局如此,但每次还是不厌其烦地听下去,渴望这次故事能延长些。但她讲这故事,宛若藏了把尺子,精确到毫米,知道哪一秒停下。她说,没了。
我草草完成祷告出门,太太从窗内伸出头,窗框如同断头台。我觉得不吉利,赶忙挥手让她退回。我说,您再睡会,中午回来给您做饭。
雪此刻停了,一径停了几天。雪并未彻底撤退。我踩着它们,咯吱咯吱声变作啪嗒啪嗒,污水已爬上膝盖。路过冬河,不知是结冰的缘故还是怎地,光秃秃如一片沙漠,不时有几根土黄的杂草飞上岸边,夹入过路人的须发。一连几天,我路过河边,没有刻意放大听力,但我的确听得到。从我尚未离开被窝,到跨过全部的冬河,都听得到一阵喊声直击灵魂的触角。我的青筋暴起,太阳穴突突弹跳,那筋脉里的血液翻腾,不曾停歇一刻。我加快脚步,倒不是为了脱离声音,而是体内河流冰凉,急需暖气。求你了,焐热就好,别管它是否吵闹。
替身
此夜,我钻入这块坟区,在一整座山的墓堆下修建房子。从某个傍晚,修到太阳重新飞升。蜷缩于这窄屋内,魔鬼与精灵是否与我同在?我渴望天使守护,与那些欲伤害我的虫蛇鸟兽作战。屋外那些没头发的树在歌唱,它们站得像一列列士兵,催生漫山遍野的雾气,将风与传说输入人身。我只能靠在这张简易床上,任凭恐怖的念头穿梭于汗毛。我如此羸弱,带不来一点点希望。焦点平台登录
午后,阳光白灿灿的,冬天果真要把人榨干。我漫无目的地,在山野上闲逛。也许某刻,我看见了一座坟上长出碗口粗的树,它想钻入云霄?替冢中枯骨申冤抱屈?不清楚。我踩断那些干透的树枝,再用手折成筷子长短,用它点炉子,比什么都烧得快。慢悠悠地往我的屋子走,不经意间又仔细端详这座山。它朴素到只以方向命名——北山。它不高,估计也不厚,只是长,一眼望不到头,大大小小的坟星罗棋布。
零星有几个上坟的人,午祷过后也有新送葬的队伍,那群白帽扛着一块白布,布里是新到的客人。无意打扰他们,我在屋前坐着,跷起二郎腿,任凭寒风呼啸。时不时也玩一会儿雪,拿筷子似的树枝画上一朵两朵的花,期待它们度过漫漫长夜。
我比雪更艰难。暮色初现,我就开始恐慌,那阵喊声混合着山的重量,一同向我压来。
焦点登录:www.sdptzc.com
此夜我遇到了父亲,他戴着眼镜,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刚刚劳动完,要读会儿书。我看见他只有半块影子,他也发现了,在阳光下暴露出癫狂。我想说服他,你来就好,影子不重要。他拿两只手按住腰使劲,像是要把上半身拔出肉体,他说,你不懂。我也看到了祖父,他身披一块龟壳,说这让他温暖。我说重吗,他说冷。我又问,怎么看不到你的腿。他说,你新得像明年的日历,看不到我。焦点平台登录
还有太爷爷,我没找到他。只有一匹白马,它的鬃毛发亮,身白如同树顶的雪。马蹄没戴马掌,身上也没鞍。它后背朝我,时不时晃动尾巴,就是不转头过来,我迈步往前,它也向前奔去。我们的方向一致,却总是你追我赶,有时它追我,我想这下终于可以看到了,你逃不掉。我转头,一下又看到它的尾巴,我又开始追。整整一夜。
醒来时,我大汗淋漓,夜风吹得木门嘎嘎响。往炉内添了块炭,把白天捡来的树枝一并扔进去,喝了口热茶,水壶放回炉子,我又躺下,等待天明。
估摸到了晨祷时间,我站上拜毡。虽然穿着羽绒服,但还有些冷,不由得往炉子走,添炭,再站回去。我长叹一口气,准备祷告。以前我仿若机器人,程序启动,等待完成就好,可今日偏偏多有疑难,念词含糊不清,动作变形,总算磕磕绊绊结束,我坐在炉火旁,直勾勾盯着屋门。
我感觉屋内坐满了人,但每个人又都是我,他们一言不发,互相笃定那就是自己。我转头看看,他们也转头,然后我们直勾勾看屋门。刚坐下时,炉内噼里啪啦,估计是新买的炭质量不好。想着炭,我们也噼里啪啦,在笃定我们就是我们之前。焦点平台登录
天已破晓,晨光降临,它穿透木板,举起小屋。我们开始合体,像一个人似的。该出门走走了,哪怕此刻还有些许晚间的凉意,但白天毕竟是白天,没有什么可以被撞破。开了屋门,我们又后退,是的,我们。又裂开了,我们的界限好像不是白天与黑夜,那昨夜就是起点吗?我们点点头,我点点头。
再一次后退,直到我们沉重如蹄的脚磕到床。床上有点挤,但我们坐了下来,我们等待。
新房
中午单位加班,但我还是请假回了家。一上午我都在想那扇被木框切开的巨大窗户,越想越像某种行刑工具,不吉利,因此生怕太太出什么意外。我担心过头了,回家时,她好好地在择菜。
今天吃扁食。太太说。我看她手里的韭菜快择完了,就洗手和面。好好洗手。她说。您倒是有力气和啊。我答。我们对视一笑。刚出锅的扁食太烫,太太早早拿醋配好油泼辣子,她似乎做好了一切准备。
扁食不是送客时才吃吗?送谁走,是我吗?没人接住我的笑话,她严肃得好像对自己下达了命令,她的无线电静默。我大口吞着,最后一个煮得有点烂,筷子功夫又不好,生生夹了半天,但我没咽下去,不敢咽下去。她说,送我走。焦点平台登录
原以为是玩笑话,直到她说起昨夜梦境。你昨晚睡后,我没睡着,人老了,睡不着。快到晨礼时分,才眯了会,就这一会会,你太爷爷走到梦里来了。他问我,为什么丢下他一个,为什么不陪他。太太的嘴鼓起又复原,我以为她要讲故事。我说,您都没多少牙了,先把扁食好好吃完。她把筷子放下,使劲咽了一口,将口腔清理干净。她说,几十年了,他从没来过,这么匆匆来肯定不简单。我看他,还是以前的样子,我要去陪他。殁不殁是真主定,人定不了,但我活着陪他。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说,我要陪着他。您别开玩笑了,趁身体还硬朗,让我孝敬您,可别让我犯愁。我好似哀号地说。她说,你不懂,你又看不到。我知道肯定拗不过她,没人能改变她。
她往墓区行,我跟着上山。
北山公墓区是夏城唯一的回民墓区,这里不分派别、不分年纪,山路绵延,路旁放满了人。我的家族在山麓处的一块平地上,估计是祖辈中某个有钱人置下的产业,因这地势平坦,送葬不需爬山,又离大路不远,人群来来往往,坟内人也不至于寂寞。起初,我并不知这埋着什么人,小时候太太让我跟族内某位叔叔一起上坟,也仅是面朝群坟,张手为他们祈祷。他们是谁,一概不知。这些低矮的坟堆没有墓碑,没一个名字属于他们。太太说我们不需要,亲人会记得他们活在哪里,亡于何处。现在我起码知道了一个,这有太爷爷。可太太不是再也没见过他吗,里面埋的是什么?太太说,我是再没见过,我也不相信他死了。这是座空坟,里面两个坟坑,一个空的一直留给他,另一个空的,我殁了就钻进去。太太说,你要记住。焦点平台登录
您能活到两百岁。站在隆起的土堆前,我打趣道。真主襄助,真活那么久就不知是不是受罪了。太太答。这有爸爸和爷爷吗?我问。殁了,都殁了。没想到她还是这么说。我猜想这肯定没爸爸、爷爷,他们一个埋入异乡,一个暂停想象。
随后太太划定一块区域,在离家族墓群不远的空地上,她指着黄土地说,就在这修。我说,什么?她说修房子。耳朵与中枢神经各走各的,我哪料到,“活着陪他”是这种陪法。她竟然想住在这。
您没力气修。我说。
你来,你年轻。太太答。
我不会。我说。
我当脑子,你当手。太太说。
一间低矮土屋化装潜入墓群旁。我手足无措,太太倒像指挥官。从木材市场买几根长木头,挖下山上黄土,举起铁锨,和泥,用木制模块做土砖。回民埋人时,先竖着挖坑,再平行于地面,横着掏一个坟,将亡人请进去,洞口用土砖垒上。做砖时,我的脑海飞速游来那些密封人的砖块,不知道我们谁用的砖好。长木头深深插入地面,四根木头上再横上四根,接着用土砖弥合它们的伤口。太太挥起前进的旗帜,旗语说,开扇小窗。焦点平台登录
又淘来一扇成品木门,放两张行军床,架起一块案板,通好炉子烟囱。不知昼夜,一件艺术品诞生。我说,我没经验,这会不会住死人。太太说,住不死。
修好当天,我似乎才从梦中惊醒,说这不行啊。太太说,挺好的。没耽误一刻,我们烧炉子,点燃从墓区捡来的干树枝,烧差不多了,再放炭、烧蜂窝煤。房子变暖很多,阴暗的小屋,没灯没水,但有火苗。屋内摆上一口大水缸,再倒入买来的矿泉水将它灌满。至于为何不直接喝矿泉水,而要有缸,我只能说是太太要求的,我把它归结为某种神秘的仪式感。一切就绪,我像个被扯入阴谋的陌生人,手脚不听使唤就成了从犯。当晚她就要睡那,我说也不急在这一天。于是,当晚我们都睡在了那。
很奇怪,那夜我睡得如此香甜,晨祷时太太摇了我半天都没醒来。那段时间我也没去上班,领导说,你这隔三差五请假,是不是不想干了?想到也不能老靠人家的接济生活,我又开始纠结。白天,我踢着木门思考怎么揍领导一顿,让他别纠结我请假的事。太太说,你上班去吧,也耽误不少时间了。那你咋办?我问。我在这,挺好的。
之后,我没揍领导,又回了单位。每天固定奔波于家、单位、公墓之间,朋友开玩笑,说我怕不是兼职单位工作,专业实际是挖坟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担心老太太,每天买点菜蔬瓜果,提点家里的炭,给她送去。她倒是泰然自若,除了屋内礼拜,一直在那坟边坐着,像极了另一座坟。焦点平台登录
有一次我正往水缸里倒水时,她走了进来。我纳闷,咋了,不守了?她说,今晚你替我守一夜,我回趟家。我以为她终于回心转意,可她又说,就一夜。我这才察觉,自己竟要在这独自待上一晚。她问,你害怕不?我挺了挺胸,看起来像个男子汉。您回去干吗?她说要回家做个草人,晚上她睡觉,白天她礼拜,这坟边要放一个像人的物件。我理解不了她,这坟又不怕虫咬鸟叫,放草人干吗?或许她真到了年纪,器官们已准备歇业,人就疯了起来。我正考虑器官退化还怎么到两百岁时,她就像一朵蒲公英,出门飘远。
我坐在床上,不,我们坐在床上。丝毫没注意门已被推开,直到那偏心的日光灼烧床单,屁股才被点着。我们站起来,双腿战栗,眼中光雾氤氲,而她覆于木门上,封住整间屋子的通路。她似乎充气了一般,像个不熟练的巨人。意识略微清晰,转身望望,曾被我戳开的狭小窗户也未幸免,她的手同样巨大,已捂住那里,掌纹清晰可见。
不要恐慌,那毕竟是她呀。我的腿提我上前,这才发现,她竟握着一根拐杖。我不自觉哇地一声,泪珠直抵胸口。她说,我的娃,你哭啥?你咋拄上这个玩意了?我抢过那老树根做的拐,丢到地上。她捡起来,笑容键还未关,说没事,昨晚走得急,腿疼。我幻想自己已准备好,其实我真没想过,她已老如山顶枯草,微风就能轻易折断。焦点平台登录
我的胸膛被她的头抵住,她的手颤巍巍抬起,准备再捻一次我的头发。此时我才明白,她需要我低下身。她是如此矮小了,活在一只手掌中。N
……
未完,详见《南方文学》2022年第6期
【作者简介:祁十木,回族,1995年生于甘肃河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人民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花城》等刊物,著有诗集《卑微的造物》。作品入选多种选本,曾获未名诗歌奖。现居南宁。】
焦点娱乐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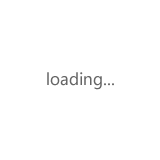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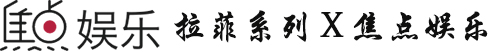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