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注册报道:
一
他,百里湾,要是肯听我的,又怎么会被砸成肉泥?
他嘴里喊着“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就被砸死了。一块大石头追在屁股后面把他放倒。我站在“滴水崖”上方目睹。然后就是草地上人们赶来看见的样子——满地肉渣子。
我第一次看到别人死得这么惨,太超出我对死亡的认知了。他的父母捶胸顿足,哭趴在地,捧着那些染了血迹的百里湾变成的泥沙,不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
我不能告诉别人我如何看见了一切。他们不会相信我。他们说我是傻子。
我站在滴水崖上方看他们如何哭泣,如何一点一滴将百里湾从泥沙和草叶上收集起来,就像收集一些弄脏了的雨滴。
百里湾算是我的朋友。我单方面把他看作朋友。当然,他不是这么看待我的,他也觉得我傻。
他们都喊我“嗨”。嗨,就是我的名字。
我女人——曾经是我的女人——也这么喊我:“嗨!”
我的女人嫁给了别人。我不想知道她嫁给谁。反正她嫁给我一天就跑了。嫌我邋遢,嫌我长得丑还邋遢。她说她闭着眼睛出去就能摸个比我好的。我已忘记她的样子。倒是记得她说过,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我肯定是能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因为我什么垃圾都能忍受。我还以为她是在表扬我。第二天她就不在我的房子里了。是我的父母(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死)告诉我的,她逃走了。我当然知道她逃走了。我亲眼看见。焦点平台
二
他们喊着我的名字说,“你是怎么看到百里湾被砸死的?是不是你故意推下去的石头?”
我说不是,我跟百里湾没有仇。
“照你这么说,那石头还会拐弯?”
我说是的,它会拐弯。
“你不要装傻。”
他们几张嘴一起问,而我只有一张嘴能回答。我很累。他们都是百里湾的亲戚,堵在我门口吵吵嚷嚷一整天。房子没有院坝,他们就坐在门口很窄很陡的檐坎上。我不敢出去。门反锁了站在堂屋中间。天要黑了。我很饿——噢,我像一条夹尾巴狗,快把自己的尾巴夹断了。
“嗨,出来说话。”
“你躲到什么时候我们就等到什么时候,你总要把话给我们说清楚了。”
我快饿死了。百里湾刚刚埋到土里不出三天他们就来质问。就是说,我当时站在滴水崖顶上他们是看在眼里的。
“它确实拐弯了。我看见的。”我试着再解释一遍。
“放你大爷的屁。”
我赶紧往后缩一下脚。
“开门!”
我犹豫一下终于鼓起勇气把门打开。
他们互相看了看,又看我。
“你为什么在滴水崖?”他们挑了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跟我对话。这个人说话的声音我很讨厌。我还没有搬到滴水崖上方的山洞居住的时候,这个人是我的邻居。那时候我们和吉鲁野萨以及雁地拉威,还有眼前这帮人共同住在峡谷河边的村庄。他很聪明。他们都说他很聪明。他在我们那个村子有个外号叫“喜鹊”。人们非常喜欢听他从四处带来的各种消息。吉鲁野萨和他的女人搬离村子以后在毛竹林(跟滴水崖差不多一样糟糕的鬼地方)疯疯癫癫生活,这种消息是他带来的,雁地拉威死后的坟地上突然长出一片竹子是他第一个发现。我要是现在告诉大家,我亲眼看到这只喜鹊像黄鼠狼一样潜入雁地拉威女人的粮仓,偷走了她的粮食,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就是发现这个秘密被挤走的。我和他的房子挨着。自从那天晚上我凑近了确认那个从窗户里把粮食拖出来的影子就是他以后,他就开始刨我的墙根。带着他的狗,一天刨一点,就在墙根下面,刨一个刚好能让他的狗头伸进去的洞,然后再换到另一边继续刨。一到夜深人静,我的墙根就开始响起来了,仿佛一大串老鼠正在攻向我这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的眼珠子都快跳出来了。“你干什么呢?”我说。“你不是看见了吗?”他说。“是呀,我看见了。你为什么要刨我的墙根?”他就不说话,牵着狗走了。等到第二天晚上,他又会跟狗一起出现,态度仍然冷酷无情,和上次那样与我对答一番,再牵着狗扬长而去。当初我把他刨墙根的事情讲出来以后,也没人相信我,他们只是捧着肚子笑了一顿说:这狗日的竟然会说笑话。焦点平台
“嗨,我在问你话,为什么在滴水崖?”喜鹊又重复一遍。焦点平台
“我住在滴水崖。”我说。
“你住在滴水崖上方,怎么那天跑到滴水崖山尖上站着?我们不相信你在那里吹风。”
“我就是在那里吹风。”
喜鹊说他不相信我的鬼话。不相信我的鬼话,却又一直逼问,我才是见了鬼了。
我给他们说的都是真话。那天早晨天空刚脱下它的黑衣服,露出灰中带白的皮肤,我就早早来到滴水崖山尖上吹风。这个习惯只有百里湾清楚。没死之前他时常到滴水崖砍柴,石头砸死他的那天早晨,他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早。我张着眼睛胡乱看了一遍,看到他从野木瓜树跟前走出来。我以为他是去采木瓜籽(其实还不到采摘的季节)。“你好啊!”我说。我一直用这句话跟任何人打招呼。他们也不排斥。他们说我读了几年书,确实应该说出几句跟他们不相同的话,只可惜读书读傻了。百里湾也不排斥我这句话。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嗨,你可真早。”
然后他继续走近木瓜树。我后来才琢磨清楚,百里湾来这么早是为了拿木瓜树出气,他要砍掉它,可惜那棵树长得太久,树干粗壮得可以在它身上搭一所房子,枝桠高而远,牵扯成了一大片林子,树龄大概是三个百里湾加起来的样子。百里湾不敢轻易动手,他扛着斧头在树下转来转去,仰着头看看树顶(当然看不到顶),又看看树干和树根。他肯定闹不明白这棵树是如何从石旮旯里抽取养分长这么“胖”。它长在陡坎上,脚下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有些生根石,有些从上面的山坡滚下来。它身上全是苔藓,苔藓长得旺盛,显然成了它的汗毛或者羽毛——如果它想飞走的话。夏天有鸟在苔藓中筑巢。百里湾一定是害怕树倒下来砸死他,迟迟不敢动手,当然,也可能还有别的担心。这棵树是附近村里好几个人的干爹。村人自古以来都有拜树为父,祈求庇护和赐予福分的习俗。像它这么旺盛的树,没有几个干儿子也说不过去。焦点平台
百里湾抡起斧头,已然拿定主意要杀掉别人的“干爹”。狠狠将刀口对准树干砍了上去。
“嗨!”我想阻止。
百里湾一刀下去没有讨到便宜,他的刀口反而缺了牙。我看他摸了摸斧头的“牙齿”。
“我操它妈!”百里湾说。隔着一段距离我也听得很清晰。他很暴躁。
百里湾扛着斧头到滴水崖山尖上跟我坐了一会儿。以往我们也是这么坐着聊天。聊完了他再去砍柴。百里湾很生气。不是那棵树惹他,是那棵树的其中一个干儿子惹他。
“难怪你要杀了他干爹。”我说。
“你懂个锤子。”他把气撒我身上。
“到底什么事呢?”我问。
“当然是钱的事。我打听到上面分下来好几个名额,能拿钱的名额。你知道的。当然你不会关心这些。”焦点平台
我就不多问了。关于钱的事,我向来接不上话。最近两年他们都在赶着写“申请书”,成为“残疾人”或“五保户”或“贫困户”或“孤寡老人”或……什么什么。
“钱的事情你不懂。”百里湾说。
“是的。”我说。
“其实你也可以争取。”他笑着。当然是知道我不会争取并且“你争取了也没有鸟用”那种笑。
“这种东西是需要动脑筋才吃得起的。”他说。
“是的。”我说。
“你有脑筋吗?”他说。
“有。”我说。
“你有个锤子。”他说。
“没有。”我说。
“那就对了。”他张口一笑。
“是啊。”我说。
“虽然你的确一个人过日子,年龄算来也不小,又穷又……(他想说‘又傻’)……完全符合条件。”
我点头。完全同意他的说法。这么些年看过来,我已经知道那些钱不是我这样的老实人吃得起。当然,也的确有实实在在的穷人依靠这笔钱并且得到这笔钱,可大多数份额,却让百里湾这样喜欢动脑筋的人争取走了——哦,差点儿争取走了。
他摸着缺了牙的刀口,眼里万分愁苦。“同样是生在荒坡上过日子,凭什么给别人不给我。”
“你不要难过,你下年再申请,在这个地方除了你谁也没资格当这个‘穷人’。”我安慰他。
“那肯定是当然的。我肯定能当上。”他冲我轻蔑一笑,横了一眼旁边长得又高又枯的杂草,怪我说了句废话。焦点平台
“我日他先人!”他说。他休息够了,莫名丢下一句脏话提了斧头就走。又去滴水崖下面砍柴。
我发了一会儿呆。心里乱七八糟。
百里湾走到滴水崖下面的草丛里,他所站的地方深草及腰,又密又厚,即使我站在高处,他弯腰下去,也差点看不见他。
“风吹草低见百里湾。”我突然忍不住笑说。他听见了。
“傻逼!”他说。
一个石头突然从滴水崖脚底滚下去。我先看到的。百里湾就站在石头下方的草坡上。他那个地方草有些深,为了不妨碍脚下,他已经钻出那片深草区,到旁边的黑泥巴草地上站着。
“快跑!”我说。
“迎着石头跑!”我说。
百里湾表现得很冷静,石头与他还有一段距离,他在观察石头翻滚的路线。
“迎着它跑。”我还指望他会听我的。他要是肯听我的就好了。毕竟这种状况我曾亲身经历。一块石头从山坡滚落,我也像百里湾那样站在石头下方的荒坡上,慌乱之中我竟迎着石头跑了几步,我的两只眼睛都要从眼窝里跳出来了,石头向左我向右,石头向右我向左,迎着它的好处在于我能看见它怎么来,在它快要跟我撞个正着时一闪身躲到一边去了。我就是这么避开了那次危险。这成了我的保命经验。可百里湾不相信。焦点平台
他甩掉斧头,好像已经拿准了石头滚去的方向。可接下来,他在大喊大叫,边跑边扭头,导致脚步乱糟糟的,连滚带爬。石头弯弯拐拐撵着他去了。任谁也想不到石头会拐弯。我以为我眼睛坏掉了。石头拐来拐去,像颗弹珠,追在百里湾屁股后面。
他大喊大叫:“我不相信!”
别说他不相信,就是我这个旁观者也怀疑自己的眼见。我不眨眼地追着石头和百里湾,百里湾往左边石头就往左边,百里湾往右边石头就往右边,他上它上,他下它下,他怎么逃它怎么追,那已经不像个石头了,像个埋了很深仇恨的滚雷。我满眼惊恐,喊不出话。
“救……”我听到百里湾凄惨地说出这个字的时候,他后面的话已经被石头砸碎了。接下来就是人们看到的样子。他们来得很及时。我站在滴水崖石头尖子上还没有把所有的气喘匀,他们已将百里湾基本收拾齐整。
他们埋葬了百里湾就来找我讨要事情发生的细节。
“天都快黑了。”我对喜鹊说。我也分不清这句话是不是在求饶。他对我所说的关于百里湾遭遇的任何细节都抱着怀疑。难道我会知道那个突然滚落的石头发什么疯吗?是它要百里湾的命,不是我。
“你就眼睁睁看石头砸死他了?”喜鹊说。很有几分打抱不平的味道。
“我喊他迎着石头跑。”我说。
“你想害死他?”焦点平台
“我曾经这么逃出一命。”
“你是傻子,百里湾又不是。”
喜鹊带着那帮人继续问了一些话,他想要的我一句也不会说,于是他带着他们离开了我的房子。显然他也不敢硬将脏水泼我身上。就算我是个傻子,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我不认,他也不好逼迫。
三
我还以为喜鹊会带着他的狗继续跑到滴水崖来刨我的墙根。把我逼到更远的角落。他没来。来的是一个女人。
我的眼睛看她的时候有点想躲。
“嗨。”她喊我。
“你是谁?”我说。
她战战兢兢来到我门口,有些害怕但又是壮好了胆子来的。脸色有些灰却并不难看。不经我同意就从屋檐角扯了一把草用它垫屁股,席地而坐,要跟我长谈什么。
“你忘干净了也好。这样我们方便说后面的话。”
我搓着两手,觉得手心里有虫子要钻出来。
“你盯着我看什么?”
我急忙躲开她,盯着天,看一会儿又盯着地,最后将视线安放在缓坡下面滴水崖的石头尖子上。我居住的地方比滴水崖还高,如果我不想活了,就可以从门口缓坡上走下去,走到滴水崖石头尖子上往下一跳就成了。但我从未想过死。我只是住在了这么一个随时方便去死的地方。
“你搓藿麻做什么?”
我这才发觉自己手心里搓着一片藿麻叶子,是它身上的毒刺像虫子在咬我。
“噢。”我说。
“你一直装作不认识我。”
我想我得出去走走。焦点平台
“你还在恨我吗?”
风吹在后背。快要入秋了。我感到后背旧疾复发,有点隐痛。我必须出去走走。
“你要去哪儿?”她追到我跟前双手拦着,“你一辈子跟人装疯卖傻——跟我也是。很早以前,你不是这样对我的。”
“我不认识你。”我说。说得心慌魄乱。
“你眼睛出卖你了。”
“没有。”
“你逃避了一辈子。”
“我没有。”
“好吧,我今天也不是来逼你承认什么,你要装傻就装傻,我不拦着,但有些事你瞒不了我,也麻痹不了你自己。我在你的视线之内过了一辈子,你敢说,不是这样吗?你完全没有关注我的生活吗?你从不把别人看成你的朋友,但你看百里湾是朋友,这说明你想知道我过得好不好。一开始恨不得我天天哭着过日子,后来我日子过得确实不怎么样,你又希望我过得好。你在暗地里关注我的一切。你以为你的心思能逃过我的眼睛吗?好歹我也读了几年书,并不糊涂,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何必这样说。”
“你还说不认识我吗?”她气急败坏的模样,脸都是红的。
我受不了女人这种样子。她们一生气就是用整个力气和整个命在生气。
“那你说我是谁?”
“百里湾的婆娘。”
“放你屁。”
“以前是我的。”
她绷不住笑开了。原本她这个时候不应该笑。她也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苦着脸,毕竟才死了丈夫。所以她立马将笑容缩回去。焦点平台
“我也不是逼你。”她情绪万分低落,“我是没有办法。你看得见我现在的情况。”
她两个眼睛看着我,眼里含着我说不清的意思。我感觉自己的两个眼睛被烧熟了,转不动。
“你根本忘不掉我。是不是。”
“不是。”
“你就继续掖着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心慌了?”
“不慌。”
“你不用在我面前装傻。我清楚你是这个地方最聪明的人。可这里不需要这种人。至少我不需要。有时候你得……我好像不用再说这些话了是吧?很久以前我们见面的那天下午一直到深夜,我都在跟你说这些话。你不高兴听。后来我就走了。我知道我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也知道。虽然你心里对我十分满意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可我不愿意。”她说到这儿突然又笑了笑,有些羞涩,“我很不好意思,那天晚上把你的窗台踩烂了。”
“哦,没什么,它本来就是烂的。”我说。
“它可以再支撑一些日子。如果我不踩的话,或许一辈子相安无事。是我踩烂了。”她说。
“烂了就算了吧。”我说。
我们已经不是在说窗户的事了。我心里有潮水在翻滚,翻出许多沉渣。她跳窗逃走那个晚上我的两个眼睛一直在黑暗中睁着,就仿佛看着我的一个魂,毫不留念从我身上逃跑。我没有阻止。书上说,各人有各人的自由。第二天父母暴跳如雷地跟我说她逃走了,要去追回来打一顿再退婚,我拖住他们说,我和她只不过办了一场结婚酒,还没来得及到官方那儿要一张牢靠的证明,她要走就走,各人有各人的自由,既然迟早要离开,晚走不如早走。这事情才算从我父母那儿过去,我自己这儿也算是过去了。焦点平台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岔开话题。
“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
“你说。”
“你应该猜到什么事了。”
“猜不到。”
“我希望你搬回原来的老房子。那是你父母留给你的,如果他们还活着也不会让你就这么搬走,他们指望你在那座房子里……娶妻生子。你总不能一直让它空着。喜鹊的狗刨坏了墙根,房子还是坚固的,回去修补一下根本不碍事,比这儿强太多。”
“我不会娶妻生子了。”
“你还不到五十岁。”
“已经老了。”
“如果在城里,成亲的年纪正好。”
“这是深山。”
“你不能这么想……从前的事情都怪我,那时年轻荒唐,心气不稳。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我不需要安慰。”
“喜鹊不会再挤兑你了。”
“我不是怕他。”
“我知道。”
“为什么要我搬回去呢?”
“你搬回去了就是在帮我的忙。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我也顾不得讲什么旧情和脸面。我得让我的两个孩子有指望。他们需要钱……不,是我需要钱养育他们。吃穿用度已经全部落在我身上了。”焦点平台
“我知道了。”
“只有一个名额……”
“嗯。”
“你心里早就明白我为什么来。”
“一开始不明白,说到这儿明白了。”
“我必须拿到这个贫困者的名额。你也清楚我需要这笔钱。虽然它很少,几乎济不了什么事,可我仍然需要。我找过他们,他们说暂时不打算给我。因为有你。你住在这所简陋的房子,你的房子在显眼的地段,又在危险的滴水崖上方,来考察的人走在你后面的公路上,一眼就看见你的房子,它又矮又难看,简直破坏这儿的形象。如果最后一个名额没有落到你手里,我们这儿的‘管家’可就麻烦大了。他们说,只要你肯申请,只要你见到他们的时候不要总是讨人嫌,连个招呼也不打,他们就会大大方方也是理所应当将名额送到你手上,毕竟你一个人过了半生,并且你还是……”
“我是傻子‘嗨’。”我接了她不便说下去的话。
“理应受到照顾。”
“我能照顾自己。”
“可你的房子没有显示这一点。”
“房子如衣服,防冷防冻防山雨就行,要什么好看。”
“当然要好看。你没有看见所有人的房子都抹上墙灰了吗?还画上了富贵竹。现在我们张着眼睛随便一眺,都是白花花的房子,在深山草林中,看着干干净净,像一片银子。”
“哈哈……”
“你打算笑多久,你是在笑我吗?”焦点平台
我赶紧绷住嘴巴。
“你这房子如果能画,我是说,你那天没有疯疯癫癫喝了酒发狠阻拦,也画上了。”
“那些墙缝是用牛屎补上,然后再涂涂画画,有什么用?”
“至少表面看去顺眼许多。”
“牛算是熬出头了。”
“什么话。”
“它们的粪涂了墙。”
“你不要开玩笑。当然我很高兴你能在我面前有什么说什么。”
我盯着她的额头,她额头上有皱纹。
“我们这儿的‘管家’还等着你写申请。只要你肯申请,他们就给你名额,你不申请,那名额也就空出来了。”
“我知道。”
“谁会比你清醒明白呢,可你这样的性格,也只能是傻子‘嗨’。”
她还是那个聪慧的姑娘。年轻时候敢跳窗逃走的姑娘。是我曾经喜欢了很久终于娶到家里待了一天的姑娘。只是已经过早地变老,心也疲惫,皱纹拔光她年轻的羽毛,包括个性的尖刺,早前她能飞翔,如今重重地摔在地上了。她并没有如她所说,闭着眼睛走出去也能摸个比我强的。我竟有点……后背旧疾复发,觉得风冷。
焦点平台登录:www.sdptzc.com
“百里湾已经死了。家里少了依靠。”她起身站到我跟前,指着滴水崖:“你住在这儿又高又险又陡,下方还有被石头砸死的百里湾,这个地方有什么好?”
她忘了她曾经说过,我什么垃圾都能忍受。
“你能搬回去住吗?他们说只要你搬回去住,不在这儿碍眼,那个名额就可以给我。”她满怀期待。焦点平台
“百里湾生前很苦恼自己当不了贫困者。”我说。
“那时候我们不符合条件,现在不一样了……我是说,那些人个个都有自己的门路,我们的门路只要稍稍窄一点,就得让路给别人。我现在说这些不是庆幸什么。毕竟他是我的丈夫,孩子们失去了爸爸。现在我家的情况的确跟之前不一样了,孤儿寡母,所有人都眼睁睁看见,只不过……”
“只不过我成了绊脚石。”
“我不是来逼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是来和你商量的。”
“我不打算要什么名额。百里湾的愿望要实现了。”
“你答应了?”她眼睛亮晶晶。
我说“嗯”。说得很难过。
她连连道谢。然后就走了。走之前帮我把屋檐草又塞回屋檐上。她胖了,走路左右晃荡。
四
我就知道搬回来要遇到什么麻烦。喜鹊隔三岔五堵我门口。不过他什么话也不多问,也不阻挡我出出进进,也不刨我墙根。我后来就当他是个鬼,遇到心情好的一天还会冲他笑。
我将滴水崖的房子改造成猪圈,每天跑着去喂猪,然后跑着回家休息。我的房子被涂抹成他们想看的那种样子,老远看过来“真是好看死了”。深更半夜来涂抹的。管家克尔迪亲自带人干的好事。他们带上了木匠的墨斗,在我的墙壁上弹出了标准的瓷砖线条,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一看,差点以为真给我砌了一层墙砖。那些人都不单纯地喊克尔迪的名字,也不喊他组长,他们习惯喊他管家克尔迪。他做事倒还认真。起码墙上的高仿瓷砖做得还挺像那么回事,连我这个房子的主人看了都信以为真。他也的确如他曾经跟我说的:保证不伤你的墙,保证妥当。他确实干得不错。焦点平台
“管家克尔迪派我来的。”喜鹊是这么解释的。
我已经很久不给喜鹊任何笑脸。我俩隔几日就在门口相见。烦透了这种该死的见面。后来我就当他是一条给我看门的狗,当我心里这么一笃定,他竟不怎么来了。当然,他来不来没什么区别,我们两个的房子始终像两个鼻孔挨在一起。管家克尔迪的房子与我本来隔着两道弯,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把房子往外又挪了个地方,如今隔着七八道弯了。
百里湾的房子掀翻了重新修建,修在离我们这片地方远一些,但从我这个地方能一眼看见的山包上。那儿一大片矮松,还有并不茂密的青冈树,再有一些野杜鹃,夏季五月的山包上所有植物都会开花。百里湾活着的时候就看中的地方。他说那座山包风水大好,活人住着旺家产,死者住着不失眠。他这辈子算是交代完了,啥也没捞着。即将住在那块风水宝地的是我的……他的女人。
五
听到屋檐背后有人说话,在争辩什么,声音极小。天气入冬,深夜里我不愿起床,哪怕有泡尿憋着,也不高兴起来放掉。说话的声音像老鼠始终咬着我的耳朵。不厌其烦我就起来了。推开房门,天空已经黑得看不见了,空气中隐藏着一场大雪。没有半点儿星光照亮,地上一片漆黑,我仗着对屋子周围的熟悉,用脚摸路,一步一步摸到屋檐后面。先前说话的声音却彻底断了。等我返回房间,屋檐背后说话的声音又响起来。这回我在房里点了油灯才出门。我们这儿的电灯只有白天亮,天擦黑以后就停了。我们的小电站修在河沟边,一台小小的发电机,每家每户轮流去发电,到了农忙时节就不发了,谁也不想熬夜,于是农忙的时候天都是黑的。焦点平台
我烧了一把松明捏在手里,刚跨出门就被风吹熄。等我摸到屋檐背后,说话声又断了。
我准备再次转身回屋,却被人一把抓住胳膊。“嗨”,那个人说……不,是在喊我。他吓我一跳。我听出是喜鹊的声音才放下心来。
“你都听到了什么?”他今天脾气怪好,没有想打人。
“没听到。”我说。
“你听到也无所谓。”
“你刚才和谁说话?”我冒着胆子问。
“没有谁。我自己说话。”
“噢。”
“你坐下来,我们聊个天。”
“为什么要找我聊?”
“因为你是傻子。”
“喜鹊,我不是傻子。”
“行了,我知道了。”他说。
这么冷的晚上我凭什么陪着一个刨我墙根的人聊天?突然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心里闷痛。“我要回去了。”我说。焦点平台
“不是我故意要堵你的门。真的是管家克尔迪让我干的。”
我没说话。
“好吧,他妈的,我全部告诉你好啦,虽然你是个傻子。”他豁出去的语气。
他干什么要生气?我这么难过还忍着呢!
“那一阵子我堵你的门,是受了管家克尔迪的嘱咐,他不让你四处走动。万一你打扰了百里湾修房子,那麻烦就大了。”
“你在说什么呀。”
“你他妈还真是个傻子,你是真的傻吗?”
“我不是。”
“你是。”
我不接这句话。听到这话也总是突然接不上来。也许我确实有点智力不足,就像我母亲跟父亲哭诉的那样,她做了什么孽生了一个蠢货。也只有百里湾的女人还觉得我是个聪明人。她曾经也是我的女人……差那么一点儿就是我的女人了。可能只有在她跟前,我才会表现出那么一点儿聪明才智,来压制骨子里的愚蠢。
“你旧情人可不是好惹的。你还是小心点儿,不要被人两颗眼泪给骗了。”
“喜鹊,你不要这样说。”
“我有名字!”
“欧慕衣合。”
“这就对了。只有你这样的傻子才不需要名字。我和你是不同的。虽然我刨过你的墙根但至少没有抢你值钱的东西。你还是好好想想,值不值得为了那样一个人从好好的滴水崖搬回这座完全可以舍弃的老房子。你不知道你上当了吗?几句话就把你的心说软了。你要是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我敢肯定,那个名额就是你的,那么现在热火朝天修房子的人就是你。名额一到手,就可以咣当咣当地给你免费搞起一座新房子。”焦点平台
“我不需要名额。”
“对。你不需要。因为你是傻子。”
“欧慕衣合,”我说,“你不要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
“滚。”他说。
我回屋了。还好回来及时,否则油灯烧干了。
六
我对欧慕衣合的恨突然就没有了,因为那天早晨,看见他坐在自家门口院墙边的狗屎椒树下,哭得像一条狗。
“你哭什么哭。”我说。
“听你的语气很不耐烦?”
“没有不耐烦,我好心好意的。”
“关你什么屁事。快滚。”他说。
到了夜里,欧慕衣合还没有进屋睡觉。他可能整个白天都坐在门口。这一天我在滴水崖那边和我的猪待了一上午,下午去滴水崖对面的山沟,找一些野生果子,天快黑了才回来。欧慕衣合只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半夜我出门撒尿,看见他还没有进屋。
“你白天去哪儿了?”他突然问。
我的左脚才踏入门槛又退出来。我俩的房子朝一个方向并排开门,秋天刚过去那会儿,我突然想让房子更敞亮一点,便拆了靠近他那边的院墙,而他也拆了靠近我这边的院墙,这样我们两个几乎是共用一个院坝了。我们彼此进进出出都在对方的眼皮底下。焦点平台
“上午喂猪,下午去山沟里找一些果子。”
“你倒快活。”
他这话说得让我很不自在。但谁会真正管他说什么呢!我要做什么事或者不高兴听他唠叨,一扭屁股就可以走开。
“天冷。我要睡觉。”我说。
“你不知道百里湾的房子修好了吗?”
这话结结实实把我牵住。
“知道。”我有点难过。百里湾的房子就修在那块风水宝地,高于我眼睛的地方,每天早晨一抬眼就看见那座一天比一天完整一日比一日漂亮的房子,房子的山墙上还画出了好看的图案,房顶上两根牛角仿佛要把左右两边的大山挑起来。我怎么会不知道它修好了?
“管家克尔迪亲自指挥呢。”他说。
“噢。”我说。
他不高兴往下说。我也不高兴往下说。
这个地方一到夜间,冷风呼噜呼噜吹个不停,山中树木繁密树种繁多,每个季节都有树开花也有树落叶,我和欧慕衣合的房子门前永远有扫不完的落叶。第二天清晨我俩若不是特别忙,第一件事保准就是哗啦哗啦打扫各自的院落。树叶都是在夜间被风吹来堆积在此,所以这个时候,我俩脚下除了冷风就是树叶不停地挑衅似的撞击。
“肏。”欧慕衣合没头没脑地骂一句。
我回屋点了一盏灯,院坝仍然黑着,但是眼睛起码能有个亮光可以追了。我又回到欧慕衣合身边。
“看来你睡不着了。”他说。
“算是吧。”我说。焦点平台
“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在房子背后的屋檐脚下跟谁说话吗?”
“不知。”
“是百里湾的女人。”
“你没说真话。”
“好吧。是管家克尔迪。”
“你们说话为什么要藏起来。”
“我们不是在说话。我们是在打架。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打完了。我敢打包票,他那天晚上有一半路绝对是爬着回去。”
“你敢打管家克尔迪?”
“是啊,我竟然把他揍了一顿狠的。他的鼻梁骨被我打断了。”
“难怪那天我看见管家克尔迪戴着一只蓝色口罩,他兴许真的摔了一跤,一只膝盖上的裤腿卷起来,血红血红的,眼睛也通红,不跟任何人说话。”
“那个杀千刀的。”
“我没听说你们有矛盾。”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我真羡慕你敢打克尔迪。”
“打完我就后悔了。你看看我现在跟烂泥有什么区别。往后我在这儿的好日子可算到头了。”
“没那么严重。”我安慰道。
“你不了解克尔迪。但我竟然打了他还能怎样?往后只能尽量不去招惹那个女人。我心里非常不甘心。我被那个女人骗了感情,天呐,说出去都嫌丢人。嗨,我跟你说的话你听得明白吗?你要是听明白了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她一开始跟我走得很近,让我把你看住,我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我真是比你还笨。现在轮到你来笑话我了。克尔迪让我看住你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谁能想到呢,她翻脸无情。她让我看住你的时候,我连汗毛都没有抖一下,把你看得死死的。”焦点平台
他说得有点急也有点乱。
我早就知道她会选择管家克尔迪。这个女人年纪已经不小,可是管家克尔迪更不年轻,很久以前,那时候百里湾还没有死,她的眼中就已经含着克尔迪的影子。我就是那样一天天崩溃下去,幸好,也渐渐想通透了,我理清楚了她选择百里湾或者克尔迪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我已经不是她的男人更不是她妈,她爱谁是她的自由。许多年以来我都在荒废自己的时日。但我不能怪她,谁让很久以前的那天晚上,她撬开窗户逃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及时阻拦。大大方方放出去的人,凭什么指望她自己回来?
落叶从我的院子吹进欧慕衣合的院子,又从他的院子回到我的院子。看不清脚下都是些什么树叶,但能闻到一些青冈树和矮松木的味道。当然也可能这些林木的味道来自那片山包。那个山包夜间看过去像个黑色的月亮。永远无法抵达的月亮。永远看不透它内心有亮光。“你什么都不要,那你活着干什么?”我想起这句话。这句话是她说的。带着一丝抱怨和一丝恨意。踩烂我窗户的同时把这句话撂下。
欧慕衣合在喝酒。喝得有些醉了。
“我还要把他揍一顿。”欧慕衣合说。
“你不要莽撞。”
“笑话,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你不会争取是你没本事,你说你有本事吗?”焦点平台
“有。”
“你有个屁。”
“百里湾那天也不听我的话。”
“你这么说是在诅咒我?”
他一巴掌拍在地上。我缩了缩脚。以为他要一巴掌拍死我的脚。
“一个人的日子过得快疯了,你不无聊吗?”他又说。
“我不。”
“也对,你一天抱着这本书啃完了啃那本书,你既不无聊也不空虚。”
我很久没有看书了。书在我房间高高的房梁上,我用麻袋将它们装起来吊在那个地方。
“克尔迪说你年轻时有三年时间一直在外面流浪,流浪够了才回来居住。你是单纯的出去流浪吗?你不是为了忘记那个女人吗?像你这样中了书毒的人总有一百种理由使自己淡忘过去,要说本事,大概这就是你的本事。你从书里找到了自己可以软弱的依据。我也上过学,说起来我上学比你还多,整整有九年时间我都在学校里面跟书打交道,可我就没有你身上这些毛病。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你读的书对你起着反作用。你是这样才将它们挂在房梁上的吧?你看见她在村里来来去去,就跟看见我来来去去没什么不同,你心里真有这么宽松吗?我不太信。”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你既不干坏事,好事也不怎么干。你跟大家一样活生生的,却又跟大家活得不一样。嗨,你是不是真的脑壳有点儿问题?我有时也相信百里湾的女人说的是真话,她说你是这个地方活得最通透的人(那时候她还不像现在这么无情,她会跟我扯闲天),但多数时候我不相信她说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个无处可去、在外也混不下去的倒霉蛋。你在外面最高的生存能力也就止于‘饿不死’——这话说得没错吧?我要是出了这片大山,你信不信撒尿都不带拐弯?像你这样出去三年回来,能让你看出还是从前那种鸟样,那就算我不是人。”焦点平台
他在胡说八道了,他醉了。我伸手想抓住他的头发,像提秧苗那样提起来甩进他的房门,又担心这个动作会引来今后更多麻烦。我想我不是傻,我只是过于小心谨慎,过于瞻前顾后,自视清高却始终陷于生活的烂泥。我什么都敢想,却什么都没做。
“睡觉咯。”我对欧慕衣合说。
“滚蛋吧。”他说。
我摸黑回屋。油灯已经熄了。
七
我摸黑回屋,重新点燃油灯又将它吹灭。欧慕衣合睡去了。外面不再有他胡言乱语的声音。外面只有风声,还有一只两个月前突然从什么地方跑进我们村的小狗。它在玩弄欧慕衣合丢在院子里的空酒瓶。白天总见它到我院里来,是一只杂毛狗,大概因为生得丑,被主人嫌弃驱逐,它来我门前接受剩菜剩饭,偶尔也接受别家的,成了一只百家狗。它的眼神总是可怜巴巴,时常夹着尾巴。我走到门边,看到它的影子,在深夜寒风中追着酒瓶飘来飘去。“你过来。”我这样喊它。它不来。“儿子啊!”我这样喊它,它就来了,在脚边闻了又闻。“去玩吧。”我说,它就跑开了。这个晚上估计是它最开心的晚上。我坐在门槛边的草凳上,后来坐在冰冷的门槛上,门槛是一根硬条石,早已在多年风雨中变了颜色,它抵在墙角的两端已经生了苔藓,犹如人在岁月中将头发浸白。都怪欧慕衣合说的那些疯话,密密匝匝地像一窝蚂蚁,一步深过一步爬入我的耳朵,像雨一样掉入心里。焦点平台
我重新点灯,爬到房梁上解开书袋,抽签似的抽了一本,在油灯下翻了一会儿又将它塞回书袋。
无法平静。无法入眠。感觉脑袋上的毛都因发愁而脱光了。似乎有件事牵扯我的心,这件事却没有轮廓。
——不,有轮廓,我已经来到门口的院子里了。黑洞洞的四面的山脉,像脚下厚土暴露于黑夜中的血管,冷风一吹,它们的血液就开始偾张涌动,涌动的风声从遥远的山顶吹来。我在向着那个小山包走。已经到了小山脚下。垂头钻入树林的一条小路,这条路不常有人走,杂草丛生,夜间走全看运气,一不留神就会碰着让人痛痒半天的藿麻。为了不让藿麻触着脚踝,我事先将裤管扎起来了。
“嗨!”有人突然喊我。
“哪个杂……”我心里想咒骂一句,又突然收住。一道黑洞洞的影子杵在我面前。焦点平台
“深更半夜不睡觉钻小树林做什么?”
是吉鲁野萨的声音。他不是疯……老糊涂了吗?他比我高出许多,像白天的阳光把他扯长了似的。
“老人家。”我喊他一声。这么黑的晚上我也懒得给他笑脸。“很多年不见您啦!您身体好吧?”
“很多年没见,现在你也看不见嘛。”
他说话真不留余地。
“的确看不清。能听到您的声音真好。您知道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我相识的长辈也……”
“也不在了。”
他抢了我的话。
“您下山有什么事吗?怎么不去家里坐坐。”
“我每天晚上都会到这儿走一趟。”
“每天晚上?”
“是啊。”
“来做什么?”
“不知道啊。”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下说了。传言果然是真的,吉鲁野萨的脑子已经不清醒了。
“我要回去了。天亮之前回。每天晚上我准时下山也准时回家。嗨,我很高兴在这儿跟你遇见,你要是遇见我的老太婆,一定告诉她早点回家。我和她走散了。”说到回家他很高兴。
“难道她老人家也在这个小山包上吗?”
“嗯。我感觉她在。”
吉鲁野萨走了。树木的影子在弱光下随风晃动。
我继续向前,但并不是往高处,围着山包转圈。已经转过一圈。吉鲁野萨是在我转第一圈的时候遇见。我转到第三圈时,又一道影子杵于眼前。
“嘘。”我故意发出声音。焦点平台
“没老没少的东西!”
“老人家,是您啊?”
“还听得出我的声音?”
“听得出。”
“好吧,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我遇见您的丈夫了。他让您早点儿回家。”
“你是说吉鲁野萨。”
“是的。”
“他不是我的丈夫了。”
我一阵惊讶,又缓和地带着几分劝解的意思:“您和他吵架啦?”
“没有。”
“您和他是一辈子的夫妻呢。”
“那又怎样。现在我和他各走各的。我们在山林中走散以后就没有再遇见过。起初我们的确真心实意寻找对方,后来就不这么干了,突然之间就不想再遇见。有时差不多快遇上的时候我就急忙拐个弯错开。我相信他也是这么做的。要不然这些山脉之中(许多年来,我们几乎把这儿的山都走遍了),如果我们真的想遇见,又怎么会遇不见呢?”
我听得有点儿糊涂。
“我已经像这些山中的一把青苔,要我重新回到家中,我会不习惯的。他也不习惯。”
“他说他每天晚上准时下山到这儿走一趟,然后也准时回家。他亲口跟我说的。”
“亲口说的也不作数。他一时冲动才说了那些鬼话,就算他今天看见你想起一些往事,顺便想起我,嘴上忍不住念一番旧情,明天他就不会这么想了。生不认魂,死不认尸,我跟他如今各有各的路,既然能在一片山林的一条路上走散,说明我和他缘分到头了。你要是再遇见他,我保准他是另一种腔调。吉鲁野萨可不是从前那个吉鲁野萨了,他现在浑身上下轻得像一根能飞的红公鸡毛,不会想着再被什么东西牵绊。嗨,你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里转什么圈子?你又不是一只野山羊。”焦点平台
“我随便走一走。”
“那你继续在这儿转圈。我要走了。”
她走了。
我想朝着山包上走却没有勇气,就算我的双脚向上跨了两步也会滑下来。或者我刚想往上走的时候,手被藿麻扎中,或者我心里才冒出一个向上迈步的念头,我的大腿就抽筋了。
天快亮时我回了家。院子里堆满昨夜随风而来的落叶。
……
(本文为节选,详情请参阅《四川文学》2023年第1期)

阿微木依萝:彝族,1982年生于四川省凉山州,自由撰稿人;著有小说集《出山》《蚁人》《羊角口哨》,散文集《檐上的月亮》等多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现居西昌。
焦点娱乐登录: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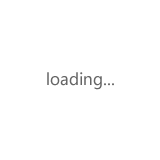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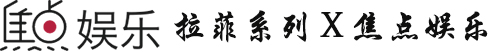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