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娱乐网快讯:
导读:
祖父、外祖父两支家族的迁徙与离合,隐藏着后人命运的线索,家族血脉的烙印,或显或隐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余一鸣,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市作协副主席。已发表小说约两百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三次获江苏紫金山文学奖。
烙印(中篇小说 节选)
余一鸣
一
婚礼主持人说,下面有请新郎的父亲王先生发表讲话。我和老葛会心地一笑,果然老王的亲家也姓王,那么老王的女婿也姓王。我们仨是大学同班同学,我和老葛还是发小,我们仨同一年毕业,同一年成家,同一年当爸爸。因为生了女儿,老王在我和老葛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说,唉,老王家五千年的家族史到我这里,画上了句号。我俩只当他是玩笑话,说,你一个堂堂大学二级教授,脑子里怎么全是封建残余。按常规女孩子结婚应该比男孩子早,可老葛的孙子已经在大洋彼岸的草坪上满地跑,我儿子也在三年前成了家。老王家姑娘年逾三十,我们也替老王着急起来,这年头,小子易娶,姑娘难嫁,鲜花想插在牛屎上,牛屎还嫌鲜花碍手碍脚。谁的单位上都有一堆“剩女”,模样俊,学历高,找对象高不成低不就。老王不着急,说,你们别有歉疚感,姑娘有姑娘的主意。前半句当然还是玩笑话,孩子们小时候,三家常聚,我和老葛都抢着要王家女儿做媳妇。俩傻小子在我们的唆使下,都抢着喊老王“泰山”,一直到半大不小才改口。这俩小子言而无信,高中毕业就出国留学,溜之大吉。老王不舍得女儿离开,留在国内读书,生女儿和生儿子的父亲,想法毕竟不一样。王家姑娘的主意是什么?到今天我们总算明白,就是嫁一个也姓王的小子,延续老王家五千年的历史。这哪里是姑娘的主意,分明是老王的主意。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老葛说,一会儿老王来敬酒,得罚他,文明社会竟敢干涉女儿婚姻大事。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我点开,是来自外市的陌生座机号码。座机号推销商多,我不接,将手机塞进口袋,任它折腾。
老葛说,如果真是这么回事,这老王还真是榆木脑袋。一个姓氏不就是一个符号吗?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本来应该姓陆,我父亲被我亲爷爷遗弃了,后来被大葛村葛姓人家收养,改姓葛。我儿子出生后,我专门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是不是把儿子的姓改回去。我父亲说,做人得讲良心,顶了葛姓的门户,世世代代就是葛家门的人。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秘密,我想起小时候的老葛作为大葛村小伙伴的领袖,带领我们打群架偷西瓜,原来他也并不是正宗的葛姓人,与我一样,根不正,苗不纯。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老葛现在是一家拍卖行的老总,据说身家已有几个亿,是我们同学中的大老板。我们这代人都只有一个孩子,他要是没有儿子,说不定也担心万贯家财随了别姓。
我正要接话茬,手机像一只网中的鸟儿又扑腾了,我点开,还是那个号码,我不耐烦地接了,说,你有完没完。对方是个男声,说,您好,您是刘家一先生吗?我是拆迁办小白。诈骗电话应该说,我是公安局,这小子换套路了。我正要挂机,对方说,我这里是淹城市天宁区拆迁办,您在本区柏树坟的房产在本次拆迁范围内,请您携带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前来办理相关手续。这消息有点突然,其实也不突然,几年前我去淹城办理祖屋租赁手续时,街坊就说快要拆迁了。等着等着一直没有下文,没想到这事说来就来了。
婚礼进入高潮,大厅里人声鼎沸。我看见老王脸上挂着喜悦的眼泪,笑成了一朵油腻的花。我存下了淹城那个电话号码,拆迁是个麻烦事,不是一手交房一手拿钱那样简单,至少有一个阶段,我得与这个号码,或者说号码后的那个小白常打交道了。
老葛说,你快看老王,掉泪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嫁女时呀。
我没顾得上说话,老葛说,你这家伙,这么精彩的时刻,你还分神,又想到你言情小说中的某个女主角了?我有个习惯,突然有某个场景触动我时,我会立即打开手机,写几行字发送给自己,备用。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但今天真不是。
焦点注册:www.sdptzc.com
二
小白是我想象中的小白的样子,微胖,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恰当地掩饰了他不算大的眼睛,穿白衬衣,是拆迁办的办事员。以前都是开发商搞拆迁,惹出的事多,现在是政府负责拆迁,拆完了再把地交给开发商。小白这样说的意思我明白,他是代表了政府,是公职人员。他验看了我祖屋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拍下了照片,不是用手机,而是用照相机,然后给了我一张《房屋调查登记告知书》,整个过程郑重其事。他把那两证还给了我,说两证上的名字不是你。我说那是我父亲的名字。小白说,那不行,你必须带你父亲来拆迁办,当面签一个委托书,我们后面的程序才认你。我有点犹豫,我父亲年近九旬,老骨头老腿,这来回一趟,得坐五六个钟头的车,我怕把他那把老骨头震散了架。我央求小白,有没有通融的办法?小白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说,没有。我说,那好吧。我请求小白让我加了他的微信,年轻人喜欢玩微信,方便以后与他联系。我父亲耳聋,这对老年人来说,反倒是个不错的毛病,非礼不听,礼也不听,省了很多烦恼。他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退休后习惯把家人都当他的小学生,诲家人不倦。耳聋以后,他的精力转移到关心国家大事上,《新闻联播》一天不落,每次见面都要与我商讨世界格局和台海形势。可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继承了他当教师的衣钵,却没有他的世界胸怀,因此,在他开讲之前,老老实实扮小学生聆听状。他说美国总统拜登,我说你冰箱里的牛奶过期了;他说蔡英文,我说这女人心机太深。反正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只要态度端正嘴皮翻动,他就认为儿子在和他互动。都说盲人轻信、聋人多疑,我父亲在这一点上表现良好,作为曾经的小学教师,他把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看得像小学生一般清澈无邪。他的毛病是一旦遇上什么事,就会整夜失眠,担心某一个环节会出纰漏,比如说我儿子在美利坚旧金山,如果在电视上看见天气预报旧金山降温,他就整夜担心他孙子会挨冻。他独自住在郊县的老教师宿舍,我进了屋才告诉他,我要带他回一趟淹城老家,他听不清,我写在纸上。他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大声说,好啊,好。然后喜滋滋地找出身份证、户口簿,还有一堆色彩缤纷的药丸。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家的祖屋坐落在柏树坟村,这村名不太好听,现在改称为柏树坟社区,但村还是个村,城中村,三十几幢破旧的小楼,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巷道,四周都被街铺和厂房包围了。我家是一幢二层旧木楼,父亲说这楼比他小五岁,他五岁那年,才有了柏树坟这楼。这楼坐南朝北,与别家的楼朝向相反,或许大门开在巷子边上,是为了方便进出。巷子太窄,小车进去就把路堵死了。我找到一处停车场,和父亲步行回家。父亲喃喃地说,变了,改变了,都换了样。我知道父亲的泪水又控制不住闸门了,脸上肯定老泪纵横。父亲的眼睛一直有个毛病,见了火光流泪。父亲解释说,他小时候,遇见过一场大火,从此眼睛就不敢看见火光。其实,不只是火光,他照镜子也会流泪,甚至和他孙子视频的时候,泪水也会滚滚而下,将他孙子吓得不轻。父亲到了巷子口,巷口坐着一位老妇人,白发稀疏,早已遮不住头皮,她闭着眼睛,对热闹的世界不屑一顾。我们走过去时,她突然睁开眼,说,二少爷,是二少爷吗?我肯定我父亲的耳朵听不见,但他却回头,说,是阿妹吗?老妇人颤巍巍站起来,伸出双手,频频点头,让我担心她一不小心会把仅剩的几绺白发抖落。我父亲在这个村子长大,少小离家老大归,遇见故旧,不仅流泪,而且哽咽了。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父亲站在祖屋门口,我掏出钥匙鼓捣了一会儿,依然打不开门锁,这屋子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进去过。我奶奶去世以后,这屋空了几年,后来我把它租给了一家外地公司做办事处,再后来,这家公司做大了,搬去了现代化大厦,这屋就空着。我的左邻右舍,从不放过一寸土地,在空隙处搭建起棚户,租给附近工厂的打工工人,赚点小钱不算什么,为的是等待拆迁,据说拆迁时违建也有赔偿款,这次终于让大家等到了。我早年来柏树坟时,邻居中就有人向我建议过,在后院搭一排平房,可我居住在几百里之外的南京,习惯了在高校混日子的我,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缺少鸟儿衔木筑巢的意志。那时我父亲耳朵尚依稀听得见,说,那种小市民热衷的事你少做,老刘家的房子越造越小,我们没脸去见祖宗八代。我父亲把小学教师剔除在小市民之外,他不知道,我这大学教师其实满脑子装的都是小市民思想,只是天生懒惰,行动上离一个合格小市民的标准尚有差距。我父亲自我奶奶走后再没有来过柏树坟,我绞尽脑汁想打开门锁,实在不行,我打算砸了门锁,换一把,我父亲却说,算了算了,我未必要进门。我和父亲直接去了拆迁办办公地点,小白告诉我,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他们早在村里临时租房办公。小白对白发苍苍的老人前来办理相关手续,很是感动,讲了一大堆客气话,可惜我父亲一个字都听不见。祖屋的房产证上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在委托书上签了字,跑腿的事交给了我,从此就不需要他老人家长途奔波,一趟趟往这里跑只是我的事了。临走时,小白拉住我说,两证上写的是你父亲的姓名,你母亲可健在?我母亲二十年前就去世了。小白说,这房子是你父母双方的财产,你母亲的那一份,你得证明你是你母亲的儿子。我说,我找谁去证明?我母亲是独女,我外公外婆只有她一个孩子,没有七大姑八大姨替我证明。小白说,你外公外婆可健在?我外公外婆在上个世纪就去了天国。小白说,你必须开证明,必须证明你是你母亲的儿子,唯一的孩子。据说我本来有一个弟弟或妹妹,可惜在来到这个世界前就夭折了,这是我母亲一辈子的痛,我母亲说,要是有个弟弟或者妹妹,你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母亲希望我是什么样子,至今我还没明白。小白这样说,我一下子头大了,小白说,去当地派出所查原始户口资料,去当地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其实很简单。我无奈地苦笑,我父亲正跟某位老邻居牵着手谈得兴浓,我拽一下他的衣袖,说,咱得回南京了。路过祖屋时,我用手指了一指,他坚决地摆手,说,反正要拆了,看什么看。有一条你要记牢,拆楼时我们自己拆,不要让拆迁公司的人来拆,听明白没?我用力点了点头,心中叫苦,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小老头如何能拆得掉一幢楼,哪怕是幢小木楼。即使雇用人工,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城市,我也是睁眼瞎,不知道去哪里找人。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的春节几乎都是在淹城度过。我奶奶有两个儿子,我的大伯,按淹城人的叫法,我称他为“大爸”,在上海一家工厂工作;我父亲是老二,他初中毕业后读了淹城师范,然后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做乡村教师,来到固城县一所乡村小学做了一辈子教师。据说他刚到这个叫葛村的村庄时,小学设在一家旧庙里,除了他,另外两位老师都是回乡知青。我父亲白天上课,晚上也住在庙里。大冬天放学后,他去河里担水。那时的小学生习惯了喝冷水,教室的后面有一大水缸,缸盖上放着一葫芦瓢,谁渴了就抡瓢灌一通。水埠其实就是一块架空的木板,他挑的是两只大木桶,桶沉板轻,他一不小心栽进了水中,好不容易爬上岸,在菩萨的慈目下钻进被窝中哆嗦了一夜,菩萨耐心地听他说了一夜胡话。这次落水事件,浇灭了我父亲想当校长的野心,他认清了自己一介弱书生的面目,从此甘心做一位平庸的小学教师,命运不忍心打击他,还是让他做了三十年的葛村小学教务主任。很多年后提起这件事,他说那天半夜他见到了老白,老白说他注定是一辈子吃粉笔灰的命,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一场空。老白是谁?老白是他爸,我爷爷。从时间上推断,那时老白早已离开了人世间,我父亲显然是在高烧中梦幻了。我爷爷死得早,我大爸和我父亲算得上是孝子,每年春节都挈妇将雏回老家陪老母亲。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淹城人喊爷爷为“阿爹”,喊奶奶为“亲娘”,我至今弄不清这种称呼的出处,似乎降了辈分。我亲娘是个个头不高的老太婆,记忆中她总是颠着小脚在阴暗的木楼里忙东忙西。我一直疑心她是“资本家太太”或者“地主婆”,与我见到的所有老太婆不同,她抽烟喝酒,床头边上还有一圈佛珠,早晚都靠在床头上念念有词,我仔细听过,自始至终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我当时有一个担忧,害怕她有一天被人揪出来批斗,幸亏这事一直没有发生。刘白说,亲娘的烟和酒都是他爸从上海捎过来。刘白是我大爸的儿子,我的堂兄。我的大爸仕途顺畅,先是做了所在工厂的厂长,后来又做了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总经理,他的手头比我父亲活络。他是最早出国谈生意的红顶商人,有一次他在饭桌上感慨,欧洲的动物内脏都丢弃掉,太可惜了。我和刘白都不相信,比如说鸭肫,比如说猪大肠,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舍得丢掉呢,外国人都是“戆大”。刘白说,他爸和他妈吵嘴,多半是为了给亲娘买香烟老酒。我一想也是,一到年底,我爸和我妈吵嘴,往往是为了给亲娘买鱼买虾的事。淹城人喜食鱼,尤其喜欢吃虾,摆筵席时无虾不成席。我父亲平时的口号是,吃光用光身体健康,算是最早的月光族,因此我打小就吃成了个胖子。但一到年底,他开始存钱,为的是买鱼买虾,探亲时大包小包孝敬我亲娘。年聚人多,我和刘白俩小子只能睡到阁楼上,没有床,把被褥扔在黑乎乎的地板上,木地板就是床。阁楼上没有窗,只有两块明瓦,“明瓦”就是玻璃,可以给黑暗的阁楼透一点亮光。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除夕夜,基本是在这个黑乎乎的阁楼度过。第一次上阁楼时,我讨厌“吱吱”作响的木地板,每走一步都胆战心惊,怕猛的一下踩出一个窟窿。我问我父亲,地板会不会踩塌?我父亲摇头说,没事,你使劲跺,这地板也不会折。刘白比我大两岁,懂得比我多,说,我爸说过,旧社会地主资本家都住木楼,木楼防小偷,小偷进了楼每走一步,地板就报警一次。我亲娘只是靠儿子们接济生活的穷老太婆,应该没钱可藏,最可能的原因是,她的儿子们没钱替她翻盖新楼,反正他们又不长住这楼。其实我怕的不是地板作响,怕的是阁楼上的黑暗,有刘白的时候,我一定要与他同上同下,后来刘白没了,尽管我已经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我死活也不肯上阁楼住,宁愿在我父母的房间打地铺睡,受大家的讥笑。我怕刘白半夜来捣我的胳肢窝,或者突然掏我的裤衩,说看看长毛了没有,这是小时候我们之间常发生的事。几十年过去,那样的场景至今仍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提醒我在黑暗中坐起,默默怀念我亲爱的堂兄。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那年代我们回淹城,我父亲手头宽裕的时候,我们全家坐公交车。从固城到淹城,每天只有一班公交,早上六点半开车,要坐半天的公交车才能到达,鸡还没叫我们就出发,赶二十里路到县城汽车站坐车。那年代汽车开得慢,沿途停靠站多,我巴不得汽车再慢一点,我喜欢闻汽油的味道,我宁愿站着,站在驾驶位附近,贪婪时嗅那股汽油味,可能那时的造车技术不过关,油路的跑冒滴漏没解决好,汽油的味道总是飘扬在车厢里,车头部分最浓,那是我最享受的时刻。在乡下,汽车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我是我们全班同学中第一个坐汽车的人,而且每个年底都能轮上一回,我为此骄傲。在葛村的小伙伴眼里,我是城市人,作为城市人的标志之一就是坐过汽车。如果我父亲钞票吃紧——他多半是把钞票换成了鱼虾鸡鸭——他就带上我和母亲搭顺风车。固城是个产粮大县,有一个专运粮食的粮食车队,把稻谷运往各地粮库,其中有淹城的一处粮库。我父亲以前的一个学生就在粮食车队做驾驶员,这个学生与我父亲关系不错,我们就搭他的车回淹城。我想坐在驾驶室,驾驶室暖和,最主要是能闻到汽油味,但驾驶室有押车员,而且常常还有别的人搭便车,我很少能如愿。我们一家三口坐在稻包上,稻包堆得很高,车一开动,寒风便加速了很多倍,我们一家三口抱成团,那风还如刀子般往脖子里袖管里钻,更糟糕的是那时的公路是土路,下车时我们三人满头满脸都是灰尘,我暗自叹息,车上仅有的一点汽油味,风一吹便无影无踪。司机把我们扔在公路边,我父亲千恩万谢地朝司机道谢,我母亲掏出一条手帕拍打我身上的灰尘。我们到柏树坟,还得在田野中走三四里的小路,这比起来时从乡下到县城的路途,已经不到一半,但是毕竟这时人已疲倦,我们一家三口肩背手提,步履匆匆,我母亲说,这哪里是回家,我们看上去分明是三个逃荒的叫花子。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只有在那样的时候,看见木楼的瞬间,我才感觉到祖屋的温暖,迫切地想冲进我亲娘的怀抱。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得证明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是我母亲的儿子?我母亲已走了二十年。小白说,你找出你父母的户口簿。我父亲现在的户口簿上没有我,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户口就迁出了。小白说,你回老家,找当地派出所,应该有原始材料。我说,房产证上是我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为什么一定要证明我母亲是我母亲?小白说,你还是个大学教授,说出这话就是法盲。尽管证上只有你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但婚后财产共同拥有,这房产其实有一半属于你母亲。我哑口无言,我在大学混了三十年,至今还是个副教授,小白抬举我,是为了摔惨我。我把电话挂了,只能听令回一趟固城老家。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固城县因固城湖而得名,解放初期属淹城地区,所以我父亲淹城师范毕业后到固城做教师,后来固城县被划到镇江地区,再后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固城县又划为南京市辖县。这固城县就像江苏延伸出去的一个岛屿,三面都被邻省包围,历来是苏南的贫困县。我父亲当年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被分配到了砖墙乡,固城县最偏僻的一个乡,因为经常闹水灾,土坯屋浸水就倒,能盖上砖墙瓦屋是乡民的梦想,就有了“砖墙乡”这个乡名。我父亲最初到砖墙乡,却几乎看不到一间砖砌墙的房子,很纳闷。但接着他就顾不上纳闷了,本乡没有一所小学,我父亲当时心中没有失望,倒是有几分激动。他看过《乡村女教师》这部电影,越是艰苦越是磨炼人,一张白纸才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将葛村边上的一座寺庙定为小学最早的教室,他是教师,却找不到学生。那时候填饱肚子是村民们的头等大事,孩子至少可以放牛搂草,干点轻活也没闲着,让孩子坐在教室里那等于少了一个小劳力。我父亲揣着干粮,一村村一户户死搅蛮缠,硬是凑到了一个班的学生,后来就有了几个年级,有了一所全日制完全小学。我母亲曾是卫校的学生,毕业后在县医院做护士,我外公是葛村的支部书记,她回家过周末时,一不小心认识了我父亲,一不留神嫁给了我父亲。在我父亲的忽悠下,她毅然调动,调到我父亲的小学做了一名小学教师。这要是在今天,是绝不可能的事。从城里到乡下,是水往低处流。从护士转行当教师,得有教师资格证,我疑心是不是我外公托人开了后门,我母亲说,哪里呀,那时代只要认得几个字就能当教师,有代课教师,有民办教师,我毕竟还有学历证书。那时候的人傻,让人看不懂。反正这样就有了我,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打小就在校园里滚爬。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父亲所在的小学就叫葛村小学,地址就在原来祠庙的地基上。葛村有大葛村小葛村,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姓葛。老师大多数也是葛村人。读过私塾的称老葛老师,读过工农兵师范的称中葛老师,高中毕业做民办教师的称小葛老师,小葛老师有高个葛老师、小个葛老师、胖小葛老师、瘦小葛老师等等,我母亲被称为女葛老师。偶尔来人喊一声葛老师,办公室的老师应声一片,很是热闹。学生之间,年龄差不多,辈分却大不同,有高年级学生喊低年级学生爷爷或叔叔,喊的人认真,应的人坦然,辈分在那里,当然也不乏孙子把爷爷揍得鬼哭狼嚎的个例。我外公在解放前是“桌爷”,“桌爷”就是长工的头,力气大,农活好,在长工中有威信,解放初期他带领长工响应党的号召,打土豪,分田地,成长为一名最基层的农村干部。因为村里有玩伴,我在外公家待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弄不懂为什么别人姓葛,我却要姓刘,强烈要求我也姓葛,其时一家人正在吃晚饭。我母亲看了我父亲一眼,给了我一巴掌,我外公把我抱到了腿上,我父亲仍然埋头吃饭。我外公外婆年轻时只生了我母亲一个,努力很多年想生个儿子一无所获。我父亲一个外乡人,娶了我母亲,似乎等同于入赘,却又从来没明确过。我外公、我母亲怕伤了我父亲的自尊,不肯开口提这事,我父亲呢,每在关键时刻装傻。很多年后我给儿子上户口时,我父亲说,其实姓不姓刘并不重要,你爷爷就姓白。可在当时,他就不松口让我姓葛。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驾车到了固城县城,离砖墙乡政府还有二十里。自从父母退休住到县城后,我已经难得来乡下。途中经过葛村小学,我泊了车,走进了校门。校门上“葛村小学”四个字还在,但学校早就合并到乡中心小学去了。校园里空荡荡的,操场上长满了茅草,据说教室曾经出租给一家服装厂做车间,但服装厂后来倒闭了,教室门上的挂锁长出了铁锈,校园成了一块荒芜之地。我找到我家的住处,那是两间旧教室隔成的房间,这样的宿舍,好处是窗子大,光线好,我从灰蒙蒙的窗玻璃看进去,原样基本没变。我家的土灶还在,只是挂满了蜘蛛网。门打不开,我坐在青石门槛上,朝远处眺望。小时候我从这个位置能看到大片的稻田,田埂上晚归的农夫,今天我坐下来,稻田还是稻田,田埂上没有一个人影,还没到农民收工的时辰。焦点娱乐平台登录
我闭上眼,校园就喧哗起来,我看到了从前,看到了少年的我和我的那些玩伴。
……
精彩全文请见《当代》2023年2期
焦点娱乐平台注册:www.sdptz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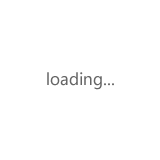
备案号: ICP备SDPTZC号 焦点平台官网: 秀站网
焦点招商QQ:******** 焦点主管QQ:********
公司地址:台湾省台北市拉菲中心区弥敦道40号焦点娱乐大厦D座10字楼SDPTZC室
Copyright © 2002-2018 拉菲Ⅹ焦点娱乐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网站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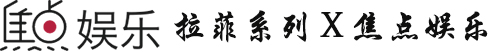
 在线客服
在线客服
